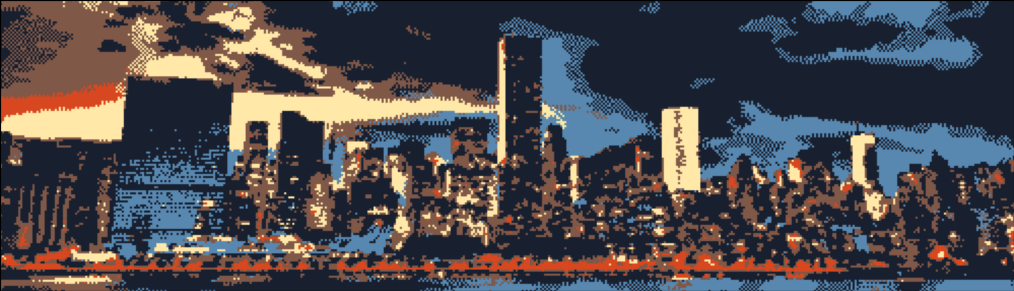 x
x
艾利克--十分令人吃驚地--是打破這讓人神經緊繃的沉默的人:「我這麼說吧。當妳得到妳的能力時,妳那天過得好嗎?」
我不需要思考太久:「不好。」
「如果我猜,妳得到妳的能力當時,正是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有猜錯嗎?」
「第二糟糕。」我安靜地回答:「大家都是像這樣嗎?」
「差不多吧。第二世代--那些能力者的孩子--才是那些唯一簡單度過的假面。」
莉莎向前靠,雙肘放在桌上:「所以如果妳需要找另一個把榮耀女孩想成個特權階級婊子的理由,不用再找了。」
「為什麼?」我問:「為什麼我們要經歷那種事?」
「那叫觸發事件。」莉莎回答我:「研究者們對於每個在世上有能力的人有個理論說,五人之中就有一個人具備超能力的潛能,但還沒達成觸發事件的必要條件。妳需要被逼迫到極限邊緣。或戰或逃的情形逼迫他們到極現,甚至,超過極限。然後妳的能力就會開始出現。」
「基本上,」艾利克說:「為了讓妳的能力發展,妳必須得有某些真的很屎蛋的事情發生。」
「這也可能幫忙解釋說,為什麼反派超過英雄的比例是二比一。」莉莎指出:「或者,為什麼第三世界國家有超能力的人口密度最高。不是假面,只是一大堆有超能力的人。」
「但是,那些父母有超能力的人呢?」
「他們不需要那麼強烈的事件來讓他們的能力彰顯出來。榮耀女孩是在體育課打籃球被犯規時,得到她的能力。她在幾次被採訪時有說過。」
「所以妳基本上就是要我們分享我們生命中最糟糕的時刻喔。」艾利克在咬下另一口他的漢堡之前說。
「抱歉。」我回答。
「沒關係。」布萊恩為了讓我放心說:「這是那種,妳只能從其他假面聽到的事情之一,而妳只知道我們。也許如果妳有選修大學的超亞人類研究課程,也許會聽過,可是我懷疑妳能在那裡得知所有細節。還是得要自己走過才行。」
莉莎伸出手抓亂了我的頭髮:「別擔心啦。」
為什麼我要提到起源呢?最後還是會輪到我,而我就得要說出自己的故事。
也許我想說出我的故事。
「莉莎說你們已經談論過我的事,講到你們認為我的生活很艱難,猜到底是什麼原因。」我盡力說出來:「我不知,我想自己一部分是想講出來,這樣你們就不會亂想出錯誤的結論。談論我得到自己的能力時的事。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講那件事又不破壞氣氛。」
「妳已經破壞氣氛了,呆瓜。」這句話從艾利克口中說出。
布萊恩揍了他手臂一拳,讓他喊了一聲。他瞪向布萊恩,不情願地補充說:「我猜,這代表沒理由不說吧。」
「就說吧。」莉莎激勵我。
「這不是個很好的故事。」我說:「可以我需要在開始前先說些事情。我已經對莉莎說了。這些我要講的人……我不想要你們為了我而向他們復仇,或作任何事情。我需要確認你們不會這麼做。」
「妳想自己復仇?」艾利克問。
我發現自己頓時想不出任何詞句。我沒辦法真的解釋出為什麼自己不想要他們干涉:「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猜自己感覺,如果你們跳進來把她們揍一頓,或污辱她們,或讓她們流淚道歉,我不會感覺自己處理了這些事。完全沒有任何結束感。」
「所以不管我們聽到什麼,都不要為此有什麼動作。」布萊恩澄清道。
「拜託了。」
「這是妳的特權。」他說,從莉莎的盤子拿了塊深炸南瓜塊,咬了一半。她把自己的盤子推向他。
「都可以啦。」艾利克說。
我花了幾秒鐘咬幾口我的培根起司堡,組織我的想法之後才開始說:
「我學校有三個女生曾經……直到現在,都讓我的生活很他媽的悲慘。做了差不多所有她們能想到的事來讓我的校園生活爛透頂,羞辱我,又傷害我。她們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做法,而且有好一陣子,她們像是要試著超過各自的創意或競爭地想出方法。」
在我從盤子轉移視線、抬起頭看向其他人臉上的表情時,我的心臟狂跳。這就是我,我想著。這就是我所來自的地方。當他們聽見真實的我,又對我的事或我到底能做什麼事毫無概念或主意,他們會怎麼反應呢?
「這樣持續了差不多一年半,然後平穩了下來。去年,差不多十二月的時候,她們……我不知。就好像她們太無聊了。惡作劇變得更溫馴,然後全部一起停了下來。全部的嘲弄都停止了,而且大部分恐嚇信也是。他們無視了我,讓我自己待著。
「我一直等著這懸而未解的事情變糟。可是我交了個朋友,一起加入她們的行列嘲弄我的女孩之中一個人還和我道歉。她不是主要的霸凌其中之一,比較像霸凌的朋友的朋友,我猜。她問我要不要和她一起出去玩。我當時太害羞,告訴她不要,可是我們還是會在上課前後和午餐時間時在一起。她靠近我、和我做朋友,是我認為象徵著騷擾已經結束的最大理由之一。我從來沒在她周圍真的放下防衛心,可是她也可以接受。
「而在十二月大部份日子裡,和聖誕假期之前兩週的課程裡,什麼都沒發生。她們不再理會我了。我當時能放鬆了。」
我嘆息一聲道:「最後在暑假結束,我回來之後。我本能地知道,她們在耍我,她們在等著接下來要執行下一個特技,好讓衝擊更強。我不認為她們有這麼多耐心。我走到我的個人櫃,然後,她們顯然襲擊了女生廁所的垃圾桶或類似的東西,因為她們把用過的衛生棉和衛生棉條塞進了我的櫃子。幾乎填滿了櫃子。」
「噁。」艾利克插話,放下了他的食物:「我在吃東西欸。」
「抱歉。」我往下看了眼我的盤子,戳了一下一片培根:「沒關係的,我能停下來。」
「現在說完吧。」布萊恩指示我,也許你能稱他命令我的語氣很溫柔。他瞪了眼艾利克。
我吞了口口水,感覺一股熱潮緩緩爬上我的臉:「她們在學校因為聖誕節關閉前這麼做,只用少數人--這點滿明顯的。我就在那擠滿人的走廊上,每個人看著我彎下腰要吐了出來。在我能恢復或阻止自己吐出早餐前,某個人抓住我的頭髮,用力到把我頭皮扯痛,然後把我塞進櫃子裡。」我幾乎能確定,那就是索菲亞:她是那三人之中最具肢體侵略性的人。可是他們不需要知道她的名字。
為什麼我要提起這件事呢?我已經後悔了。我看向其他人,然而我沒辦法讀懂他們的神情。
我不能在到這地步,又不說完這故事,即使我真的很想放棄:「她們把櫥櫃關起來然後鎖上。我就被困在那裡面,有腐臭油脂和嘔吐酸味,幾乎沒辦法移動,櫃子完全被塞滿了。我能想到的是,某個人願意弄髒手來搞我,可是所有學生都看到我被塞進櫃子裡,沒有人去找工友或老師來把我放出來。」
「我恐慌了,完全嚇壞了。我的意念四處亂跑,然後它找到了在那裡的蟲子。不是說我在那時候就知道它們在那。我沒有感覺到不同比例,而我能力那時給我的所有資訊,我的腦子完全不知道該怎樣處理。就我所知,環繞我全身,在學校牆壁、牆角角落都有,它們還在骯髒的櫥櫃裡面爬著,那裡有上千隻抽動著的、異形似的扭曲東西,每個都將關於它們身體和亂透了的生物情報,極小的所有細節全塞進我腦子裡。」
我嘆了一聲:「真的很難解釋,那就像,開啟了一個新的感官,可是你完全沒辦法理解。每個它們聽到的聲音都以一百倍音量彈回到我身上,音調、所有東西全亂透了,就好像它們想盡可能地讓聲音聽起來讓人不爽又痛苦。就算它們能看見東西,那就像我的眼睛在黑暗中一陣子之後打開,可是眼睛卻沒連接在我身上,而且他們看到的視野就像是一個非常骯髒的、汙穢的萬花筒。上千個萬花筒。而我又不知道該把它們任何一個關掉。」
「真糟糕。」莉莎說。
「當某個人終於讓我出來時,我馬上打了起來。咬人、抓人、踢人。毫無條裡地尖叫。大概讓所有跑出教室的同學都看了場好戲。老師們試著處理情形,醫護人員之後總算來了,那以後我幾乎什麼都不記得了。
「我在醫院猜出了我的超能力,同時他們也觀察著我,這也幫助我冷靜下來,讓我再次感到理智。大概,一週之後,我總算能把能力的一部份關掉。我爸從學校拿了點錢。足夠付住院的帳單之外還多出一點點。他說要告那些霸凌我的人,可是真的沒有證人願意說話,然後律師說沒有穩固的證據指明出應負責的人,起訴就不會成功。如果沒辦法確定結果,我們就沒錢上法庭。我從來沒跟我爸說誰是主要的霸凌。也許我該說,我不知。」
「我感到很抱歉。」莉莎將手放在我肩上。我為她沒有拉開距離或笑出來,心中充滿感恩。這是我第一次說出這件事,而我不確定如果她不接受的話我會怎樣反應。
「等等,這些女生作的事情還在持續?」艾利克問我。
我聳了聳肩:「基本上沒錯。我在出院回到學校後,事情就像以往那樣糟糕。我那理論上的朋友,不會和我對上視線或跟我說話了,而且她們在看見我,呃,發作之後,甚至也沒對我下手輕些。」
「為什麼妳不用妳的超能力咧?」艾利克問道:「甚至不用搞太大啊。讓一隻蟲子跑進她們午餐裡,也許讓一隻蜜蜂叮在她們鼻子或嘴唇上啊。」
「我不會對她們用我的能力。」
「可是她們讓妳過得很悲慘欸!」艾利克抗議道。
我皺了眉:「那點只會增加不這麼做的理由。猜出某個人開始用超能力惡搞她們一點都不困難。」
「妳是認真的?」艾利克靠在椅背上,雙手在胸前交叉:「聽著,妳和我沒聊過很多,也許我們並不那麼認識彼此,可是,呃嗯,妳並不笨。妳在誠實地告訴我妳沒辦法找到一個微妙的方法報復她們嗎?」
我轉頭看向莉莎和布萊恩,感覺有點被逼進角落:「幫我下?」
莉莎微微一笑,沒有說任何話。布萊恩聳了肩然後思考了一會兒,對我說:「我有點傾向於同意艾利克。」
「好吧,就這樣吧。」我承認道:「我是有想過。我考慮過執行些不會被追蹤到我的方案,像給她們蝨子。可是你們還記得母狗命令她的狗攻擊我時,我怎樣反抗的。」
「有點壓抑的憤怒喔。」莉莎說,仍然微笑著。
「對這些人也是一樣的啊。你知道如果我對她們做些惡作劇會發生什麼事嗎?她們會變得很悲慘、很惱怒,然後把氣發洩在我身上。」
「喔我老天。」艾利克笑著:「惡作劇。妳在我們每次對上假面時都需要這麼做的。妳能想像嗎?」
「我寧可不要。」我做了個鬼臉。艾利克在此為止的對話中固執地糾纏我,給我一種,若沒有好理由便難以說服的印象,所以我捏造出一點點真相來告訴他:「在我控制蟲子時,我差不多能看到我蟲子所見,感覺到蟲子所感。我不想讓我的蟲子爬進濕漉漉的跨下變成一件普通的事情。」
「喔哦哦。」
「如果你別再切換話題--我試著說的重點是,這些女孩們大概會把她們的悲慘發洩在我身上,就算她們不知道我在搞她們。我不信任自己不會報復,提高賭注籌碼。你看過我和瑞秋之間,第一次見面發生的事。狀況會惡化升級,我最後做得太過火了。洩漏祕密身分或讓某人嚴重受傷,像竜那樣,只是沒有他的恢復能力。」
「我不懂妳怎麼能就這樣冷靜承受。」艾利克說:「去報仇啊,或讓我們其中一人幫妳報仇。去請求其他人協助啊。」
「這些我都不能選。」我說,希望自己的陳述帶有足夠強調語氣讓這成為定論:「如果我自己處理或讓你們為我處理的話,有太多機率是事情演變到超乎我能控制。說起請他人協助,我不相信系統。經過法院裁判,和我一些老師談過之後再也不信任了。如果事情有這麼簡單,我早就已經處理了。」
莉莎向前靠:「跟我說,如果我們綁架她們的頭頭,頭上蓋好布袋,把她拖進一個貨車然後半夜丟到森林裡,離城鎮十哩遠,就只穿了件短內褲,妳不會覺得實在是棒透了。」
我對那個想像中的情景微笑,可是我邊搖頭邊說:「這正是我說的事。那樣太超過了。」
「她們把妳塞進歷史上最噁心的櫃子裡還鎖起門欸!」艾利克看著我,像我在試著跟他吵說地球是方的。
「把她留在荒野之中又沒穿任何衣服,幾乎就是邀請第一個看到她的卡車司機猥褻她吧。」我指出。
「好吧。」艾利克翻了白眼:「所以我們降低一點強度。丟下她時不給她鞋子、沒手機、沒錢包、沒零錢,她沒有任何能討價還價讓自己回家的方法。強迫她遠足。」
「那還是會有她被攻擊的危險。」我嘆息道:「漂亮女孩晚上走在路邊?」
「她們攻擊過妳了啊!」
「這不一樣。」
「唯一我能看出的不同,是她們應當被報應而妳不是。我是說,我沒和你們一樣聰明,所以也許我錯過了某些事。」
我搖頭說:「你沒有錯過,艾利克。我們是從兩個非常不同的角度看這件事。我不真的相信那種『以牙還牙』的作法。」
我正開始感覺自己再一次掌控了對話。然後艾利克突然扔下一發砲彈。
「那妳幹三小當超能反派啊?」
「逃跑啊。」這個詞幾乎立刻從我嘴裡說出來,在我有機會思考這代表什麼意思之前。我沒辦法在說話前花時間思索,不然他們可能會察覺有鬼。莉莎大概,一定會察覺的。
非常緊繃的幾秒過去,我窺探了下莉莎和布萊恩的神情。莉莎正看著我們的對話,她臉上掛著小小微笑,她手掌撐著下巴。布萊恩神情有點難以理解,雙臂在身前交叉,臉上沒有多少表情。
我解釋道:「如果我能將這不管的話,就能處理真實生活。痛扁一些人,為我自己闖出名聲,和朋友們一起鬼混。享受生活。」
這有點讓我自己驚訝,可是我理解到自己所說的都是真實,所以我甚至不需要擔心給莉莎更多提示。一秒之後,我發現自己可能有點冒昧:「我是說,假使我們是朋……」
「如果妳把那句話說完。」莉莎警告我:「我會給妳腦袋一巴掌。」
我感到我雙頰和雙耳有陣熱潮。
「是啊,泰勒,我們是朋友。」布萊恩說:「而且我們很感激,或至少,我很感激妳足夠信任我們到願意分享妳的故事。」
我不確定該怎樣回應。他聽過之後還沒有讓我難受的這個事實,對我來說意義超級大。只有艾利克反駁我,而他也沒有非常刻薄。
布萊恩皺眉說:「你們倆不是也應該要分享你們的故事嗎?」
艾利克搖了搖頭然後伸展雙手到頭上方,接著把雙手放到他肚子上休息,他的沉默已經足夠回應了。
莉莎,就她的部分,微笑然後說:「抱歉。我喜歡你們,可是我需要先喝幾杯我才要分享那個特定的趣聞,而且我還有幾年才能合法喝酒呢。」
「只有泰勒說的話看起來就不怎麼公平了。」布萊恩指出。
「我、我不是因為期待你們報答才講我的故事的。」我趕緊補充:「真的,沒關係啦。」
「那麼,你就是自願囉?」莉莎問布萊恩,無視我的抗議。
布萊恩點頭:「是啊,我猜我自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