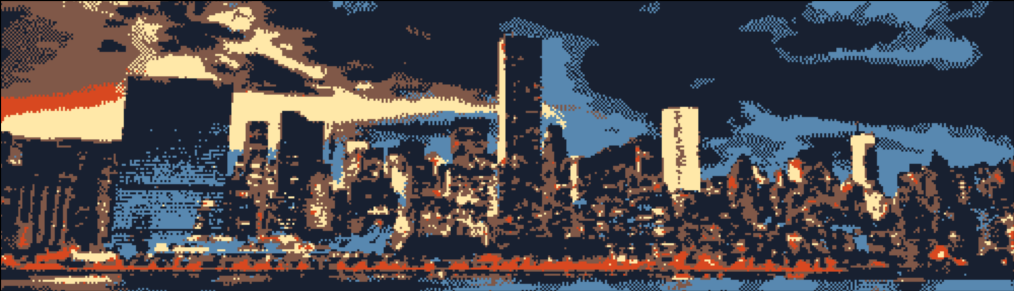 x
x
求寵 2.4
「沒有人喜歡她。沒人想要她在這裡。」朱利亞說。
「真是個魯蛇。她上禮拜五甚至也沒交美術課的主修計畫呢。」索菲亞回答。
「若她沒想要認真,那她又幹嘛來學校啊?」
儘管這段對話聽起來如此,他們正是在談論我。他們只是假裝彼此說話。他們成功創造貌似有理的推諉不知情,同時又算計心機,表現像個青少年似的,假裝我不存在。是僅有高中生才能辦到的不成熟混和詭詐。如果不是針對我的話,我會嘲笑其中的荒謬。
就在我離開教室時,艾瑪、麥迪森和索菲亞把我推擠至牆角,還有另外六個女孩支持她們。我沒辦法鑽空隙離開又不被推回或槓拐子,所以除了靠在窗戶聽著這八個女孩無止境的嘲諷與奚弄之外,我什麼都沒辦法做。一個女孩結束前,又有另一人開始。在她們羞辱著我時,艾瑪站在後面保持安靜,臉上帶著淺淺微笑。我沒辦法在不激起另一陣新鮮的侮辱叫囂潑上我臉的前提下對視她們的眼睛,所以我直直盯著艾瑪。
「全年級最醜的女孩。」
她們根本沒想過自己到底說了什麼,許多辱罵失去控制地錯失准心或互相矛盾。比如,一個人會說我是個蕩婦,接著另一個人會說男人會在碰觸我前噁心到吐。重點不在措辭巧妙,或聰明,或正中目標。這比較像為了一次次傳遞話語背後的感覺,敲它進心裡。如果我有時機插嘴,也許我能想到些反擊。如果我能直接終止她們的氣勢,她們八成不會再回到這樣輕鬆的節奏。雖說如此,我沒辦法找到妥當的話語,而她們沒給任何開口交談的空隙讓我能回話。
這個特定的策略對我而言相當新穎,但現在,我已經被這樣對待一年半了。到一定程度時我得到了結論,放輕鬆待著,接受大部分事情,會比較輕鬆。她們想要我反擊,因為所有事都對她們作弊般有利。如果我為自己反抗而她們仍「贏了」,那這只會助長她們的自負。如果我以某些方式取得優勢,那麼她們下一次會更固執更卑鄙。所以因著相同原因我沒有在麥迪森拿走我的作業的事上反擊,我僅僅靠在窗戶旁邊的牆上,然後等她們對自己的遊戲膩了,或太餓得去吃午飯。
「她都用什麼洗臉啊?肥皂鋼絲球?」
「她應該這樣洗!她會變得更好看!」
「別再跟任何人說話了。也許她知道她聽起來像個智障然後保持她的嘴閉著。」
「不對,她沒那麼聰明啊。」
在距離艾瑪身後不到三呎,我能看到蓋德利老師離開他的教室。我看著他端著一疊資料夾在他手臂下,找著他的鑰匙鎖門,而這段激烈的辱罵沒有停下來。
「如果我是她,我會自殺。」其中一個女孩如此宣揚。
蓋德利老師轉身看向我的雙眼。
「所以真開心我們沒有個體育室給她用。你能想像在換衣間看見她嗎?噁心到我都想催吐了。」
我不知道我臉上帶著什麼表情,但我知道我看起來不開心。在不到五分鐘前,蓋德利老師曾試著說服我和他一起到辦公室,告訴校長霸凌的事。我看著他給我一個悲傷的神情,將檔案夾堆換到另一隻空著的手然後離開。
我太震驚了。沒辦法轉動腦袋理解他怎麼能就這樣無視這群人。他試著幫我之後,他有挽救自己的錯誤,面前發生無法無視的情況中做他被要求的事嗎?他單單已經放棄我了?在用他那完全沒有效果的方法試圖幫忙後,在我拒絕他的幫助兩次後,他就這樣決定我不值得他的心力了?
「你應該看她剛剛在課堂上失敗的樣子。光看著都難受呢。」
我握緊我的拳頭,然後強迫自己放鬆手。如果我們全是男生,情況會徹底不同。我現正值一生中最好的體態。我能開打時揮個幾拳,也許造成一、兩個人流鼻血。我知道我最終會打輸,被數個人踹擊和強力塞進地板裡,但事情會就這樣結束,不是像她們一樣拖延。我身體受傷個接下來幾天,可是我至少能有知道其他人也受傷的滿足感,我也不必坐在這堆辱罵的彈幕中。如果造成了足夠傷害,學校就會注意到,然後他們也沒辦法無視一個一對九鬥毆的情況。暴力吸引注意。
但事情在這裡不是這樣。女生的玩法很骯髒。如果我給艾瑪妝點些淤清,她會跑到辦公室說些虛構的故事,她的朋友們會支持她的事件版本。最重要的是,向學校告密是社會性自殺,不過艾瑪或多或少是所有人的頭頭。如果她想要去找校長,大家只會將事情看得更嚴重。在我回到學校時,他們會私下以一種讓我完全看起來像個徹底瘋子的方式彼此傳遞著故事。事情會變得更糟。艾瑪會被視為受害者,而其他之前無視霸凌的女孩們會在艾瑪的代表下加入霸凌。
「而且她聞起來有臭味。」一個女孩無聊地說。
「像過期的葡萄和柳丁汁。」麥迪森帶著一點笑意插話。又來一次,提起果汁?我猜那是她的點子。
看起來她們耗盡了力氣。我認為一、兩分鐘之後他們就會感到無聊然後走開。
看起來艾瑪得到了同樣的印象,因為她向前踏一步。女孩們讓路給她空間。
「怎麼回事,泰勒?」艾瑪說:「你看起來心情很差。」
她所說的話看起來不符合現在的情況。我為了他們那不知有多久的辱罵維持了冷靜。我感覺到一股混和挫折和無聊的情感勝過任何一切。我張開我的嘴要說些什麼。一個毫無優雅的「幹你娘」就足夠了。
「你這麼心煩,你要一整週哭到你睡著嗎?」她問。
我正思索著她所說的話時,文字死在我的喉嚨裡。
在我們幾乎一年前尚未進入高中時,我在她家,我們倆人一起吃早餐,過度大聲地一起聽音樂。艾瑪的姐姐拿了電話下樓。我們關掉音樂,然後我爸在電話另一邊,等著以一種破碎的聲音告訴我,我媽在一場車禍中去世。
艾瑪的姐姐載我回我家,而我整程嚎啕大哭到家。我記得艾瑪也哭了,也許是因為同情。也可能是因為她認為我媽是世界上最酷的成人。或者可能是因為我們真的是最好的朋友,而她不知道該如何幫助我。
我不想去想接下來的那個月,但記憶碎片無視要求便自己浮現於我的腦中。我能想起意外聽見我爸嚴厲責備我媽的遺體,因為她邊開車邊傳簡訊,而她是唯一一個該承擔責罵的人。某一次,我連續五天幾乎沒吃任何東西,因為我爸徹底頹喪而我不在他的雷達當中。我總算向艾瑪求助,請求到她家吃幾天飯。我想艾瑪她媽將事情瞭解清楚,打了電話給我爸,因為他開始重新振作起來。我們建立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讓我們家不會再分崩離析了。
在我媽過世一個月後,艾瑪和我在一座公園的遊樂設施的橋上坐著,背靠著潮濕的木頭而冰冷,啜飲著我們從炸甜圈洞買的咖啡。我們沒任何事做,所以就只是四處走走隨意聊聊。我們遊蕩到遊樂場,在那裡讓腳後跟休息。
「你知道,我很景仰你。」她突然說。
「為什麼?」我回應,徹底因為某個像她這樣美麗、受歡迎、令人感到驚奇的人發現我身上有什麼值得欣賞的事實而困惑。
「你非常堅強。你媽去世後,你完全崩潰了,但在一個月後又這麼沈著穩定。我做不到。」
我能記得我的坦承:「我才不堅強。我能在白天時保持冷靜,但我曾整整一週都哭著入睡。」
就在那裡,我的話語已足以開啟洪水閘。她讓我在她肩膀上哭泣,我平復時咖啡已經冷了。
現在,在我瞠目結舌地看著艾瑪,沒有言詞,她的微笑擴張。她記得我當時曾說的話。她知道那個回憶能被激起。在某些時候,她想起那段記憶,然後決定要以其為武器。她一直等著要將其砸在我身上。
肏我的。這真有效。我感覺一滴淚滑過我一邊臉頰。我的能力在意識邊緣咆哮,嗡嗡作響壓迫著我。我將它壓了下來。
「她做到了!她在哭欸!」麥迪森笑著。
我對自己感到生氣,我的手擦過臉頰刷去眼淚。還有更多淚水在我裡面膨脹,準備要取代那滴的位置。
「艾瑪,這好像你有超能力一樣!」其中一個女孩吃吃地笑。
我為了能靠在牆上,剛才把後背包放了下來。我伸出手檢起背包,但在我手能觸及背包前,一隻腳鉤住背帶將它從我身邊拖走。我抬頭看向那隻腳的主人--深色肌膚,柳枝般苗條的索菲亞--對我嘻嘻作笑。
「喔我的天!她要做什麼?」其中一個女孩說。
索菲亞靠在牆上,一隻腳隨意地踏在我的後背包上。我想,如果這給她一個繼續她那保持距離遊戲的機會,不值得和她為此爭執。我將背包留在原地,在聚集的女孩中挖開一條路出去,以足以撞倒人的力道肩膀撞上一個旁觀者。我跑到階梯,跑出在一樓的門。
我逃跑了。我沒有確認,但有很高的機率他們正從走廊底的窗戶看著我。這真的不重要。事實是,我剛答應要以自己的錢付三十五元買一本世界議題課本來取代那已經浸滿葡萄汁的課本,而這不是我最優先的擔憂。即使那幾乎是我買假面服部件後全部所剩的錢。我的美術期中作業也在我背包裡,全新修整了。我知道我不會以完美狀態拿回任何東西,如果我真能拿回的話。
不是的,我最重要的擔憂是離開那裡。我沒要打破我對自己立下的約定:不要把我的能力用在她們身上。那是個我不會跨越的界線。即使我所做的事並非徹底無害,比如給她們全部人虱子,我不信任自己會就此停手。我也不相信自己能不提供露骨的提示,僅僅為了看到當他們瞭解一直折磨的女孩是個貨真價實的超級英雄而有的表情,便讓人知道我有能力或損壞我的秘密身分。這是某些我忍不住想著的白日夢,但我知道衍生的長期問題會破壞這夢。
我合理化地想著,也許最重要的是讓兩個世界分隔開來。如果我試著要逃跑的世界混著我試著逃避的人事物呢,這樣逃避現實有什麼用?
在回到學校的想法浮現腦海之前,我發現自己正納悶著自己要做什麼來填滿我的午後。
ns3.139.90.252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