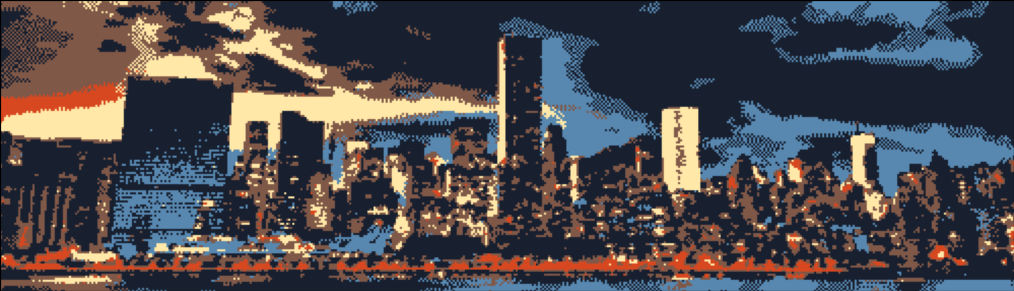 x
x
布萊恩比他一般身高的男人更快。他踩到一邊來避開我的出拳,並轉動著身體令我意識到他準備要踢。我並不知道他要踢往哪裡,而他踢得也不比出的拳輕。明白到這一點,並遵守著他要我保持不被預測的指示,我向前衝去,笨拙地摟住他。
他的大腿在扭身的時候擊中我的肋部,雖然很痛,但也不會比被直接踢中更痛。雖然如此,我還是成功地把他撲倒。但我感到的任何勝利感都是短暫的,因為我跟他一起倒下,而他對接下來的比我更有準備。在接觸地面的那一刻,他用他的雙手和仍抬起的大腿借力把我撥到右邊。並趁著我還沒反應過來,朝著我的方向翻過身來,用雙腿夾住我。
我對著他的肋部出拳,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腕,扭動我的胳膊,直到肘部指向我的肚臍。我用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襯衫,希望可以擺脫他(想得美),卻也被抓住了。他調整扭著我右臂的手,將它固定在我頭上方的地面上。
「還不錯的開始,」他對我微笑著。
意識到我被他綁著的姿勢,感覺到他的大腿頂著我的臀部,他一部分的體重壓在我的下半身上,我的神經差點要被燒掉了。我停止了思考。更別説我腦裏首先想到的是將他說的「開始」解釋為我們所處在的姿勢會引致其他事情。
「繼續這樣下去的話,你會變得很能打呢,」他解釋道。「當我們在地上,而我把你往一邊推的時候,你應該借力往旁邊滾,跟我拉開距離。如果你夠快的話,你可能還可以趕在我之前站起來,那樣你就有攻擊的優勢了。」
「唔嗯...」是我唯一能夠給出的回應。
「你是要放過她了,還是想繼續享受著?」莉莎坐在沙發上問道。她的手交叉靠在椅背上,下巴放在靠墊上。她的嘴巴被手臂遮住,但我懷疑底下是個奸詐的笑容。
布萊恩微笑著站了起來,「抱歉,泰勒。你也要來一場嗎,莉莎?」
「我的衣服不適合,而且太早了,我也不想阻礙到泰勒,」她頭也抬地説著。當我生氣地看著她時,她對我眨了眨眼。
布萊恩與我站著互相面對對方,我們兩個都猶豫了許久,我確保著自己剛好站在他的攻擊範圍外。
「我很驚訝你們倆還有體力這樣搞耶,」莉莎評論道,「昨晚在外頭到處跑完之後你的腿不酸嗎?特別是你,泰勒。今天早上你才剛跑完步,現在又要練拳?」
「如果我的膝蓋可以説話,它們會已經痛得尖叫了,」我告訴她。布萊恩趁我分心時起步準備進攻,我對他舉起了手,他便退了回去。「但運動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一切都還好嗎?」布萊恩問我。我聳了聳肩,瞥了一眼莉莎。
「泰勒回了家之後,」她解釋道,「跟她爸吵了一架,所以又回到了這裏。可能會在這呆上一會兒,沒錯?」
「沒錯,」我同意道。
「抱歉,」布萊恩同情地說。
「我也是,」我説道。並往前踏了一部,試圖引誘他出擊,但他沒有上當。「我愛我老爸。我從來沒有像其他小孩經歷那種叛逆的階段,沒有在他身邊感到羞恥,或跟他有過什麽衝突。我以爲我們比那樣更親近,直到昨晚。」
「事情會好轉起來嗎?」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爲了轉移話題,我承認著,「好吧,我卡住了。站在這裏面對著你,我不知道可以做出什麽不會讓我被打或是被撲倒的動作。我向前走一步,而你就有一萬個把我痛揍一頓的方法。如果換做是你的話 ,會怎麽做?」
「老實説?嗯……」他放鬆了一點,「問得好,我想我會去找附近的東西來當武器。」
「除了那個呢,這裏沒有什麽可以用來練拳又不會傷害到你的東西。」
「那我就做你現在在做的,等敵人先出手。」
「好吧,出啊。」
他應承著,向我靠近,並假裝往高處踢,然後又低下身子試圖把我的脚踢開,使我絆倒。我倒是可以應付這種程度,輕輕越過他的腿。儘管如此,他還是比我領先一步,用他伸出來踢我的腳踩在地上,一個勁得用肩膀把我撞倒。我聽取他給我的指令,順著往後爬來拉開距離,但是他有站著的優勢。他側身跟上我的速度,用膝蓋往前一頂,在我臉前幾厘米的距離停下。
「你有在學,」他説。
「很慢地學。」
「你在學,」他强調著,「你聽從我説的話,牢記在心裏,而我幾乎都不用再次提醒你任何事情。」
他伸出手給我,我們互相抓住對方的手腕,他便把我從地上拉起來。
「我帶著咖啡和早餐而來,」艾利克宣佈,「因爲某個隊長懶得來拿。」
「滚蛋啦,艾利克,」布萊恩回應道,他語調不含一絲惡意。他放開我的手去接咖啡,「每十天有九天我都會在來的路上幫你買東西吃。」
「那是為你住在外面而給我們添麻煩的賠償,」艾利克回應道,並走到沙發來給莉莎和我遞咖啡。莉莎從紙袋裏拿出几塊蛋糕,並給了我一個。我在她一旁沙發上的坐下。
「那麽,」布萊恩對著準備坐下來的大家說。「我認爲我們應該先把一些事情説清楚,畢竟現在得知了我們的雇傭者的身份,雇傭我們的原因,以及我們未來的可能性。」
母狗在另一個沙發上坐下,她提起她的腿,小狗們紛紛在她一旁跳上。那表示布萊恩唯一能坐的位置在艾利克和我的中間。我對他的腿和肩膀碰到我的位置異常的在意。我跑過又打過,應該流了很多汗。聞得到嗎?會不會臭?我忍不住感到自覺,但我又不想看起來突出。於是我試著專注在討論上。
「首先,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對蛇蜷提出的建議進行多數表決。就我看來,這件事情太重要了,帶來太大的變化,假如有人感到不高興或不滿意,我們就不應該魯莽行事。要麽我們達成共識,要麽就不做。」
我並不是唯一一個默默點頭同意的人。
「第二,艾利克,我想知道蛇蜷説的是什麽意思。你過去的身份,你的父親。這些會在以後給我們添麻煩嗎?」
艾利克嘆了口氣,翻著白眼往後靠,「沒法忽略這個嘛?」
「我不知道,可以忽略嗎?」
「我老爸在蒙特利爾經營他自己的組織。我在這一切之前爲他幹活。」
「他是誰?」布萊恩問道。
「尼科斯.瓦席爾。碎心漢。」
我揚起了眉毛。
莉莎吹了聲口哨,「自從蛇蜷透漏了那個綫索,我想到了幾個可能性。排除后剩下四個。包括碎心漢,都説得通,就是比較難相信。」
「他很強欸,」布萊恩說。
「不對,」艾利克搖著頭,「他很嚇人,恶名昭彰。但他並不完全跟你所説的一樣。」
碎心漢是當你有像豪俠一樣的能力,可以控制情緒,但是毫不節制地用來做自私的事情。跟豪俠的差別是,碎心漢並不需用什麽能量打中你才有效。他只需要靠近你,並且對你的影響是長期或永久的。
儘管艾利克試圖使他的父親顯得沒那麽大不了,我也很難忽略從小就在晚間新聞上聽到這個傢伙所做的事,也經常在網絡上有關假面的地方讀到對他的提及。碎心漢會找一些美麗的女人,令她們愛他,非常地愛他,她們組成了一個像邪教一樣的團體,無微不至地侍候他,為了他而犯罪。她們敬拜他到了甚至還願意為他而死的程度。當然,這也表示他有一大堆小孩。其中包括著艾利克。
「哇,」我小聲説。我問艾利克,「你在那家伙身邊長大?」
他聳了聳肩,「那對我來説就是正常的。」
「我是說,那是什麽感覺?我都無法想象。那些女人對你很好嗎?怎...那種生活都是什麽樣子的?」
「我爸的受害者只在乎著他,」艾利克說,「所以答案是不,她們對我或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好。」
「講細節,」莉莎說,「來嘛,説清楚一點。」
「我不是個健談的人。」
「說,不然我打你,」她威脅著。
「同意,」我説。
他皺了皺眉頭,把一隻脚越過另一隻脚放在咖啡桌上面,把咖啡杯平衡在皮帶扣上,更深地沉入沙發。「我們要什麽就有什麽,不管是金錢還是物資。家事都由爸的手下處理,而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偶爾照顧一下嬰兒。我們不需要上學,但我的一些兄弟姐妹為了躲避我爸而有去上。」
「爲什麽?」我問道,「還是這樣問很笨?」
「額。很難解釋。他培育了我們,爲了我們而繁殖,那當他的『家庭』成員被帶走,他會竭盡全力將我們救回來。有必要的話發動戰爭也可以。但是當我們在他身邊的時候,他幾乎一點也不會關注我們。而在他有關注的時候,也只是爲了訓練或是考驗我們。訓練通常意味着因爲不听话,侮辱他甚至有时看了他一眼而被注入一劑麻痹的恐懼。考驗則是在我們的生日或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進行的...他會企圖製造一場觸發事件。那並不難,考慮到我們是第二代的假面,這不用說,但是他從我們八歲左右的時候就開始這麽做了。」
「你當時幾歲?當你能力顯現的時候?」我小聲問道,爲了不只是碎心漢的受害者,也爲了處於那種情景的小孩深深地感到同情。
不管我感覺怎樣,艾利克仍然看起來對這個話題感到無聊。「很難說。畢竟我沒去上學,也沒有特別記錄下來,我自己更數不清。可能十歲或者十一歲吧。我是他第四個顯現能力的小孩,而當我離開的時候他大概有十八個左右,大部分都還是嬰兒。」
那代表著他,而不是戰慄,才是我們當中最有經驗和資歷的人。
艾利克聳了聳肩,「就這樣啦。我在他底下幹了三到四年。我們做了不少事,我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我當初是叫劫體師。他後來開始煩我。可能因爲自從我有了能力之後他發現要控制我沒有之前那麽的簡單,所以他開始濫用我。試圖突破我的極限,逼我做很多危險的,令我良心受損的東西。希望我會受不了,去求他停下來,這樣他就可以用來做讓我服從他的條件。」
「還有呢?」
「他會叫我把侵略我們的地盤的士兵幹掉。然後他會說我沒做好,要我對一位俘虜再做一遍,而我知道不管怎樣,他只會一遍又一遍地叫我做同樣的事情。那又是一個逼我突破極限的方法。我說服自己不去關心剛剛殺害掉的人,也許我真的沒有。也許我現在也沒有。我不知道。但那真的很沒意思。」
他聳了聳肩,「我沒有什麽理由留在那。所以就跑掉了。換了我的名字,搞了新的身份證,還改了我的反派稱號。」
他按照父親的命令殺了人,這表示他是我們當中的第二個殺手。兵器大師一定是在發現艾利克的舊身份之後挖出了一些資料才得到的結論。
「是在什麽時候的,你殺人的事?」我輕聲問道,「你當時候是幾歲?」
「嗯。老闆找上我的時候我已經離開兩年了,而那距離現在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所以是三年前。我當時應該十二或十三歲。」
這樣可以原諒嗎?他是被逼去做的,他還是小孩,又在那種沒有道德指南的情況下。但是,他描述的方法讓我感覺有點不對勁。冷血的謀殺。
「你説他會想辦法把小孩帶回去,」布萊恩說,「在這裏也會嗎?假如他發現了你的身份?」
「不知道,可能吧。我猜他會先派我的其中一個兄弟姐妹來跟我談,如果我不答應回來他才會用其它的辦法。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大概會趁他自己還沒來之前先走。」
「或者我們可以支援你,」布萊恩提出。
「也可以,」艾利克同意道,顯然並沒有察覺友意。「沒了嗎?還有問題想問尊敬的本人嗎?」
「還有一大堆,」我説,「但是我認為我們需要先解決當今的另一大話題。」
「對,」布萊恩贊同道,「我對你從來都沒有提到這件事不是很高興,我很擔心像那家伙的人會衝著你而來,衝著我們而來,但是我們現在沒什麽可以做的。所以先讓我們專注於更緊迫的事情。」
莉莎把腳收到沙發上,「你們都有什麽想法?在投票之前先説説。」
「我覺得這很合理,」艾利克回答道。「那也是我覺得最終會做的事,控制一個區域,成為它的大佬,讓錢毫不費力地滾滾而來。」
「也可能會很麻煩,」我説,「這取決於他是否能夠保持秘密,并且有多成功。要是搞砸的話,我們就要準備對付捍衛者給我們派來的任何假面。如果消息傳出去的話,我們可能還要面對波斯頓或紐約的分隊。」
「叫我樂觀主義者,」 艾利克說。「但我不覺得會那麽糟。」
「泰勒讓我想起在搶劫銀行時説的,以及後來發生的事。」布萊恩說。「我們之所以總的來說一直成功,是因爲我們只挑能贏的戰鬥,以攻擊爲主,並令敵人出其不意。而在我們沒有那麽做的時候,我想特別像是跟爆彈打的那場,我們真的很難獲勝。那是我們最接近被幹掉的一次。考慮到我們在掌控地盤的時候要打的主要是防禦戰。」
「我們還是可以取得優勢,」莉莎回應道,「以策略,資料收集,先發制人。我可以從内部得到訊息,也沒人阻止泰勒用蟲子監控著區域。此外,蛇蜷也沒説我們不能自己雇傭一些超亞人,只是任何想在布拉克頓灣幹活的都必須經過他的許可。因此我們理應上可以雇傭其他人,如果需要增加勢力的話。」
「我的問題是,」我小心地説,「這一切聽起來好得難以置信。要是最後不成功怎麽辦?要是結果對我們不益,或是他背叛我們,要是他其實並不想他自己想得那麽有本事怎麽辦?我們就退出嗎?我們能退出嗎?」
「我擺脫了我爸,」艾利克說。「要擺脫蛇蜷有那麽難嗎?」
我沒有一個好的答案。「我想我們對他和他手上的資源都瞭解不夠。」
「我也有我的擔憂,」布萊恩說,「但是我感覺不管我們加不加入,蛇蜷也還是會實行他的計劃。比起在一旁靜觀其變,我更寧可參與其中。」
「嗯,」我認同著,「我想就目前而言,我們加入然後成功的收益,遠遠超過了損失的風險。」
「那麽,有誰贊同呢?」莉莎問我們。
我舉起了手。布萊恩,艾利克與莉莎也跟著舉起了他們的。那只剩下一個唯一沒有參與有關蛇蜷的提議的人投反對。母狗毫不在意地揉著布魯圖斯的肩膀。
「怎麽啦?」布萊恩問她。
「我不喜歡。不信他。」她頭也沒有台地說。
我往前傾向著她,「並不是説你不信他有錯,但能説説爲什麽嗎?」
安潔力卡,那隻單眼,單耳的小獵犬用鼻子磨蹭著她,母狗撓了撓她的耳朵。她解釋道,「他講太多廢話,會像他一樣講廢話的人都有東西想藏。」
「我不覺得他有什麽東西要隱瞞,」莉莎說,「如果有的話我的能力應該會提醒我。」
「我只聽我的直覺,而我的直覺説不。再説,現在我們也過的很好。」
「但是我們可以過得更好。」 艾利克說。
「你的看法,跟我沒關。我們講完了嗎?你説要是大家不全部同意我們就不幹了,而我就不同意。」
布萊恩皺著眉頭,「等等。我以爲我們會討論一下,聽聽大家的意見。」
「沒什麽好討論的,」母狗站了起來並吹出兩聲口哨。她的狗從沙發上跳了下來跟著她。「我去工作了。」
「等一下,」布萊恩說「別……」
莉莎停住他,「那就等一下吧。他説我們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們可以等個一兩天左右再聊。母狗,去做你該做的,別讓它耽擱你。但是下次議題再出現的時候,試著更開放地跟我們談判跟討論,好嗎?」
母狗的眉毛擠成了怒視,但並沒有針對任何人。她把注意力轉移到收集她需要的東西……塑料袋,幾塊能量棒,牽狗的繩子,以及一個的背包,帶有亮藍色塑料棒從拉鍊的縫隙中伸出。
「喂,」我説,「我能跟著來嗎?」
我告訴自己我想和這些人更好地交流,那我就不能只坐在一旁等著被邀請。我需要積極一點。想到我是犧牲了什麽才能做在這裏,我至少要做到這點。
母狗卻看起來并不是很高興。她給我的眼神似乎可以把小動物嚇跑。
「幹你娘,」她噴出那話。
「嘿。怎麽能這樣?」我愣住了。
「你想過來煩我讓我改變主意。那麽幹你的。你不准跑來我的地方,干擾我的事,讓我做不想做的。」
我開始舉手示意,但又停了下來。母狗有不一樣的方式處理社交。她分別不了語氣,强調或者諷刺,而先例使她對任何言論都視爲諷刺和敵意。而那不只言語,我懷疑連舉起手的動作也會被視爲威脅,或者像是一個動物想要使自己看似龐大來去趕走他人。
我需要以有最少誤會的空間的方法跟她溝通。
「你要去幫那些被救回來的小狗,對吧?那就是你出去做的?你的『工作』?」
「跟你沒關。」
「蛇蜷說你過勞了。我能提供額外的幫手,這樣你能跟專注在需要注意的小狗上。」
「放屁。」
「夠了,」布萊恩開始站起來,「你要冷靜一下……」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壓著他。「我沒事。瑞秋,我來跟你做個約定。」
她眯起眼睛。
「我覺得上一個約定還蠻公平的,所以聽聽看?」
「好吧。」
「讓我跟著來。我會試著幫忙,我們可以聊聊,但不提蛇蜷的事,除非你先講。而如果我提了,或者嘗試用某種方法忽悠你,我就免費給你一次機會。」
「機會做什麽?」
「打我一拳,你想怎麽打就怎麽打,往哪裏打都行。我知道布萊恩説了不能重複我們第一天見面時發生的事,不能在隊裏打架之類的,但這是個破例。完全批准。」我瞥了一眼布萊恩,他擔憂地看著我,並輕輕搖著頭。
「不用了,」母狗說,「你只會用另一種方法騷擾我。」
我衝動地說,「那這樣吧,如果我們回來之後,你覺得我有哪裏讓你不開心,你就可以打我。」
她盯著我看了一會兒,「所以我只要跟你呆著幾小時,就可以把你牙齒打掉?」
「不可以,」布萊恩大聲地説。
「可以,」我告訴她,並看了一眼布萊恩。「如果我擅自開始講蛇蜷的事,或者我惹怒了你。」
她把我看了一遍,「隨便。如果你怎麽想被打的話,那就來找死吧。」她把背包脫下來往我一扔。我用了雙手接住。那比看上去更加的重。
當我趕去把跑步鞋穿上的時候,艾利克小聲對我説,「你瘋了。」
也許,應該吧。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對付母狗。
我希望這不是我要後悔的事情。
ns3.15.165.7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