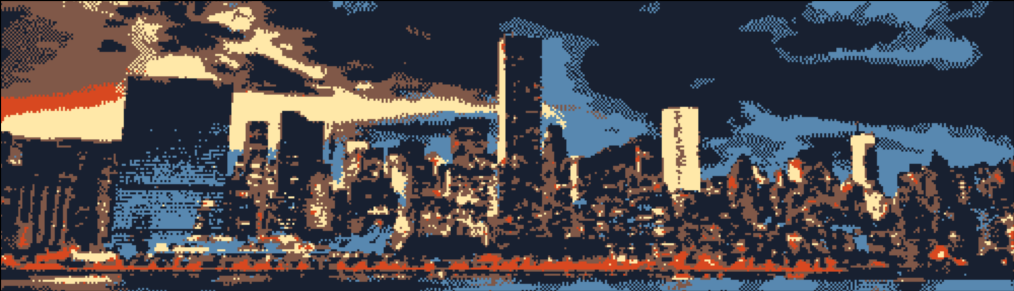 x
x
「你被打中了嗎?」在我們四人於街道上衝刺時我問了攝政。沒有回應。我試了一次,更仔細些:「攝政!聽我說,你被打中了嗎?」
他細微地搖頭,緊緊將另一隻手抓著依靠肩膀:「不是被打中。我的能力用太過頭、太快了,回火了。左手臂抽筋,是痙攣。我沒辦法動它。別擔心。」
「回火?」我問。
「別擔心!」他咆哮的回應,因為是我們那通常沈著、過渡淡然的艾利克,特別讓我震驚。他彷彿想補償自己的爆發,低語道歉:「幹。抱歉。這很痛,但我會接受。你們先專注把我們弄出這場混亂吧。」
「媘蜜。」我仍握著她的手,所以我捏了下確定我得到她的注意力:「這就會是妳發揮的絕佳時機了。」
「特別在妳讓我們直接走進那幹他媽的情況,搞砸了之後。」戰慄低吼著。
「好吧。」媘蜜因為我們奔跑和她的惱怒,噴氣地氣喘噓噓,放開我的手將頭髮從她的臉上撥開,撥到耳後:「明顯的是:她在說謊。」
「關於?」
「她不是ABB的新領袖。」
「什麼?那誰是?」戰慄問。
「你和我知道的差不了多少。她不將自己視為掌權者,就算她再享受那個位置也是。她是在假裝。」
大地隆隆低吟,我們轉頭望向身後,看到了戰慄用黑暗掩護我們的撤退路線之處,破瓦殘礫飛了出來。
我們只因為看見一發火箭從黑暗中炸出的瓦礫。毫無必要地,躲了開來,而那枚火箭在我們頭上三呎畫出弧線飛過,穿過巷子,筆直地往那個立體成像炸彈所在的地點飛去。
火箭和炸彈爆炸時,我們接二連三地掩住自己的頭部。第一個爆炸連我們的頭髮都沒有弄亂,可是我們距離它不到一百呎。不過,第二波爆炸,是我體驗過最強烈的冰冷,衝擊掃過我們。甚至穿過我的假面服,也能感受到那個冰爆風。
我們一睜開眼睛,面前成了副奇景。第二個爆炸一瞬凍結了第一個仍在爆炸的炸彈,大概就是它吸收了爆風的衝擊。煙霧、碎屑和塵土全都被冰凍成一座冰塔,很可能有兩層樓高,它的冰刺和冰霜指向我們前進的方向和上方。大部分都被平均分佈在儲藏設施裡的路燈桿照耀著。它已經開始慢慢崩塌--沈重的殘骸讓支撐著的冰塊裂開,落下,撞進如紙般薄的冰霜網格結構。
眼能見之處,那層冰霜覆蓋了整個地面和每面面向爆炸點的牆壁。這蓋住了我們。冰柱小巧細緻得像眼睫毛從我暴露出來的假面裝上冒出來。在戰慄的黑煙凍結的地方甚至還有扭曲、彎曲的冰塊。
「大家都還好?」戰慄問。他用他的身體護住了媘蜜,冰片在他們站起身時滑下身體。當他看到我在看他時,解釋道:「媘蜜的假面裝有皮膚露出來,比我們任何人都還要多。如果她徹底在爆炸下……」
「別。」我回答:「別擔心。這樣很聰明。但我們該走了。」
我們開始奔跑。我們周圍,有著飄下的細小冰塊結晶,於光中閃亮。
媘蜜繼續搬出關於爆彈的情報:「謊言二號?她在那些她放在她的人腦子裡的炸彈的引爆方式上撒了小謊。她說她能以思想引爆,但她沒在頭上穿戴任何外部硬體,而且她也不會讓其他某個人在自己身上動手術。她是個超級控制狂,對自己的腦子太驕傲了。」
「但你不知道她怎樣讓那些炸彈爆炸?」我猜測道。
「我正好知道她引爆的方式。是腳指戒。」
「腳指戒。」戰慄說,就算他的嗓音扭曲了,語調中的不信任也非常明顯。
「她腳大拇指和食指上有個戒指。在她將一隻腳指和另一隻交叉時,兩枚戒指錶面接觸就會發出訊號。她再用內建於護目鏡的系統選擇目標。這不看起來像是她再做任何事情,這大概也是她想達成的效果。表現出形象。」
「能知道很好。」戰慄說:「可是現在這對我們沒有幫助。她的弱點是什麼?」
我們身後有道爆炸撞擊聲。那塊區域閃亮了一會兒,但沒打中近到值得擔心的距離。
「自戀型人格障礙。誇大狂。她所花費的一生比她周遭所有人還更聰明,即使在她有超能力之前也是如此。不斷被讚美、嬌慣。但是她幾乎聽過批評,大概也從來沒被嗆過,而這就是在她的自尊膨脹到神經質等級的一個巨大因素。她八成提早從高中畢業。我敢賭她的觸發事件和這有關。在求職時被人無視,或某個人真的對她大吼大叫,然後她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現實。」
我想到某些事,補充道:「她用她的能力做的第一件事,在她來布拉克頓灣前唯一的事,是挾持一所大學。也許她有些爛成績,在一堂課裡被當掉或沒得到一個教學助理的位置。震動她的自我形象到她足夠抓狂。」
「大家,我要某些我們能用的東西!」戰慄低吼著。
「那個人格障礙。」媘蜜說:「就算是我們這邊的小小勝利,也會從她那獲得巨大反應。自尊方面,她有顆玻璃心。很難說我們贏一次,會不會表示她會發狂然後把所有東西都炸了,或是她就只是被粉碎,但我保證她不會接受得很好。」
戰慄點頭,開始說話,但跌了一跤。我盡我所能阻止他整個人摔倒,但是他大概有我體重的一倍半重。他重新找回平衡,咆哮一聲,然後說:「我們要怎麼贏?或是怎麼避免輸掉?她有什麼計畫是我們不知道的?」
「那個護目鏡,她能看見熱徵像。這就是她一直找到我們的方法。那個冰彈算是我們因禍得福,因為這大概隱藏我們一些熱源特徵。她一定有個理由使用那個冰彈。呃。她的槍是以她的指紋鎖著,所以你沒辦法撿起她的榴彈發射器然後用來對付她。」
「還有什麼?」
「這是我現在想到的所有事了。如果你有想到計畫,最好快點執行。我認為她是坐上那台吉普車來追我們。」
「那們我們分頭走。」戰慄哼了一聲:「我在那個黑洞爆炸時,踹開門幹壞了腳踝。之後跑這麼多步把它搞得更他媽的糟糕了。我要留在這,看看我能做什麼。」
「幹三小?」我大口呼吸:「不行。」
「我會為你們爭取時間。你們先走。現在走!」
「我沒可能走的。」我說,但他停了下來,轉過身。我也,試著停下來,但是媘蜜抓住了我的手將我拖在她身後。我喊著:「戰慄!別做傻事啊!」
他沒有回答我,轉身對著最靠近他的光芒打出陣陣黑暗,將整條巷子黯淡。他緩緩地,朝向我們反方向走,護著他那條腿。
隨著一道尖聲呼嘯和響亮的爆裂聲,另一發火箭撞上冰塔。整座塔像一座巨大個紙牌屋一樣倒塌,聽起來就像十萬扇窗戶碎裂一樣。即使有這樣的雜音,我依然聽見輪胎的尖銳摩擦聲。我看到吉普車模糊的外型穿過一團團從倒塌的冰塔翻滾遠去的白雪和冰霜之中。
戰慄沒在吉普車高速接近時撤退,沒有跑開來。他以他那扭曲的嗓音,使盡肺部所有空氣吼道:「來啊!」
「戰慄!」我喊著,但他沒有反應。「幹!」
沒有蟲子。數量還是太少。我們剛才一直在移動,所以我的蟲子沒有一個能聚集的地方,而且不管怎麼說,這地方的蟲子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很糟糕。我怎麼能這麼天殺地愚蠢?我應該總是準備好才對,而現在在他最需要的時候,我卻沒處於幫忙一個朋友和隊友的狀態,就因為我猜想自己有蟲子能可以用。
吉普車上只有三個人,在後座站著的是非常顯眼的爆彈,手裡拿著榴彈發射器。那個坐在副駕駛椅上的混混一手拿著一隻手槍,而駕駛則一手握著方向盤,另一手拿了把槍。
戰慄在駕駛踩住油門時絲毫動搖。他是在和一輛加速的車子比誰是膽小鬼?
「來啊!」戰慄,又一次吼道。
「別光是看著!」媘蜜扯了下我的手臂,把我拉到角落:「我們現在就得走不然就沒意義了!」
這很蠢,但我抵抗了她的力道,抓著貨櫃邊緣確保自己至少留得夠久能看到什麼事發生在戰慄身上。看看也許他是否安好。
這些希望迅速消逝。那輛車撞進黑暗環繞的人形,快到讓我確定他不會從那樣一個衝擊後安然離開。
車輪發出又長又尖的噪音,吉普車轉向停住時滑過了半轉彎。爆彈把自己拉起到一個站姿,在她看向四周時握住圓弧欄杆,大概在找我們。
「來啦!」媘蜜壓低聲音催促我:「我們走啦!」
我在她之前瞭解了。「那輛車沒有損傷。」
在媘蜜停下來確認我所說的話時,她不再繼續猛扯我的手臂。車窗沒有破,車蓋沒有凹陷,保險桿也沒有塌陷。
一朵黑暗從巷子一側的陰影中綻放,吞沒吉普車和那三個乘客。
兩秒之後,吉普車轟鳴衝出黑暗,如魚擺尾似地在凍滑地面上辛苦地試著取得掌控。那個駕駛轉向朝我們來,同時,爆彈將她的榴彈發射器上膛,她著注意力放在那朵剛才離開的黑雲。那個坐在副駕座位上的人……不見了。
爆彈將榴彈發射器瞄準向那團黑暗。
「肏,戰慄欠我一次。」攝政低聲抱怨著。他放開肩膀,朝向吉普車舉起手,然後朝另一邊揮動。就在他這麼做時,放聲尖叫,聽起來十分原始、粗野。
那個駕駛的手和攝政的手動作一樣,失去控制地揮到一旁,吉普車轉了向,打滑,旋轉,將爆彈和五、六盒裡的爆炸物甩到巷子的地板上。車子撞上一個貨櫃,過程中一半撞進了一扇門,狂旋突然迎來的停止讓一個安全器囊爆開,那個駕駛卻在車子後面跛腳走著。
幾乎在吉普車停下來時,攝政開始正要倒在地上,失去意識。我在半空中抓住他防止他撞傷,把他輕輕放下以免傷及他的頭。我看向媘蜜:「回火?」
「不是,但很接近。」媘蜜說:「在回火之後,他得要讓超能力休息。這就像用斷掉的手揍人一樣。他之後會痠痛,大概也會一陣子用不了能力,但他會恢復的。」
「很好。」我說,凝視著那個場面。車子撞壞了,凍結的街道覆蓋著手榴彈和金屬罐,爆彈仍躺在這之間。戰慄從那朵黑暗中一跛一跛地走出來,手裡拿著副駕駛的槍。
「戰慄!」我喊了出來。我跑向他,擁抱住他。我的放鬆感是如此強烈,甚至都沒感覺到尷尬。
「嘿呦。」他的聲音迴盪著:「我很好。只是佯攻。在沒有光線時。很難分辨是我,或者是一團約略看起來像是個人的黑影,對吧?騙到她了。」
「騙到我了。我幹他媽的差點嚇出屎來。」我回應他:「你這混漲。」
「知道妳這麼在意也很不錯啊。」他笑了下,像是拍狗一樣拍了我的頭:「來吧。我們得把這瘋子綁起來,把她帶走好讓我們能拷問出母狗和錢的去處。也許能瞭解ABB的情況。」
我在面具之下微笑道:「聽起來是個……」
我沒能說完話。所有東西都變白色,我每一吋皮膚都綻放起一道道烙印似的劇痛,連我感受過最糟糕的痛苦也無可比擬。
自從我們痛揍一頓上人和黑客文後,一次又一次驚險逃脫。被暴民圍困、衝鋒,被槍指著,從一個小型黑洞逃脫,差點像是在琥珀中的昆蟲一樣被時間凍結,還有無數場爆炸。我們千鈞一髮地從每個威脅中逃跑,我們也瞭解這同時全部只要有一發瞄準好的攻擊,我們又完了,死了,退役了。
全部就只要被打中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