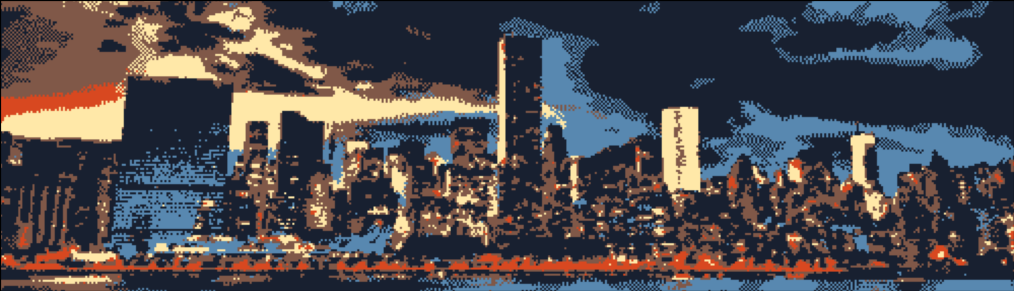 x
x
【本篇翻譯由Xavia大大提供】
『走!』那位士兵用土耳其語吼道。他把槍用力地頂在她的肩胛骨之間。他的身高是她的兩倍,也比她強壯許多,因此就算他沒帶武器也不能有攻擊或抵抗。她跌跌撞撞地走過草叢和樹木,樹枝刮擦著她的前臂和臉。
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的前面,哈娜告訴自己。她向前邁著每一步,腳就像鉛塊一樣重。樹上的針頭和灌木叢划過她的皮膚。就連樹枝也很粗糙,甚至是棘手的,它們鈎住她的衣服和襪子,插穿布料來割開她的皮膚和刺穿她赤裸裸的雙脚。
『走快一點!』那位士兵威脅著。他説了些更加長和複雜的句子,但是哈娜的土耳其語并沒有好到足以聽懂那些話。她回頭看到那位站在入口處的男人。他在那一班被士兵圍繞著的孩子面前揮舞著步槍,背後的意思十分明確。如果她走得不夠快,就有人要付出代價。
這七年讓她的村子得到了虛假的信心,他們以爲自己住的夠遠,在山谷和樹林之間隱蔽著,讓他們可以逃脫這場戰役中的交火。那個幻想在幾個小時前就破滅了。
她當時藏在房子旁邊的地窖裡。她聽到那些尖叫和槍聲。考慮到她村里的人只有幾支還能運作的槍,那是太多的槍聲。對於收入只有來自院子裏種的和打獵抓到的人來説,槍支和子彈是十分昂貴的,而去最近的城市買這些東西的路也是十分艱險的。他們只能擁有算是剩下來的,或是那些被游擊戰士們從敵人手中奪走,并在他們經過村莊時,留下來和用物資和醫療交換來的少量武器。而那些擁有槍支的人又缺乏使用它們的技術和訓練。保護平民免受襲擊,阻止敵人走這麼遠應該是那些戰士們的工作。
她急忙向前邁出了一步,一根小樹枝被踩斷,她退縮了一下。最小的嗚咽聲從她的嘴中逸出。
當敵人在地窖里找到她,并把她拖到村裏的另外九位小孩子當中,她知道自己的父母已經死,或是快死了。士兵們帶著他們穿過村莊走進樹林,她直直盯著地上的泥土,淚水在她的臉上流下,不願意看到那些血攤、尸體,在她的家院裏散落一地。她一生中每天都會見面的人。
她的雙眼仔細觀察著樹林的地面,但她并不知道要找什麽。凸起的泥土?繩索?密密麻麻的棕色針頭?她往前踏出另一步,等待著災難發生。而當災難沒來之後,她再次踏出一步,便停了下來。
在不久之前,她才從遠處看著科文,那個喜歡給她取綽號的胖男孩往前走一步,他的腳便陷進了一個坑。他尖叫起來,當哈娜和其他孩子們衝上前去試圖將他抬出來時,他們只增加了他喊叫的聲量和掙扎的猛力。在他們身後的土耳其士兵靜靜地註視之下,哈娜和其他人用他們的雙手從土地中挖出堅硬的岩石,露出插在坑裏側面上的木樁。每根都以往下傾斜的角度安置在土裏,有一些在底部刺穿他的腳。那柔順的木頭彎曲得足以讓腿落入洞中,但是企圖抬起科文的舉動只會將他的腿和腳往等待著的木刺上拉。
她知道,那是被她村子里的獵人或游擊戰士們爲了保護他們的家園而放置的陷阱之一。它們到處都是,遍布整個樹林,圍繞著她的村莊,靠近道路和其他的重要場所。她聽過一位戰士向她的父親描述其中的這一個陷阱。她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她不准在樹林裏玩耍,就是爲了這個原因,她要是有任何理由要進入樹林,便必須要一位成人陪同。直到她看到對科文發生的事,她才意識到那些警告背後的現實。
他們已經嘗試了很長時間把那位男孩的腳釋放,隨著發現越來越多的他那條被刺穿的腿,看到那些傷口和流出的血量,他們明白他無法再走多遠。他們知道這是沒有希望的,但科文是和他們一起上過學的人。他們每天都見到過的人。
一位士兵用對著科文腦袋的一發子彈了結了他們的努力,這讓科文成爲第二個死去的孩子。
哈娜是下一個被選中的。去測試那條路徑。
她緊緊抓住裙子的前部,將布料揉成一團,手上仍然沾滿了污垢和傷口,那是她為使科文脫身而付出的努力。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的前面。她的每一個感官都處在警戒。留意著腳下踩著泥巴的聲音,松針對著衣服的布料刮擦的觸感。當她走進透過松樹滲入的一道光線時,便感到陽光落在皮膚上的溫暖。
她用力地眨一眨眼,清除積在眼裏的淚水。那是多麽的愚蠢。她必須要能看得見。任何綫索。不管是什麽,只要能找出陷阱。哭是她能做最糟糕的事情。
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的前面。
她停了下來。她的腳拒絕再次前進。顫抖著,她環顧四周。
她知道,如果再踏出一步,她就會死。
那并沒有仍何邏輯,沒有理由也沒有綫索。這片土地與森林的其他地方沒有什麼不同。腳下有一片紅棕色的草根,灌木和樹木充滿在她周圍。
但她知道。不管她向左向右還是向前踏步,她都會踩入陷阱。像是抓住科文的那個洞,或者是一個爆炸裝置,就像帶走了阿什蒂的那一個。她至少死的比較快。
從她身後遠處看著她的那位士兵呼喚道,那聲熟悉的『走!』同時是威脅也是命令。
因恐慌而反感,哈娜環顧四周,尋找仍何東西可以告訴她去哪裡,怎麼走。
在那一刻,她知道自己不會馬上死掉。她不能再繼續走,那是不可能的,她的腳就像樹一樣紮根在地上。他們會把另一個小孩折磨致死給她看。然後他們會對著下一個,可能甚至哈娜她自己,直到他們又有一個願意爲他們以最快和危險的方式清除陷阱的小孩。
『快……
她看到一個蒼茫的東西。
那并不是像樹木或甚至山脈那樣的龐大。那樣的龐大遠遠超越了她可以看到或感覺到的。那就像看到比整個地球更大的東西,但還是不夠;這個東西大到無法理解,它往外擴展著。她無法用一個更好的詞語來形容她所感知到的東西。它猶如有著許多鏡像,但是每個圖像都存在於同一個位置,有些圖像以不同的方式移動,而有時,非常難得地,有一個圖像與其他圖像沒有碰到過的地方接觸。每個圖像都與其他圖像一樣真實和具體。這使它大到就算她是一百歲的學者或哲學家並獲得了世界上最好的圖書館,也無法形容。
而且它還活著。是有生命的東西。
她不需要想就知道,那個生魂的每一個迴響和衍生就像她的手或鼻子對她來説一樣是相連著整體的一部分。每一個部分都被這個帶有生命的生魂意識到,控制和有意圖地移動。就好像它同時擴展並在所有的可能性當中存在著。
它快要死了,她心想。那個生物最外層的衍生隨著它在沒有空氣的空虛中蠕動而逐漸剝落并破散成碎片,那并不能説是移動,而是不斷地調整每一個自我在每一個迴聲中的存在,縮起一邊并伸展另一邊,以遠遠超越光的速度離開。而隨著它的身後,塵跡和碎片就像種子在風中不停地從一朵不可思議的大的黃花地丁,或蒲公英,一樣從生魂上脫落。那種子的數量比整個地球上所有的灰塵污垢都還要多。
而那其中的一個碎片似乎擴展著,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直到那是她唯一能看見的東西,彷彿月亮正在墜落,與大地相撞。直接落在她的身上。
……走!』士兵毫無停頓地説完那句話。
哈娜感到無比的暈眩,她仍在森林裡,手掌上佈滿刺痛的傷口,雙脚因走過的路而毫無力氣。她的心臟猛烈地跳動,她幾乎能在嘴裏嘗到恐懼,那是跟膽汁一樣的苦涩。
那些記憶正在消失。甚至有發生過嗎?儘管她努力地保留它們,那些記憶繼續躲避著她。那就像早上一起來就忘記的夢,但是又模糊到就連她有做過那種夢的想法也逃脫了她的腦海。
那位士兵對著他的隊友大聲喊一些她聽不懂的句子。哈娜把注意力從那些記憶的碎片中拔開。現在,這裏,才是最要緊的。她要么向前走,并邁向她的死亡,要麼站在一旁,看著其他人為了她的怯懦而被殺掉。只有一點那些事情已經發生的想法,她便仿佛被從癱瘓中喚醒。也許她應該踏出那一步。
她抬起了一隻脚……
然後停了下來。有東西擋在她的面前。一個殘影懸掛在胸前,劈啪作響,猛烈地閃耀著。她讓自己的腳落回之前的位置,凝視著那像萬花筒一般不斷變換的黑色和綠色。
她觸碰著那團光,感覺到重量落在了手掌上。她的手自然地合上,并感覺到一股熱力。感覺就像是在撫摸一隻友善的小狗。考慮到她自己正在看到的東西,那是一個奇怪的想法。
一把槍,光滑的灰色鋼鐵。有一點熟悉的感覺。是她看到游擊戰士們攜帶著最小的手槍一樣。
我不能用這個。她的腦裏浮現一個冰冷的想法。我一開槍,他們就會把其他人殺死。
槍閃爍著,變回綠色和黑色的殘影,然後化成了新的形狀。也是她見過的。其中一爲戰士有和哈娜聊過,并給她看一本英文的機槍雜誌,都是爲了討好她的姐姐。那是一把跟之前相近的手槍,但是在槍口裝了一根金屬管子,使槍的長度多出一倍。她知道,那根管子讓槍變得更安靜。
其餘的孩子和士兵在遠處的後面。那仍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
『走!』她身後的士兵叫道。『再不走就-』
她轉過身,雙手握著手槍。她用了一秒鐘對準槍口,而那位士兵的震驚使她剛好有足夠的時間扣動扳機。
漢娜猛然地睜開了眼睛。
這就是爲什麽我不喜歡睡覺。
當她從床上起身走到浴室時,她發現自己仍然穿著假面服。至少她有想到結下圍巾,這樣休息時至少不會被勒到。
她是唯一一個還記得那件事的。其他人都早已忘記那個不可能的龐大存在,那也是如果他們有瞥到一點的話。她并不確定。要是他們真的有看見,也馬上會在能有説出口的想法之前就忘光了。就像她原本一樣。
但是她記住了。她觸碰著掛在她腰上的戰術小刀,就像是要確認它還在那裏。她對賦予自己的這個能力保持戒心,它改變了她的心理,塑造她的人格。她最憤怒的部分、最幼稚的部分、她夢見的部分,以及被遺忘的部分。她能想象,插在她腰上的刀爲了她而昏睡,爲了她而發夢。她有時能過一整年而一次都不用停下來把頭放在枕頭上。
當她閉上眼睛讓自己昏睡時,是因為那是她認爲自己應該做的事情,而不是需要做的事情。盡管如此,她也從來沒有做過夢。反而,她會回想,她的大腦非常詳細地重播過去的事件。而因爲某種運氣關係,那表示她也記著那個生魂,還記得把它遺忘,那是十分矛盾的。
而她永遠也不會告訴任何人。
她把那班用村裏其他小孩當人質的士兵都殺了。幹掉第一個之後,她假裝恐懼,讓他們以爲游擊隊戰士在樹林裡。然後,她等待著他們忙於看著樹林的那一刻,用步槍對著其餘的人掃射。她并沒有為此感到難過,也沒有因爲其中一個孩子--比海爾--被流彈擊中而失眠。
她爲那些死亡感到後悔,那是不用説的,但她并沒有爲之感到愧疚。他們十位當中,有七位能活下來,都是因爲了她與她的天賦。他們回到了村子里,把尸體都移開,并盡量保存著糧食直到游擊戰士們的歸來。
哈娜讓其他小孩發誓,不讓別人得知她的天賦。她知道要是那些游擊戰士聽到的話,一定會企圖招募她,利用她。不管她獲得的這個能力是什麽,她并不認爲它的目的是在那上面。
當戰士們回來的時候,他們見到這班孩子的處境,并決定把他們送走。戰士們把他們帶到城市里,而那裏的一位男人確保了哈娜和其他小孩都能坐上通往英國的船,那是許多其他難民都去的地方。他們被分散,而其他的孩子們一個接著一個地被送去不同的孤兒和其他陷入困境的兒童的收養院。哈娜排在之後,幾乎最後一個,她被送到飛機上去她的新家。而她也在這裏遇上了麻煩。她傳過了一道拱門--後來才知道是一個金屬探測器--并響起了警鈴。保安們便發現了她無法抛棄或遺落的那把武器,并把哈娜抓去了另一個地方。她被問了許多問題。她被帶到了厠所,在重新進入審訊室之前徹底地搜過身體,然而他們又在她身上發現半個小時前被拿走的同一把槍。
在那之後,其餘的一切都發生得非常快。是一個穿著軍裝的美國人拯救了她。他把哈娜帶到美國,確保她被那裏的一個家庭收養。當最初的三個監護者隊成立時,她就被招募入伍。當她第一次穿假面服上場的時候,她幾乎只懂了一百個英語單詞、數字和字母。
漢娜彎過水槽洗臉。她找到了牙刷,并清潔了牙齒,然後用牙線,再刮一刮舌頭。沒有用睡眠的節奏斷開每天的連續性,是很容易忘記這些事情的。至少多做比忘記做更好。她漱了漱口,然後露出牙齒看一看牙醫給她上的牙冠。那潔白的牙齒有著完美的形狀。但并不算是她的。
在她放下漱口杯不久之後,她的武器便偷偷地跑到她的手上,變成一把和它當初的形態差不多的手槍。她沿著扳機用手指把槍轉了幾下才把它收在槍套裏并踏出浴室。她走到窗前俯視著對岸的城市。打在捍衛者總部周圍防禦力場上的光因折射而微妙地偏移顔色,就像一台設置差的電視,使畫面過度的鮮艷。
就算她重來都不會做夢,美國對她來説還是虛假、夢幻的。這裏離她的出生地是那麽得遠,那麽的不同。這裏沒有戰爭,并不算有,但是人們依然找到這麽多可以抱怨的東西。無論是工作、愛情、醫療或是缺乏最新型的智能手機。這些埋怨往往都比她村裏的任何人對哀悼親人或是外人對他們的冷血屠殺都還要帶著更多的激動和憤怒。當她聽到她的朋友和同事們如此的抱怨,她只是點了點頭,并説一些簡單的同情話。
路光、便利、豐衣足食、電視、跑車、牙冠、巧克力……那全都列不完,而她試過了許久才開始適應它們,但一切的轉變又是如此的快,當她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住了,就會有一些新的、她應該知道或理解的東西。
當她的收養父母告訴她應該改用更加美式的「漢娜」稱呼自己時,她毫無怨言地接受了。她也同意讓他們把自己的親生父母給她的性改成他們的。與她所見過和所做過的相比,那是如此得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得埋怨。每個人都稱讚她在學校和訓練中多麼盡職。她從來都不會放棄。有何必要呢?與她在那片森林裏度過的時光相比,這算不了什麼。
還是很難相信她在夢裏見到的那些事發生在二十六年前。
那從來沒有感覺完全是真的。不止一次地,她會讓自己開始相信她已經死了,她在踩下那一步之後就從此都沒有活著走出那片森林。早在她成為英雄的那幾年,她讓自己以這種方式思考時,她會犯出許多錯誤,使自己陷入太多的危險。現在,每當她感覺自己會開始產生這些想法,她就會嘗試著睡覺。她睡眠中的記憶是完美的,毫無干擾,幾乎比現實還要生動,那也是爲什麽她并不會經常睡。那是十分諷刺的,她往往必須去睡,是爲了能讓她保持在現實當中。
她漸漸地愛上了這個國家。爲了它所象徵的而真正地愛上了它。她能把國旗放在她的服裝上也是她爭奪而來的權利。美國不是完美的,但是沒有一個被人類觸碰過的東西是。這裏有著貪婪、腐敗、自私、卑微,和仇恨。但是也有許多好的東西。自由、思想、選擇、希望,以及在這裏的人只要願意為之努力,就能成爲任何他們想要成爲的可能性。當她接受了自己的這個新的國家之後,她讓自己結交許多的朋友,甚至男朋友,也讓自己與父母和他們的教堂更加親近。當她開始上大學時,她的口音已經幾乎完全消失了,而她也對一切足夠地了解到至少能夠假裝聽懂別人談論流行文化,音樂和電視時在說什麼。
人們很容易產生偏見,她知道,所以她永遠也不會告訴別人在獲得她的天賦的那一刻說發生的事。
甚至在其他信徒中,如果她說她見過上帝或祂的一位戰士天使,說祂給予了她能解救自己的能力,并指出祂們已經超越了人類的理解範圍,她也會遭到懷疑和輕蔑。其他人會提供不同的見解,說祂也把這些天賦送給了壞人,他們會望向科學的一面尋求答案。也許她的一小部分懷疑這些假設的人是對的。儘管如此,與那些不確定性相比,她更偏向自己的信仰。要不就會表示她所見到的那個東西不是良性的,它可能是帶有惡意的,甚至更糟的是,它對自己給人類存在的影響完全沒有概念?猶如蚋群當中的大象?那并不是一個使人放心的想法。
她瞄了一眼時鐘,早上六點三十分。她把脖子和下巴鬆散地用旗子印花的圍巾裹住,然後離開了房間。她的能力成爲一把吊在她肩膀上的步槍,隨著她的步伐在她的背後輕盈地擺動著。她爬過一層樓梯并走到走廊的盡頭。
她聽到了一個男人的聲音,和一個女人的。她便停在打開了的入口并敲了敲門。
「什麽事?」兵器大師喊出。
「我打斷了什麽嗎?」
「沒有。進來吧,」他回答道。
她走進房間。那裏似乎落在一個工坊和辦公室之間。兩副備用盔甲立在房間的一邊,每件都有小小的功能差異。一排戰戟挂在兵器大師身後的架子上,一把破成了碎片。架上空出了一個位置,兵器大師有一把放在他的面前。
「你又工作到忘記時間啦,科林?」漢娜問道,那個答案是很顯然的。
他皺了皺眉,伸手在電腦上按下一鍵。他看到時間,并咕噥道,「可惡。」
「早安,民軍小姐,」一個女人的聲音從電腦傳出。
漢娜意外地眨了眨眼,「理龍,抱歉,我沒注意到你在這裏。早安。」
「你起得真早,」理龍評論道。「而且從我在網上看到,你昨天也在外面待得挺晚。是睡不着嗎?」
「我不需要睡覺,」漢娜承認道。「自從我得到能力之後就幾乎完全不用睡。」
「是嗎?我也一樣。」
科林一邊靠後椅背一邊用手腕揉著眼請,「我可是願意犧牲一條腿來學那招。」
漢娜點頭回應。有別人跟她一樣?她對著電腦熒幕問,「那你記得嗎?」
「抱歉?我不懂你的意思,」理龍回答道。
「沒事。」漢娜知道要是理龍真的記得,那她的回答就會有所不同。理龍那麽聰明是不會錯過那個關聯的。
「我們剛在聊閑話,」科林說。他對面前的戰戟示意。「用工匠玩意兒拖延一些工作。我感覺這次的實驗是個成功。」
「哦?」
兵器大師起了身,用一隻手握著戰戟。他按了手把上的一個按鈕,而刀刃則變得模糊起來。連揮動的力道都沒有,他讓較重的頂端降落在一個空出來的不銹鋼假人身上,那應該是用來展示他的備用盔甲。刀刃碰到假人的地方冒出一團粉末,并且毫無阻力地穿過。假人被切下的部分散落一地。
「不錯嘛,」她告訴他。
他再按一個按鈕,刀刃周圍的模糊消失在鋼色的煙霧中,剩下的則是原本的戟頭。
「唯一的問題是它容易受力場,火焰和其他強烈能量的影響,而且裝置也在頂端占用太多空間。就算用我的能力,也很可能意味著我不得不抛棄一些我已經習慣的設備。」
「我相信你能找到解決辦法,」漢娜告訴他。假裝著嚴厲的態度,她用一隻手撐著腰部,「好了,別再讓我分心了。你倆在拖延的東西是什麽?」
科林摸摸他的那頭棕色短髮,并嘆了口氣。「對噢。在這事上,你跟我一樣有發言權。」
他走回辦公桌,并陷到座位上。他把雙腳交叉立在桌角上,并踢開一把螺絲起子和鉗子。他順著另一邊拿起一曡文件夾,并讓它砸在桌上。
「皮戈特在考慮了最近的事件後,決定要采取一些行動。監護者和捍衛者兩邊的人員都會被整體調動。」
漢娜緊張地問,「情況有多糟?」
聳著肩,科林説道,「就監護者而言,我們會失去神盾。皮戈特和反應部隊都想看看他帶領另一個小隊的表現,而那小子的父母也很贊同。他比較年輕,應該會在監護者裏呆久一點。」
「很遺憾。那我們會收到誰?」
「是個交換。我們會得到鐵焊,從波斯頓分隊來的。」
「我不認識他,」漢娜承認道。
「他是個記錄良好的好孩子,」理龍透過電腦加入,「亞鐵生理,能透過皮膚吸收金屬。强壯、堅硬,整體成績也不錯,在戰術模擬中的得分很高。他挺討人喜歡,網上掃描顯示對他的反饋高於平均,考慮到他是一個案例五十三,那是滿出人意料的。」
「他有那個刺青?」漢娜問道。
「印記被烙在他的脚根上,不算刺青,但是沒錯。」
漢娜點了點頭。「還有呢?」
科林皺著眉頭,「我們要再這邊的監護者隊裏再選兩個人調去附近其他大城市裏的分隊。我想到勝利小子,第二個我還沒決定。」
「恫巖?」
「太新了。有可能説服皮戈特,但我懷疑她會覺得那會讓我們看起來很差勁,把新人推給別人。」
「嗯。豪俠也不能離開這裏。太多物流上的問題,」漢娜瞥了一眼電腦。她不能講太多。
「沒事,你能隨便說,」科林提到,「理龍要麽一早就看過這些記錄,要麽現在就在看。」
「豪俠在本地有一些責任,並且也有望開始幫助他父親的管理本地企業,」理龍說,證實科林説的話,「民軍小姐説得對,他是本地的支柱。而且他的女朋友也在這裏。」
漢娜點點頭,「也很難放棄遠璟和吊擋鐘。那兩位是我們的主力,而且因爲他們在那次炸彈事件裏的付出也提高了在本地的名氣。暗影潛行者?」
科林搖著頭,「把暗影潛行者交給另外一隊會比把恫巖交給他們更麻煩,她的紀律有問題。」
「還有問題?」她問道。兵器大師點了點頭。
漢娜皺起眉頭,「好吧。你就這麽做。先提出暗影潛行者和勝利小子。假如皮戈特反對暗影潛行者,那你應該說暗影潛行者可能需要改變 一下環境,那之後皮戈特就會比較難拒絕恫巖了。」
科林摸了摸他的鬍鬚在下巴的邊緣留下痕跡,并點了點頭。
「要是她兩個都不認同的話,而你要確保她拒絕得很難堪,那還是可以提議吊擋鐘。反正他這個夏天就要畢業了,而我也認爲他在這裡有足夠的朋友和聯繫人,他可能會想在十八歲時申請回到布拉克頓灣加入我們的捍衛者隊。那是對我們來說最好的情況,再説波斯頓和紐約都不需要更多的假面。」
科林嘆了口氣,「你在這方面永遠都會比我更好。」
漢娜不確定她應該如何回應。科林有他的長處,但他是對的。
他繼續說,「恭喜啊。」他把另一個文件夾遞給她。
「什麽?」她接過來并打開了它。
「根據皮戈特和其餘的監督,我們的分隊也會有調動。你被升職了。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這棟大樓和這個分隊都會被轉移到你的管理之下。」
她站在那裏,驚訝地翻閱著文件夾。「你會去哪裏?」
「芝加哥。」
漢娜開心地笑了,「芝加哥耶!那太棒了!你會有更大的城市,更大的團隊!那梅爾丁會被調到哪裏?」
「他會留在芝加哥。」
漢娜搖著頭,「但是……」她停住了嘴。
柯林臉上的苦澀表情足以說明一切。
「我很抱歉,」她說。
「是官務上的東西,」科林往後一靠,并説道,「我擅長於此。如果您不介意我吹牛的話,我在這方面比大多數人都要拿手。我帶到桌上的所有東西,都是我拼著命工作而得來的。但是當涉及到跟人打交道,管理人員,在官僚機構中尋路時……那并不是我擅長的,永遠都不會是。因此,我被降職了,而且我應該從此都不要再指望有帶領團隊的機會了。」
「對不起。我知道你有多想要……」
「沒關係,」他説,但他語氣的刻板表示那明顯不是沒關係。他轉過頭敲了敲鍵盤。在房間的黑暗中,他的臉短暫地反射了屏幕的藍光。他緊皺著眉頭。
「理龍。你給我的那個軟件,用來預測S級威脅的,還記得嗎?我做了一點修改,想看看可不可以抓住一些重點的地方,我現在同時有幾十個在進行。其中一個叫HS203,我需要你直接看一看這個。我把它放在了一些滿強的安全措施後面,但是如果你等一下,我可以……」
「我已經在看了,」理龍插著嘴,「我明白你在做什麽。把我的資料和氣候變化連起來。我想我看到了。」
漢娜繞過桌子并從科林身後看著熒幕。顯示著東海岸的地圖上疊加了彩虹色的雲。「我看不懂這有什麽意義。」
「這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是真正隨機的,」科林解釋道,他的語調緊凑,「只要你研究得夠深入,任何數據最終都會出現規律。理龍開始爲那些終結召喚者建立一種預警系統,以了解我們是否可以預測他們下一步將要襲擊的地方,并進行一定程度的準備。我們知道他們遵循著某種規則,但是我們不知道爲什麽。它們每次只來一個,相隔數月,很少在短時間內再次襲擊同一個區域。我們知道他們被吸引到他們認為最爲脆弱的、認為他們能在那裏造成最大傷害的地區。核能發電廠、鳥籠、最近遭受自然災害的地方……」
他按了按鼠標,而地圖則放大了海岸上的一部分。
「……或是有持續衝突的地方,」漢娜替他説完,并瞪大了眼睛。「ABB,還有八十八帝國,在這裏的打鬥?他們要來這裏?現在? 」
科林并不需要回應。「理龍?布拉克頓灣落在了預測的範圍内,而這座城市也的確在敏感或負面媒體量度上獲得足夠高分的地區列表中。加上我的數據,溫度、氣壓的突然微度移動之間的相關性還有……」
「數據是好的。」理龍爲了掩蓋最能夠透露她身份的的細節而被數據化的聲音裏絲毫沒有疑惑。
「好到可以去請求支援了?」
「是的。」
科林迅速地行動,轉過他的椅子到一個小控制台。他打開了一個玻璃板并撥了後面的開關。空襲警報器立即開始不祥的吟呻。
「理龍,我會聯絡皮戈特和捍衛者部隊。你去召集所有其他重要的人。你知道我們最需要什麽。」
「已經在做了。」
他面向著漢娜,他們的目光短暫相遇。在那一刻,他們之間交流了許多,但她不確定自己是否喜歡在他眼中所見到的東西。
那是一絲希望?
「民軍小姐。召集本地的勢力。我們也需要一個可以會和的地方。」
她嚥下自己的擔憂。「收到!」
#兵器大師 #理龍 #民軍小姐
ns18.219.206.240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