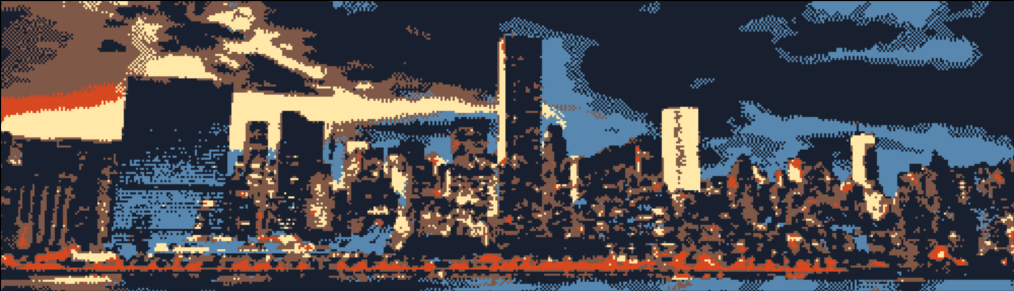 x
x
我發現自己面對著十幾個槍手,三十多人拿著臨時湊合著的武器,和一位有炸彈迷戀癖的瘋狂科學家,令我非常、非常感激母狗在隊上的位置。
「這些全部。」媘蜜非常小心翼翼地說:「是妳在玩弄我們。這就是為什麼妳沒在最開始時叫妳的人對我們開槍。」
「妳說得非常正確。」爆彈的面具可能將她的嗓音轉變為,大概像喉嚨沙啞的機器人小機【艾西莫夫《機器人短篇集》的典故】,可是我總有她嘗試以肢體語言來補充聲音的不足的印象。她對媘蜜晃了晃手指彷彿在責罵一隻狗。「但我認為妳--特別是妳--應該閉起嘴巴。兄弟們?」
她將手歇在一個站在她的吉普車前,雙手握著把手槍的ABB成員頭上。他在她碰到他時抖了一下。「如果那個金髮再張開她的嘴巴一次,就對他們全部人開火。我不在意其他人有什麼話要說,但她要保持安靜。」
她的士兵們調整他們握住槍的手姿,不只一人,特別將他們的槍管轉向指著媘蜜。我瞥了眼媘蜜,我看到她的雙眼瞇了起來,她的雙唇緊緊堅硬抿成一條線。
「好啦。」爆彈直起身,將一隻腳放在吉普車的門上,雙手手臂靠在她的膝蓋上,她朝我們傾身。「妳是唯一一個我不理解的人。我不清楚妳的能力。可是看到妳和那個瘦皮猴男孩欺負了我那些沒什麼用的傭兵們,我想自己會打安全牌,讓妳安靜點。也許是某種次音速東西,在妳說話時轉變情感,也許是其他別的。我不知。但妳閉嘴。瞭?」
我眼角餘光中,能看到媘蜜十分細微地點了頭。
「現在,我碰到了點小麻煩。」爆彈絲絲聲道,檢查著她的手背。看起來她不只用肢體語言來補足機械化嗓音,她也很喜歡說話。也不是說我想為此抱怨。「你瞧,竜教了很多東西,可是我真正學進心中的教訓是當一個有效的領導者,全在乎恐懼。我們這樣的職涯,人們只會對他們所畏懼的人真心保持忠誠。有足夠的恐懼,他們不再擔心自己的利益,不再想著他們能不能竄奪你的位子,他們也會完完全全奉獻自己來取悅你。或說至少別讓你不爽。」
她從吉普車跳下來,抓住一個更高、頭髮更長的二十幾歲日裔男人的頭髮。把他的頭髮繞在她手指上,她讓他彎下腰來直到他的耳朵就在她面前:「不是這樣嗎?」
那男人含糊回答她後,她就放開他:「但是這能更進一步,不是嗎?瞧,我也許繼承了ABB……」
這幾乎無法察覺,可是我看到媘蜜的臉上有一瞬閃爍的動作。表情的一個轉變或她的頭的移動。
爆彈沒停下來繼續說:「但是我也繼承了竜的敵人。所以你瞧,我就有了個兩難困境。我能對你們做什麼才會說服他們,我值得被避開呢?什麼樣的姿態才會足夠有效,讓他們的人在看見我要來時拔腿就跑呢?」
她轉了一圈,從她其中一個混混手中抓起一把手槍:「給我。」
她然後開始大步走進人群之中。
「這裡蟲不夠多。」我在她的獨白停頓時趁機壓低聲音說道,希望其他人能聽見,也祈禱我沒有太大聲。至少我的面具蓋住了我的臉,將我的嘴唇移動的事實隱藏住:「攝政?」
「沒辦法無力化這麼多把槍。」他低語回應:「我是說,我……」
「你。」爆彈喊了出聲,嚇了我們一跳。不過,她沒對我們放太多注意力。一個穿著私校制服的韓裔美國男性--從位於城市裡最好的部分的,純美高校--在她面前畏畏縮縮。人群慢慢地後退,從他們倆周圍清出幾呎的空間。
「是、是的?」那男孩回答。
「帕克.吉霍,對嗎?之前有拿過槍嗎?」
「沒有。」
「有揍過人嗎?」
「拜託,我從來……沒有。」
「有打過架嗎?我是說真的打架,咬人、抓人,拿靠你最近的東西來當武器?」
「沒、沒有,爆彈。』
「那麼你完美適合我這小小的展示。」爆彈把手槍按進他的雙手中:「射他們之中一個人。」
那男孩像是拿著一隻活著的蠍子似地,用兩隻手拎著那把槍,離他身體一個手臂的距離:「拜託,我做不到。」
「我會讓你輕鬆一點。」爆彈可能試著輕柔地說話或讓自己聽起來安慰人心,但是面具不允許那種變調:「你甚至不需要殺掉他們。你能瞄準個膝蓋骨,一隻手肘,肩膀。懂嗎?等一下喔。」
她將那把槍留在他的手中就站了開來,指向她的一個混混:「把攝影機拿出來開始拍。」
他聽從了命令,從吉普車的側邊拿出一個小型手持攝影機。他弄了幾秒之後將攝影機舉到他的頭上來俯瞰人群,從那個翻開來的側邊螢幕板上確認攝影機的拍攝方向。
「感謝你的等待,帕克.吉霍。」爆彈將她的注意轉到那個拿著槍的男孩身上:「你現在可以射某個人了。」
那個男人用韓語說了些什麼。那可能是個祈禱:「拜託。別這樣。」
「真的?如果你擔心道德的話,他們可是壞人喔。」爆彈將她的頭偏向一側。
他將眼淚閉眼堵住,向上瞪著天空。那把槍從他雙手匡噹一聲掉在地上。
「那就是不行了。可惜。對我來說沒能成為士兵呢。」爆彈踹了他的腹部,用力到讓他四肢張開躺倒。
「不要!不不不!」那個男人仰望著她:「拜託啊!」
爆彈半踏步,半往後跳幾幾呎。圍繞他們的人將那當作遠離他的指示。
她什麼都沒做,什麼都沒說,什麼命令、指示都沒說出來。那有一道聲響,彷彿一支在桌上震動的手機,然後帕克.吉霍在一秒的時間中液化成一攤湯湯水水的髒亂東西。
死了。他就這樣,死了。
在尖叫聲、哭嚎和憤怒的咆哮中很難聽見其他聲音。人群從這場面倉皇後退時,全部人都試著躲在其他人身後,其中一個混混對空直直開槍。所有人都停了下來。震驚的尖叫後,有十分短暫的停頓,那已經足夠長到讓一道聲響把每一個人拉回令人暈眩的沈默。
那聽起就像提起乾樹葉時的沙沙噪音,但是更大聲,有種人造聲響似的舊式電話答錄機風格。全部人眼睛都盯著爆彈。她的音量擴增兩倍,雙手環抱著她的腰。
笑聲。那個聲音是她的笑聲。
她站直起身子時拍了拍她的腿,發出可能是吸氣或輕笑的噪音,但是她的面具沒有將那轉譯成任何能分辨出的聲音--只有鎮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的絲絲聲。她高聲歡喝時身子轉了個半圈:「第十六號耶!我連自己做過那個都忘了!根本完美!比我以為的還要好!」
如果她的工作是嚇唬人,那她就成功了。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我想吐出來,但是必須拿下我的面具才能那樣做,而且我害怕如果自己動了,就會被射中。對槍枝的恐懼已足以無視我那脹大的暈眩感,但是這結果卻是我在顫抖。不只是顫抖,是整個身體讓我難以站直地搖晃。
「這還滿酷的。」
這樣說後,攝政成功得到和爆彈笑聲相同數目的人眼睛瞪大。他也讓我瞪大了雙眼。這不只關乎他所說的話。還有他的語氣中那樣地冷靜。
「我知道,對吧?」爆彈轉過身面向他,將她的頭傾向一邊:「我以特斯拉關於震動的作品作為它的模型。他提出個理論說,如果你能取正確的頻率就能將地球摧毀……」
「我無意冒犯。」攝政說:「嗯,我該重新說:我真心在意自己有沒有冒犯到妳。不過別對我開槍喔。我只是想阻止妳繼續說下去,告訴你我不在意那些科學東西、所有怎樣辦到的技術屁話。那太無聊了。我只是想說,看到一個人溶解成這樣,還挺酷了。很噁,很詭異,幹他媽糟糕透頂,但這很酷。」
「沒錯。」爆彈在所有人的注意之中狂喜:「就像獲得一個,你不知道自己在問的問題的答案!」
「妳是怎麼做的?把炸彈塞進這些平民身體裡來叫他們為妳工作?」
「每個人都有喔。」爆彈回答道,幾乎為她的「實驗」成功和攝政的注意力顯得興奮到錯亂。她半跳步半地穿過人群然後靠在她其中一個混混身上,拍了拍他的臉頰:「就算是我最衷心的也是。做起來有點泛賤。畢竟把東西塞進他們頭裡不是正當程序呢。在最先的二十人之後,我閉起眼睛都能做手術了。是如字面意義上閉起眼睛喔。我真那樣做了幾個呢。」
她噘起嘴說:「但是在麻醉最先十多個人之後,在他們清醒錢給他們驚喜,好讓我有圍剿其他所有人的人力?一個又接著一個打?一旦新奇感退去之後就變得很煩人乏味了。」
「就算我有妳的能力,也太懶得那樣做了。」攝政說:「我能靠近那個屍體嗎?看得更清楚一點?」
她的心情一瞬間改變,她生氣地朝他戳出手指:「不行。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試著要做什麼。我是他媽的天才,懂了嗎?我甚至能在你決定第一步之前先想出十二步。這就是為什麼你們站在那裡而我……」她將自己從剛才坐著個吉普車身旁邊拉倒車上:「就坐在這裡。」
「冷靜點吧妳。」攝政回答:「我就是問問啊。」
我能看到媘蜜的表情和我的想法相同。稍微尊重點這個瘋狂炸彈客吧。我安靜地說出媘蜜沒法說出的話。
「放點尊重。攝政。」我低聲說道。
「沒差啦啦啦啦」爆彈拉長音說:「瘦皮猴男孩剛才失去了任何他欣賞我的藝術所獲得的好意。或至少,他能裝得非常有說服力。」她輕輕拍了那個拿著攝影機的男人的肩膀:「你還在錄嗎?」
那男人半點了點頭。當我看向他時,我看見他臉上有幾滴汗水滑落,即使現在是很涼爽的夜晚。看起來她的混混也是,被她嚇壞了。
「很好。」爆彈將她的粉紅手套一起摩擦:「我們會把那段講話剪掉,然後我們會放上網路,也給每個當地新聞台都送一份。你覺得呢?」
攝影男人以一種帶口音的嗓音回答:「計畫不錯,爆彈。」
她將雙手拍在一起。指向人群說:「好啦!所以,你……沒錯就是你,穿著黃襯衫和牛仔褲的女孩兒。如果我叫妳去做,妳會拿起槍然後射人嗎?」
我花了整整一秒才看到那在人群最後面的女孩。她以嚴峻的表情看著爆彈,想盡辦法回答說:「那把槍也融、融化了,女士。」
「妳要叫我爆彈。妳知道了。沒什麼花俏的。如果那把槍還在那裡,妳會開槍嗎?或是如果我讓其他人給妳一把槍?」
「我、我想我大概可以。」她的雙眼不斷瞥向那灘曾經是帕克.吉霍的水灘。
「這樣就結束了我的展示了。」爆彈向群眾們演說道:「恐懼!這就是為什麼竜特意招募了我。我總是瞭解在人心深處,恐懼是強大的工具。他只是說得太好聽。真正的恐懼是確定性與不可預知的混合。我的人知道如果他們跨過我的界線,我只會考慮讓他們腦子裡的炸彈咔碰一聲。砰轟。他們知道如果我死了,每一個我做過的炸彈都會引爆。還不只有我塞進他們腦子裡的喔。他媽的每一個都會爆炸。而且我已經做過很多了。這就是確定性。」
莉莎伸出手抓住我的手,緊緊握著。
「至於不確定性呢?」爆彈雙腿踢著吉普車的車身側邊,就像一個小學生踢著一張椅子一樣:「我喜歡混合起我的武器庫,所以你永遠不會知道妳會得到的是什麼。但是你也要讓其他人不斷納悶著,對吧?讓他們隨時膽戰心驚?最恰當的例子就是:沙贊【就是超級英雄電影的那個沙贊】!」
那個詞同時伴隨著一陣非常真實的爆炸響聲,緊緊接著是某個聽起來像雷聲的東西,但莉莎已經拉住我的手,把我拉了開來。
我一瞥進混沌之中,尖叫的人們從爆彈的群體中發生爆炸的地方跑開。奔逃的人們擋住了拿槍的人們的視線。
攝政的手伸了出來,朝外揮動,讓十來個人跌在其他人身上,將那群人變成毫無秩序的暴民。我聽見過大的槍響轟鳴,看到攝政抓著松垮垮的左手臂肩膀,我不確定他是否有被打中。
最後,還有爆彈,仍然坐在吉普車的一邊。她沒有吼著什麼或笑出來。她正在讓我們從她的掌握中逃脫,她的人正處於無腦恐慌地殺死彼此的邊緣上,而且她正好一時興起殺了她一個人。從我們剛才看到的來說,我願意賭她在所有事情發生時,還在笑著。
我幾乎沒注意到夜晚已經降臨,天空就好像邀請我們更深入這個迷宮,電線桿在我們頭頂上閃爍、點亮。戰慄以一簾黑暗掩護我們的撤退路線,我們跑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