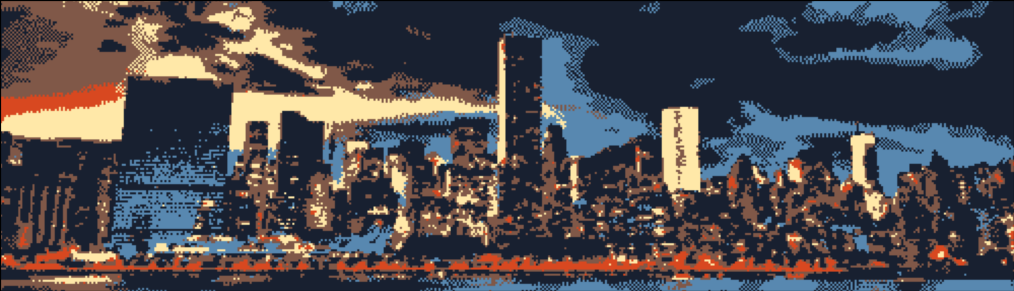 x
x
「嘿泰勒,醒醒啦。」這是個女孩的聲音。
「泰勒?」是一道更低沈、更成熟的嗓音說:「拜託啊,孩子。妳已經做很好了。」
我感覺很溫暖,模模糊糊的。就像在一個冷天走進一張暖床一樣,全身都蓋得正合適,感覺像徹底休息了,知道你不必立刻起床。或是像個六歲小孩,夜裡爬進爸爸媽媽的床然後到他們兩人中間。
「我想她正漸漸醒過來了。等她一下。」是某個比較老的人在說話。也許,是個老人。是我不熟悉的人。
「我剛還擔心她不會再醒來了。」那個深沈的男性嗓音說道。
「我該告訴你她沒昏迷。」那個女孩回答。
「妳也同樣,絕對、百分之百確定她沒有嚴重的腦損傷?」那個老男人問道。「因為麻醉劑能遮掩住那些症狀,而且如果我們等太久才行動……就那樣。」
「沒比我剛跟你說的還更嚴重的。」那女孩說,只是有一點暴躁:「除非你的儀器故障。我需要正確的資訊來工作,不然我會得到假情報。」
「我向妳保證,我的儀器也許有些限制,但絕對完美運作。」
我試著睜開我雙眼,發現所有東西都太耀眼。霧茫茫,彷彿我從水面下看著所有東西,可是我的雙眼卻如沙紙般乾燥。某個暗沈的東西穿過我的視野,讓我的眼皮跳動了下。其他某個東西搔癢了我的臉頰。我試著抬起我的手到臉上撥開他們,但我的手臂仍在我身側,埋在我無力移開的床單之下。
「嘿,睡美人。」那個低沈的嗓音又說了一次。我感覺到一隻大手按在我的額頭上,將我的頭髮往後梳著,再次讓我想起我媽和我爸。我就像個孩子,被照顧著。
那個老人和女孩依然爭執著。她的語調毫無耐心:「腦震盪,嚴重失血,挫傷,內外傷都有,加上不管那什麼他媽的亂搞她神經系統的東西,懂了嗎?我沒理由對你說謊。」
「我和妳說的是,如果有別的東西存在,會有併發症產生,那就是妳的責任了,因為我在這事上相當信任妳。當然,我寧可這女孩活下去,或只是最後有腦傷害,但如果她真的沒撐過去,我也不會有罪惡感,而且我……」
「如果因為我的錯誤而導致事情發生,這不是因為你給我錯誤的訊息或使用的工具,我會承擔錯誤。我會這樣告訴他,然後你的名聲不會受到影響。我答應你。」
那了老人含糊嘮叨地發著牢騷,但是沒再說任何事了。
我再次試著張開雙眼。我認出了那張臉。布萊恩。莉莎來到床邊加入他的行列。
「嗨囉。」她說,語調充滿同情:「妳被痛揍了一頓,嗯?」
「我猜是。」我回答道,除了我不確定有沒有將「是」說出來。我可能飄回了夢鄉,可是我臉上另一陣搔癢讓我鼻子皺起來:「這是什……」
「那個呢,甜心,是我們試著叫醒妳的唯一原因。妳在睡著時一直使用妳的能力,然後在這個鄰里的所有蟲子一直聚集到這裡爬到妳身上。不是一起來,沒有聚在一起,可是它們一直累積,就會有人注意到了。」
布萊恩掃視了房間:「我們把窗戶和門用保鮮膜和膠帶封了起來,它們還是能進來。沒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帶妳到任何地方,而且這裡這位好醫生需要我們離開,以免真正的病患走進來。」
「我需要的是個無菌工作環境。」那老男人抱怨著:「一個沒爬滿了蟑螂和……」
「我們在處理了。」莉莎瞪了他一眼。然後,以更輕柔的嗓音,她說道:「泰勒,先別睡喔。」
我驚訝地理解自己正在打瞌睡。真有趣。
「我知道止痛藥很舒服。我們給妳打了一大箱,因為妳看起來真的很痛。但是我們需要妳把它們弄走。那些蟲子。」
喔。我朦朧地想起,在我暈倒不久前有告訴我的蟲子來到我身邊。我猜我還沒叫它們停下來。我想,失去知覺阻擋我這麼做。我發出一道指令,告訴她:「做好了。」某個東西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嗯嗯。這音樂很有趣。」
「音樂?」莉莎頓時看起來十分擔憂。她看向布萊恩。
「在外面。在前門。也許,是一支智慧型手機。那裡有一個男人,在聽著音樂。也許他沒有把耳機戴到耳朵裡。也許它們沒插進手機本身。聽起來像交響樂,或是流行樂。那是拉丁文?還是英文?兩個都有?最後一點聽起來像日文。或是中文。我沒辦法分辨這之間的區別會很種族歧視嗎?」
「泰勒,妳在說蠢話了。」布萊恩說著,語氣並非嚴苛。
莉莎短暫地從我視野中消失:「但她是正確的。前門外面有個男人,是在聽音樂。妳怎麼知道的?」
「門上有隻蛾。我忙著聽音樂,我忘了叫她離開。我很抱歉,我會……我會……」
「噓。放輕鬆。沒事的。把蟲叫走之後,妳就能回去睡覺了。我們會處理所有事情。好嗎?」
這樣正好。我睡著了。
■
我從夢中被推擠出來。
「當心點!」
「我很小心了。別這麼焦慮啦。關起車門就好了。」
「我才沒有焦慮。你幾秒前差點把她掉在地上。我發誓,如果你讓她的頭撞倒……」
「我沒有啦。」他的話語成為在我身體一側的一陣低沈震動,那在我耳中成為了噪音。我身體那一側也很溫暖。聞起來真香。就像皮草和刮鬍泡。
我開始說了些東西,然後停了下來。太費力了。
一個女孩的聲音聽起來離我耳朵不遠。「嘿呦,泰勒。在說什麼呢?妳醒了?」
我搖了搖頭,然後將我的臉緊緊靠在那個溫暖的身體上。
她笑了。
有一陣敲打聲。是「剔鬚理髮,兩毛五」的經典旋律【C-G-G-A-G B-C,就是「登登登登登,登登」】。門不久之後就打開來了。
「老天,泰勒。那是她嗎?」
那個女孩--我現在認出來了,是莉莎--回答道:「她很好,只是很想睡。就像我在電話上說的……」
「我很抱歉打斷妳,只是……我很抱歉,我完全忘了你的名字,但我能幫你把她扛進來嗎?」
「實際上,我還好,而且我認為如果我們試著調整到兩個人扛她的姿勢更有可能讓她掉下來。我名字是布萊恩。」
「布萊恩,很好。謝謝你。如果你能就把她帶到這裡。在妳打電話過來之後,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我弄好了沙發床,以免我們沒辦法把她搬上樓,或者如果她得要用輪椅。我還在想最糟糕的情況……」
「沙發就非常好了。」莉莎說:「她肯定沒處在能夠,或甚至接近,可能有的最糟情況。她會睡很久,你需要每半個小時就確認下她的情形好不好,這樣持續十二小時。此外,她也可能想在小睡之間看電視,所以這看起來是最完美的地方呢。」
「好的。太好了。」
我完全躺平,立刻想念我前一刻接觸的溫暖和親密感。某個人將烘乾機暖和了的被子和一張沈重的蓋被在我身上,我決定,自己可以接受這樣的情況。
「你能到廚房來嗎?我們房子很小,而我也怕沙發床拉出來之後客廳就沒地方地方坐了。在廚房裡,我們會比較安靜點。」
「可是還能看到她有沒有醒來。」莉莎回答:「滿合理的。」
「我能給你們倒些飲料嗎?茶,咖啡?」
「咖啡,拜託了。」布萊恩回答道:「今夜很長。」
「赫本先生,在你還忙著準備咖啡時,我可以要杯茶嗎?」
「你們做了這麼多,倒杯茶是我至少能做的事。但是拜託了,叫我丹尼吧。」
如果我方才在嗎啡引起的朦朧感中感到舒服,我在聽到那名字的這一刻,十分、十分清醒,我理解到這些聲音和我認出的名字毫無任何理由出現在一起。
我爸、莉莎和布萊恩。就在我家餐桌旁。我讓我雙眼維持半閉著,然後緊密聆聽每一個詞彙。
「她還好嗎?」
「像我在電話上說了,她還好。」莉莎說:「腦震盪,淤清,有些失血。縫了九針。」
「我該帶她去看醫生嗎?」
「你可以。但我爸是醫生,他已經在他的診所看過她了。動用了點關係讓她照了電腦斷層掃描,MRI。他認為在他給泰勒更強的止痛藥之前要徹底確認她有沒有腦損傷。這。我在這些口袋中其中一個裝了一罐。這個。這是可待因。她大概會有些嚴重頭痛,然後在睡著時、最疼痛時呻吟。一天給她四次各一片,但只有她需要時再給。如果她像現在這樣好,就讓她戒掉。一天兩片,或是一天四次半片。」
「多少?」
「可待因?四片……」
「電腦斷層掃描,MRI,還有處方藥。如果妳能給我一點時間上樓拿我的皮夾,我會付……」
我能想像莉莎抓住他的手,阻止了他。「丹尼,她是親友。我爹地他根本沒說過要你付錢。」
如此超現實。聽見我爸的名字和「爹地」,從莉莎的嘴巴講出來。
「我……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謝謝妳。」
「沒關係啦。真的。我感覺很內疚……」
「我們很內疚。」布萊恩插話說。
「……讓這種事發生。讓泰勒被衝擊打中。我也很抱歉我們沒更快打給你。我們得等泰勒醒,她思緒足夠條理到能給我們你的電話號碼。」
我很確定自己沒這樣做。這大概成了媘蜜的詭異時刻之一,是她想出某個我沒猜到她能辦到的事。
「我……沒關係的。你們其他朋友還好嗎?」
「瑞秋比泰勒有更多刮傷和淤清,可是她沒有腦震盪,而且她是個強壯的女孩子。我猜她現在正在家裡安穩地睡覺吧,她這個下午就會起床活動了。艾利克,我們另一個朋友,在爆炸時昏了過去,醒來的時候頭痛很嚴重,但是他還很好。我們笑他像女生一樣昏倒,這讓他滿他媽……呃,讓他很煩。就好像男生不會昏倒似的。」
「你們倆呢?」
「有一點太疲倦,但是顯然,你能直接看到我們的狀況。刮傷、撞傷、淤清。我只有一點點,有被燙傷。沒比曬傷還嚴重啦。」
「我看,沒有曬到妳眼睛周圍?」
莉莎笑了,如此自然你幾乎不會對此多想:「對啊。我當時戴著太陽眼鏡。有這麼明顯嗎?」
「沒這麼嚴重,而且如果這是像曬傷一樣,妳幾天之後就會好多了。妳能告訴我更多點,到底發生什麼是了?妳在電話裡,說到某個關於……」
「一個炸彈。你有看新聞嗎?」
「整個城市不分日夜的好幾個爆炸,有聽過。還有在PHQ的那個事件。全部都是由一個超亞人類引起。我沒辦法記住她的名字。聽起來像是日文?」
「爆彈,對嗎?是呀,我很確定那就是她了。我們從羅德街市場回來時走捷徑穿過碼頭,我猜我們是正好在錯誤的時間點到了不好的地方。上一秒,所有東西都很普通,然後就變成了災難。布萊恩在泰勒重綁鞋帶時拿著她的包包,所以她爆炸時在我們其他人的後方一點。布萊恩和我爆炸之後就站了起來,然後艾利克也能起來,瑞秋和泰勒站不起來。泰勒是躺著的人之中最恐怖的那個,因為能直接看到血。」
「我的老天啊。」
我睜開眼睛偷看,然後看見我爸坐在餐桌旁,他的臉埋在雙手之中。我吞下第一個罪惡感的腫塊,再次緊閉住我的雙眼。
是布萊恩的聲音:「我感覺好差。我不應該在泰勒綁她鞋帶時往前走,不然……」
「布萊恩。如果你站在她旁邊,你會和她受一樣重的傷。那樣你就沒辦法搬她了。」莉莎反駁道;「是我提議要穿過碼頭的錯。」
「我得要問……」我爸開始說話:「為什麼……?」他漸漸沈默,沒辦法找到適當的說法。
「我們普通來說不會走城裡那部分的捷徑。」莉莎說:「可是我們有五個人,而且你知道的……看看布萊恩吶。你會想找他這樣的男生的麻煩嗎?」
「天吶,謝了,莉莎。」布萊恩說。他和我爸一起笑了。
太超現實了。
「我……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奇怪。」我爸有些猶豫地,說道:「但即使妳和我說這是一顆炸彈,在電視上,我還是沒辦法相信。我以為這是卑鄙的惡作劇,或泰勒曾經歷過的,呃。」
「那些霸凌?」莉莎幫我爸說完話。
「你們知道了?」
「她解釋很多事情,還包括了一月的事件。我們全部人都講清楚,如果她要求了就會幫忙,不管她想要的是多大多小的幫助。」
「我懂了。我很高興她有人可以聊,那些事情。」
莉莎有些同情地,回應說:「可是你對那個人不是你,感到很沮喪。」
如果罪咎能讓你感到肉體上的疼痛,我認為這就像把彈簧刀插進我心。
我爸,讓我難以理解地,笑道:「唉呀,妳可真不是恐怖地敏銳呢?泰勒有說過妳很聰明呢。」
「她說過,真的嗎?這真是個好消息。她還有什麼說了其他事情呢?」
我爸又笑了下:「我在說些她會想要我保持隱私的事情前,現在不會再說了。我想我們都知道她總是把事藏在心底。」
「說得太好了。」
「那兒,那罐子裡有些手工餅乾。還是熱的。我把沙發弄好了之後,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我得要做事讓焦慮發洩出來,所以我烤了餅乾。在我看看你們的茶和咖啡好了沒,就請當作自己家吧。」
「謝謝你,丹尼。」莉莎說:「我要去客廳,看下泰勒,這樣可嗎?」
「請吧。」
「就只要先拿片餅乾……嗯。聞起來真香。」
我閉起雙眼假裝睡覺…我能聽見布萊恩和我爸在另一個房間說話,聊著我爸的工作。
「所以呢?」當莉莎爬上沙發床躺在我旁邊時,她以安靜的嗓音問我:「這個故事有通過檢閱嗎?」
我想了下:「我不喜歡對我爸說謊。」
「所以我們就幫妳說謊了。除非妳想告訴他真相?」
「不是,可是我也不想要你們在這裡。」腦子的煞車應該阻止我的嘴唇亂動,卻失敗了,讓我的言詞離開我嘴。我閉上雙眼,感覺雙頰脹紅得火熱。
「我……我很抱歉……這聽起來太糟糕了。我很感激你們所做過的,還有妳正在做的事。你們很讓人敬畏,而且和你們出去玩時是我幾年來最有趣的時候了。我很高興你們在這裡,我也想只平靜下來,在那些事情全部結束之後放鬆一下,可是……」
莉莎將一隻手指放在我的雙唇上,讓我安靜下來:「我知道。妳喜歡將妳生活的不同部分區隔開來。我很抱歉,但沒有其他方法能避免了。妳受了傷,而且我們不能在妳爸不激起事情的情況下留住妳。」
我垂下視線:「是啊。」
「妳大概會在幾天中感覺有一點點不穩定。妳的,呃,剛才那殘酷的誠實大概就是腦震盪的效果。這會影響妳的情緒,大概會讓妳像有一點醉了一樣放鬆抑制想法。妳的記憶可能會有一點不可靠,妳也許會更混亂,或可能有更極端的情緒搖擺,像哭泣狂飲之類的。妳大概也更難理解社交線索。妳要努力度過這些全部,若妳說了些普通而言不會說的話,我們也不會在意。就只是……試著別在妳爸周圍讓任何私事洩漏出來,就不會有秘密洩露了喔?這樣的情況應該不久就會結束。」
「好吧。」最後那一部分是件讓我安心的事。
布萊恩加入我們,坐在莉莎躺著的位置對面角落,就在我腳旁。「妳爸是個還不錯的男人。」他對我說。「很讓我想起妳。」
我不知道該回答什麼,所以我只是說:「謝啦。」
「就算妳之後回復得差不多了,我想我們會安分下來把頭壓低避免麻煩,至少一段時間會是這樣。」莉莎說道。布萊恩點了點頭。
「我喜歡這個主意。」我回答說:「所以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移動了頭的位置好讓她能和我共享枕頭:「從何時開始?」
「從艾利克讓車子撞翻。一秒之前所有事都還好,然後下一秒,我幾乎沒辦法移動,沒辦法思考。」
「她裝死了。我忙著照看艾利克,猜你們正在監視她。同時,你和布萊恩--我猜--以為我在監視她。在我們都沒有注意力到她時,她把榴彈發射器上了膛射向妳。那應該會燒傷妳的,但我猜想是妳的假面服在那時救了妳。不過,妳假面服沒辦法防止腦震盪。那炸彈還有第二個效果,它對妳的神經系統作了某些事情。就像被電擊棒桶了一樣,但更專注於,以十足痛楚將妳無力化,而不是將妳電暈。」
我抖了一下。光是想起那是什麼樣的感覺都令我刺痛,彷彿聽見指甲刮在一片黑板上。
「我距離你們比較遠,而且我認為妳的身體護住了布萊恩,也可能是他的能力起了些幫助,因為我倆沒妳一半嚴重。那仍足以將我們兩人放倒,久到讓爆彈上膛兩發黏膠絲質的噁爛東西。等到那時,我們處境相當糟糕。一直到妳翻轉逆境。」
「我捅了她的腳。」我想起來了。
「妳切掉了她左腳兩隻半腳指。其中一隻有戴腳指戒。布萊恩說妳在昏過去時,把刀子推向了他。他把整片區域覆蓋上黑暗,成功拿到了刀子,釋放他自己,然後救了我們其他人。」
「還有爆彈呢?」我低語著。
「她就是兩個壞消息之一。她在布萊恩解開繩子來救我們時跑掉了。」
「幹!」我說,有一點點太大聲了。
布萊恩聽起來慚愧:「妳的狀態當時很不好,我不確定攝政發生了什麼事,還有莉莎受到把妳搞砸的同一波衝擊而有一點虛弱。我也許能追上爆彈,阻止她,可是我決定,確保你們狀況良好比較重要。」
我點了頭。我沒辦法和他確切在那點上爭論。
莉莎接著說:「我打給了老闆,他讓我們到一位有著保密和為超亞人類工作的名聲的醫生那裡。他做了二十年。我們也很擔心妳。」
「抱歉。」
「沒有什麼好道歉的。不管如何,這或多或少都算解決了。醫生把膠囊從布萊恩的鼻子拿出來,把妳縫縫補補,給攝政一劑靜脈注射。布萊恩出門去找瑞、她的狗和錢時,我就坐著看著妳。只有損失兩、三千塊,是某個拿袋子的人想說,算錢之前不會被抓到才拿的。我們老闆派了輛貨車,時間過了午夜一點點時去把錢收了回來。他給我們的錢已經在我們的公寓了,他決定那些文件值多少後,還有更多錢會進來。」
「妳說或多或少算是解決,而妳仍然沒告訴我第二個壞消息。有什麼是妳沒說的?」
她嘆了口氣:「我還希望妳沒清醒到問起這個。妳真想知道嗎?」
「我真的沒想知道。但如果我要在這繼續躺一陣子,調養生息,我不想被留下來想像最糟糕的狀況。」
「好吧。」她伸手進她的皮夾口袋裡拿出東西,然後交給我一塊剪報。不過這是撕下來,而不是剪下的。撕報?在最上面,有著粗體大字,寫著「逃脫」一詞。
然而,當我試著讀文章時,發現自己無法將視線固定在一行字上。「幫我讀?」
「我給妳個簡介。就正在她開始坐上吉普車追我們前,爆彈發出命令,開始實行另一個計畫。炸彈在整個城市各處引爆。炸掉變電器來切斷整個區域、學校、橋樑、火車軌道,之類的地方的電力。大家都在抓狂。在每一個頻道上,這件事都成了頭條新聞。他們說,目前至少二十人確認死亡,還有其他屍體沒被指認出來,而且還沒算上那四個她用槍指著我們時炸掉的那四人。」
帕克.吉霍的結局畫面,生動地浮現在我眼前。他死了。他真的死了。我從不認識他,但是他已永遠離去,而我沒辦法做任何事來幫助他。
「這就是第二個壞消息了。那些爆炸事件?全都是過度膨脹的混淆視聽。是個讓城裡每一位假面忙著的東西,同時李鬼則讓竜從PHQ衝出來。」
我嘆了一口長長的氣:「幹他媽的。」
「現在這城市是片戰區。ABB膨脹成兩週前的十二倍規模,還有爆彈橫衝直撞。每幾個小時都有更多炸彈被引爆,可是它們這次沒針對主要設施。而是公司行號、廉價公寓、大型倉庫還有船。我猜她是瞄準著其他主要幫派和派別在城裡所在的地方,或是他們可能設基地的地點。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說起來,你還會認為切掉她三分之一腳指會讓她慢下來呢。」布萊恩說。
莉莎搖了搖頭。「她在處於躁狂階段。如果那還沒結束,她也會消耗殆盡,那一連串爆炸幾小時內就會停下來了。不過,竜一旦作為領導復職,就代表ABB不會喪失任何熱度。很大的概率是,他會徹底利用爆彈為他創造的優勢。接下來就只是地點、時間和程度的問題了。要看他所處的狀態如何。」
我沒得到機會持續這個話題。媘蜜舉起一隻手指放在她雙唇前,我們都閉上了嘴。幾秒後,我爸走進了客廳,端著個托盤。他將盤子放在我腿上。上面有三個馬克杯,一盤餅乾和兩個烤好的貝果,一個塗著果醬,另一個則是奶油。
「我還有一個貝果在烤箱裡,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更多的話就請自便吧。綠色馬克杯是布萊恩的咖啡。茶室給妳們女孩兒的。這妳的,莉莎。伍斯托克馬克杯是泰勒從小到現在的最愛。這。」
布萊恩在我兩手端過馬克杯時輕輕笑了下。
「嘿!不要在我這樣的時候笑我啦。」
「這讓我想起來,要多久她才會回復正常?」我爸問莉莎。
「至少,要一週。」莉莎回答:「也許要護送她從廁所來回,直到你確定她能自己站穩,不過除此之外,大概只要她留在床上,待在家裡放輕鬆到下週六就好了。」
這讓我頓了下:「那學校呢?」
莉莎輕輕用手肘推了下我的上臂然後微笑著:「你有了完美藉口不用去。為什麼又要抱怨呢?」
因為我在幾乎翹掉了一整週的課之後逼了自己去學校,以不再翹任何課作為目的,而現在我又要翹掉另一整週的課。我沒辦法這麼說,特別不能在我爸面前說。
「我們再留一會兒好嗎?」我爸離開去拿第三個貝果那時,莉莎對我耳中輕語。
「可以啊。」我允許道。我該說,傷害已經造成,他們已經在這裡了。我急忙挪開好讓布萊恩能坐在床上,正好在我左邊,而莉莎起身一下抓起了電視遙控器。她找到一部只開始了幾分鐘的電影,同時她安頓在我右邊。
我頓時打起瞌睡,醒來時發現自己的頭正在布萊恩的手臂上。即使在我雙眼睜開後,我再次開始專注於電影上,就留著頭在這個位置。他看起來沒有很在意。我們三人對著電影一連串的笑點笑著,莉莎還開始打嗝,這正好讓布萊恩和我笑得更開懷。
我看到我爸在廚房閒晃,大概是在看著我,我們的視線交會了下。我對他微微揮手,沒有移動手臂,就只有我的手掌,我微微笑。他也以微笑回應我,那大概是我很久以來,第一次在他臉上看到的真正真誠的笑容。
學校那回事?我之後再擔心吧,只要我能活在現在這當下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