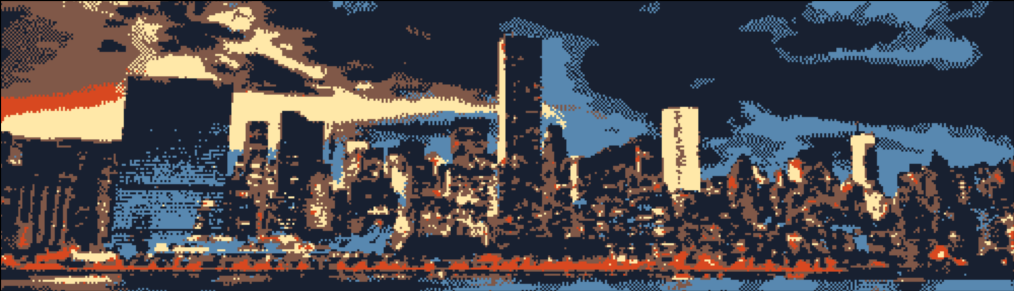 x
x
我對一個非常瘦、和戰慄差不多高的男人擺好架勢。他一隻手拿著一把刀,另一隻手拿了一把武士刀。
一道勉強的微笑出現在他臉上,同時他也以迅速動作在身邊揮武武士刀。
在我的命令下,一群黃蜂從我假面裝的護甲下蜂擁到他身上。他痛苦嚎叫之前,他困惑地拍打自己幾下。在他開始用雙手對著蟲群亂揮時,武士刀和刀子落到地上。
我抽出我的甩棒,甩上他的鼻梁。我最後比自己想的還要更用力打中他,因為他剛好在我揮動時向前彎腰。他搖晃旋轉著時,血從他的臉汨汨而出,我向前衝,朝他膝蓋外側低姿勢揮出一擊。
他癱倒在地全身扭曲,太痛苦,無法反擊。我彎下腰撿起刀子,那把刀看起來很廉價,而那把武士刀看起來則像古董。我用刀子將刀鞘從他腰旁割下,把刀子丟掉,踢進風暴防洪口。
我一手端著插入刀鞘的武士刀,另一手拿甩棒,我仔細觀察了夜晚中的戰場。
那棟隱約凌在我們頭上的建築是棟出租戶,就像在碼頭的無數其他房子一樣。五棟或更多個公寓擠在這樣狹小、應只能容下三棟的空間之中。十到十二個家庭共享一間浴室和淋浴間。現實十分醜陋,而我們也聽說,ABB把出租樓變成像這樣給他們的士兵使用的軍營。那些不怎麼熱衷的新兵--也就是那些腦袋裡被植入炸彈的人們--在這裡聚集,好讓他們能被監視、訓練、裝備,然後由ABB的隊長派出去。
我一開始有點畏怯。我之前擔心這是凱薩幹的好事,要讓組織起來的布拉克頓反派攻擊一棟滿滿是無助人們的地點。就算在媘蜜確認這是ABB的一個行動基地後,我還是抱持疑心。
我抱持的疑心也只持續到,在我們攻擊後,ABB的士兵就像螞蟻爬出蟻丘似地湧流而出。那是群小丑車的丑角。不管怎麼說,難以置信的數量的人們在一棟不是很大的建築裡,仍然很驚人。
我們二十比一,數量徹底被壓制,但是我懷疑我們中任何人真會為此全力以赴。ABB防禦方裡,沒有人有超能力,因為只有爆彈沒有受傷,我們也有些概念她在做什麼。也就是說,我們得擔心的是他們的幫派普通成員,方才也已經解決了拿槍的人了。
和我身高一樣的火焰猛輝環繞那棟出租樓點飾著。另一個地點,是一團團黑暗留駐。這片區域沒有電力,已經什麼都沒有好幾天了,八成是軍隊的成果,戰場只被火焰點亮,給予持續進行的戰鬥一種幾乎地獄似的氛圍。ABB成員的一張張臉龐,扭曲出痛苦與恐懼。反派們前進,毫無寬恕,一張張臉像戰慄的骷髏頭盔、嗆辣火那改裝過的防毒面具鏡片反射著火炎與格雷戈那麵團似、有藤壺狀硬殼的面孔。
我猜,我也在其中。我面具那修好了的嶄新黃鏡片,還有著貼緊我下巴顎部的設計。
我朝向戰鬥主要發生的地方走去,與一個二十幾歲的男人面對面。我立刻把他定位成其中一位新兵。他是那種,沒有炸彈植入他腦子中就不會打架的人。他把一根棒球棍像拿一把刀子似地指著我。
「投降。」我對他說:「把武器放下,趴在地上,然後把雙手放在頭上。」
「不、不行。我做不到。」
「我有超能力。而你沒有。過去十分鐘裡,我用比你更好的武器,放倒比你還大隻的人,他們還有殘忍頑強性格,而我根本沒有認真起來。我現在就告訴你,你會輸。你會輸掉這場架。趴下然後把你的雙手放在頭上。」
「不要!」他往前踏步,舉起球棒。
我不喜歡和這些人打架。不喜歡傷害他們。可是如果他們不會投降,我能給予最接近寬恕的東西,是足夠傷害他們到當他最後必須對爆彈解釋時,他們參與戰鬥的意願不會被質疑。
我讓我的蟲子爬上他,希望干擾到我有足夠時間揮出決定性的一擊。不過,這男人沒有屈服。他沒有掙扎,而是一股腦衝刺穿過螫咬叮刺的昆蟲蟲群,盲目地朝我的方向胡亂揮著球棒。我得倉皇後撤,避免自己被棍打中。我將甩棒拉到身後,試著決定何時、如何打擊。如果他的球棒打中我的甩棒,他能解除我的武裝。然而,我若能打中他的手,或在他的空隙中抓住他……
但沒有這樣的必要。戰慄幾乎是隨意地插手進來,拳頭猛穿那可憐傢伙的下巴。那男人直接倒在地上,球棒從他手中滑落。
「謝了。」我即使對那個打昏了的男人感到同情而皺眉,也如此說。
「沒問。」他嗓音縈繞的氛圍和他隨意的言語完全不一致:「我們這裡差不多結束了。」
我環顧一眼這個戰場。受傷的和失去意識的ABB成員們散落在建築周圍的地上。雖然我們先手時人數被遠遠超過,他們卻只有幾個掉隊的人殘留。
「媘蜜!」戰慄喝道:「有多少?」
「就醬!這棟樓清空了!」她喊了回來。我跟著她的聲音,看到她趴在少數幾輛停在路邊的車頂上,手槍吊在她手指上,停止了戰鬥,但仍拿在手中起威嚇作用。
「嗆辣火!」戰慄大喊著:「蝸牛!」
那兩位斷層線的隊伍成員正協力工作。嗆辣火從她那面具底部噴嘴噴出一道液體猛流,將它對準了建築底部,接觸到東西時便起了火。格雷戈蝸牛男則是,向附近的建築伸出一隻手,轟出一道穩定的泡沫急流。他在戰鬥之前就有告訴我們--他能在自己那龐大到驚人的胃裡調製出不同的化合物,然後以一道液體形式從皮膚排出。有黏著劑、潤滑劑以及強酸,也混和了其他東西。他現在會用上的帶有火焰阻滯劑,正如我們計畫的那樣。這樣就不會燒掉整個社區了。
當嗆辣火努力把那棟建築燒為平地的同時,格雷戈不斷將火災維持在那棟建築上,我們其他人花了幾分鐘時間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將傷者和失去意識的敵人從建築周圍移開。戰慄給我一包有好幾個塑膠手銬袋,我開始把它們用在ABB成員身上。
戰慄走進我:「我沒了。有多的嗎?」
我給了他一把塑膠手銬。
「所以這個ABB的事差不多結束了。」他說:「我之前和迷霧人--凱薩的其中一個部下--講過話。他聽起來沒要在母狗和鬥犬的事上施壓,正如你推測。」
我點了頭:「很好。我不喜歡他們,可是那是我們還不需要打的架。」
戰慄和一個帶著受傷的腳的幫派成員摔跤,把那男人的手臂扭到背後,然後當他的掙扎讓手銬很難戴上去時,戰慄揍了他的腎臟好幾拳。那男人就放棄戰鬥了。
「妳明天有計畫嗎?」
我將注意力從我正在銬起來的無意識女孩移開,然後看向戰慄。
「有嗎?」他問。
「我無計畫。沒計畫。」我笨拙地摸索詞彙。嚴格來說,我可以/應該回去學校,但我還有腦震盪的暫時性藉口,所以翹掉幾天也沒關係。學校會議那樣結束之後,我對於自己有這個藉口感到歡欣。
「想要來我家嗎?我應該參加個小組聚會來談論我現在上的線上課程內容,可是我還有我妹的社工那天下午會來看我的公寓。我希望買些家具,到時候組裝,但我時間也很趕,兩個人一起做的話會簡單非常多。」他對我說:「……這真是個胡亂說出口的解釋。」
「我懂你的意思。好呀,我可以。」
我足夠經常看過他那男孩似的笑容到,能想像出他在面具背後的表情了。
「我到時候再簡訊給妳時間和地址?」
「好的。」
他給了我一個很有「男人」風格的拍肩,接著走去街道較遠處,抓住一個試著爬走的人。
在他走了後,媘蜜加入我的行列,從我這邊拿走了一些手銬,幫我綁起其他人。她正在微笑。
「什麼?」
「沒什麼?」
「妳想太多了。」我告訴她。
「他沒有邀請過我喔。」她給了我一個淘氣的表情。
「也許他認為妳不會接受。」
「也許他認為我會,他還是想要花時間只和妳在一起。」
我有過我的猜疑。關於她正在暗示的事,相當明確的猜疑。我也沒機會澄清了。
「小心頭上!」格雷格吼道。建築開始塌下時發出一陣隆隆聲,接著是建築折彎塌在自己上面。嗆辣火將她的凝固燒夷劑吐息到建築的其中一個角落,抹消那裡的木頭石頭。她迅速後退,建築也被控制地倒塌了。
殘骸正靜下來時,格雷戈將他的滅火泡沫從一隻手噴出,以另一隻手手指引導那道液體好讓它廣角分散開來。每滴液體都掉落在建築一部分上,它們漲大成幾呎寬的泡沫團。整個建築相當迅速地,足夠覆蓋殘骸到幾乎看不見火焰的痕跡。
「我們好了,走吧!」戰慄喊了出來,回到媘蜜和我所在的位置。
我們立刻走了,讓混混們被綁著,而嗆辣火和格雷戈蝸牛男則消失在街道之下。
我們之前闖進一家老舊荒廢的維修五金行,將我們的車子藏起來,我們很快在媘蜜打給當局,告訴他們已經被處理好的ABB成員後我們便回到那。當車子倒車出來,前往水邊,我讓自己再次呼吸。
自從母狗和我對上龍之後,我們第三個晚上就是這樣了。每個晚上都比前一晚要簡單,而我也不確定這背後有多少是我自己對這些事感到更舒適,有多少是ABB在持續的屠殺中傾倒下來。
「我認為ABB已經完蛋了。」戰慄在駕駛座上說著,附和了我的想法和他早先所說的話。
「三日三夜來自警察、軍隊、城裡所有好人和大部分反派的壓力,就會有這效果。」我說。
莉莎評論說:「這就像我告訴妳的,泰勒,某個人打破潛規則,整個社會就來保持現狀。我們反叛和當地官方和平相處,我們真以某個方式和合作了起來,警察、假面和軍隊早上維持戰線,拿下任何探出頭來的ABB成員,而我們反派則做真正重要的事……這次這案例,八成比任何我能想到的例子更無恥、更有用。我猜我們該為此感謝蛇蜷。」
「這段經驗十分有收穫。」我補充說:「除這個之外,我對其他隊伍也更瞭解了。我不認為蛇蜷的士兵和我在戰鬥時看到的那些人一樣厲害。我和斷層線小隊的成員見過面,也和行旅人見過面。他們都不是壞人。」
「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是是以不同的方法。」媘蜜從後座往前傾,將她的頭和肩膀塞近兩個前座之間:「我說過我想和魔閃師和他的變形者對有待在一起的一部分理由,是要猜出他們的能力,對吧?我從來沒講過。」
「然後?」戰慄問。他一隻手放在方向盤上,用另一隻手把他的安全帽摘下。花了一秒鐘才將臉周圍的黑暗清空。
「然後魔閃師,他們的頭頭,是個瞬間移動者。移動的不只有他自己。他能瞬間移動任何能看見的東西。但是他的超能力還是有條特殊規則限制。他必須是將兩個質量差不多的東西交換位置。質量差異越大,交換就越慢,距離也越短。」
「這聽起來像是個滿大的缺點。」布萊恩說。
「他還是讓能力能運作。他讓ABB成員揍上自己人,也輕輕鬆鬆就他們解除武裝了。至於那個『變形者』。」媘蜜手指做出空氣引號:「她的名字是創使。她的能力?是遙控投影。」
「她沒有真的在那?」
媘蜜搖了搖頭:「出現時是用三角龍公牛生化機器東西,衝過一樓,觸發了一個陷阱,被炸成碎片。然後魔閃師就笑了。兩分鐘過後,她又組成了一個閃亮鎧甲的女性騎士,處理掉拿著槍的人們。」
「天吶。」我說:「烈陽舞者有個迷你太陽。軌彈天人,就布萊恩和我昨晚看到的,只需要觸碰就能讓物品在一秒內飛出幾百呎外。不管車子車輪承軸或一輛車都一樣。把這加入新情報吧,他們都是……」
「重擊手。」布萊恩接著我的話。
「幸好他們和我們在同一邊。」我說。
「目前如此。」布萊恩指出:「我們仍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在這裡,還有為什麼他們會幫忙。」
他看了眼媘蜜,眉毛抬起。她聳了聳肩:「我的能力沒有告訴我任何具體情報。我和你們一樣好奇。」
我加入布萊恩的行列拿下面具。這輛車,由我們的老闆提供,車窗上有著淺色漆,那方面不必有壓力。我得在穿過軍隊封鎖線時戴上面具,可是現在還不成問題。
我把太陽眼鏡鏡片放在擋風玻璃下,用鏡子檢查我的脖子。那邊的淤清依然很明顯。就像母狗曾說的,我看起來像是從吊刑中倖存。
「今晚,我可以待過夜嗎?」我問道。
我從後照鏡,看到媘蜜在後座聳肩。「那也是妳的地方喔。妳連問都不用問。不過,我認為妳該打給妳爸,別讓他擔心。」
「是啊,打給妳爸。」布萊恩保證說。
「好吧。」我早晚都會打給他。
當軍隊封鎖線上方的閃光燈在遠處進入視野時,我們停進了曾經是一個小雜貨店的等待區,就在他們視野之外。
「要趕嗎?」我問。
「我們沒問題。」媘蜜說:「我要打給攝政和母狗,看看他們的小組在做什麼。」
「那麼我就打給我爸了。」
我走出車子打了電話。
他在第一聲鈴響之後接了起來。
「嗨爸。」
「泰勒。聽到妳的聲音我就放心了。」
所以他確實在擔心。
「我今晚,也要待在莉莎家喔。」
「我希望妳回家來,泰勒。妳從學校會議離開後我就沒看過妳,我很擔心妳。」
「我很好。」
「不是我不相信妳,可是我自己見到妳的話,我會感覺好更多。我想和妳聊聊,一起吃個晚餐和早餐,聯繫下感情。我不想要像我們之前那樣疏遠,在……」
「在媽死後。」我幫他說完:「沒關係的,爸。我只是……我猜我需要轉換下節奏,從所有事情逃開一會兒。我已經為今晚作了計畫。取消的話會很尷尬。我明天晚上回去?」
他猶豫道:「好吧,跟我說妳有去學校。」
「是啊。」這道謊言輕易通過我雙唇,但它沈沈壓在我的良心上。不過,讓他失望我會感覺更糟。我試著以一半的非事實,將罪惡感的尖銳除去:「我週一時沒去。我昨天下午有去。」
「我想那比沒去還要好吧。那麼,我們明天晚上見吧。」
「愛你喔,爸。」
「我也愛妳。」
我掛斷了。那是個白色謊言,對吧?我沒真要傷害任何人,而且如果我告訴他我沒有去上學,我爸只會徒增擔心。
媘蜜和戰慄在我戴上我的面具時爬出了車子。
「都好了?」她問。
「準備好了。」我回答。
她打開在雜貨店地下室裡的艙門,那會讓我們走下延伸過封鎖線的隧道。
我們沈入了黑暗之中。
ns3.146.206.173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