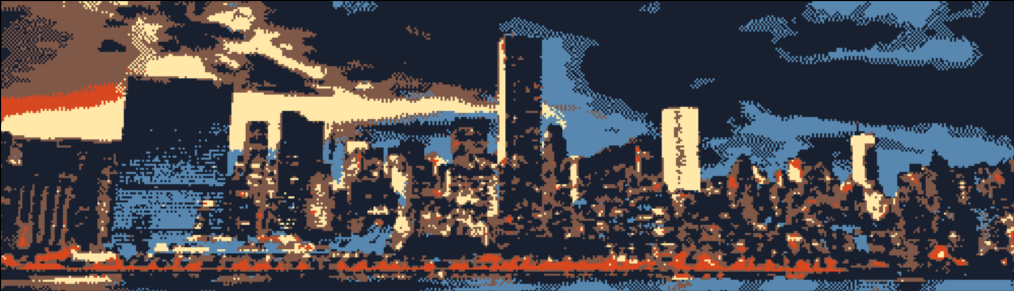 x
x
「投降吧。」兵器大師命令我們。
「不要。」戰慄回嘴。
「假使你讓這情況延長,你只會讓你自己丟臉。」
「我們數量五比三壓制你們,加上狗的話就是八比三。」戰慄回應:「我能看到你的朋友極迅埋伏在那裡。」
「你希望達到什麼?我承認,控制戰場很聰明,你可以在自己的掌握中下達每個交戰指揮,還用我們的武器來對付我們……但那些武器再也不運作。你們沒一個武器能用了。」兵器大師將他的頭轉看向用槍指著攝政的民軍小姐。「也表示你能別再試著把超能力用在我身上了,攝政。我顯示畫面角落中有一個閃爍的小燈告訴我,你在試著做些什麼。我設置了心電感應和共感防護,那會在你和媘蜜能力下保護我。」
我朝媘蜜瞥了一眼。他在物理上防禦了她?那是怎麼運作的?
接著我想了起來。當我們槓上榮耀女孩和萬癒時,媘蜜不是說,她能讀心嗎?現在兵器大師的錯誤情報讓他以為自己免疫。
「我不需要讀你的心。」她對他說:「你是唯一一個有防禦的人,所以你的隊友們和PRT隊員沒有裝備任何心電感應防護,我就能從他們身上讀出任何我需要的東西啊。你不是最好的發明家,但就像大部分巧匠,你有個專長--正好是個縮和融合科技。只在你周圍有效,但你仍然能把更多技術塞進原本不該在的空間……就像你的長戟。」
兵器大師皺了眉頭:「妳在說謊。」
該死。我真希望自己告訴她,他頭盔裡面有裝備測謊器。可是我不能在不說出我認識他的情況下解釋。
媘蜜邁開大步,微笑著:「當然,我對讀心撒了點小謊。卻沒亂扯你的武器和能力。我們來看看……對付我的伙伴戰慄,你把那東西做成了一個精美的調音棒。感受到空氣中的震動,再用你的精美頭盔把訊號轉換成影像?」
戰慄啪啪地扭著指關節。他已經得倒了訊息。黑暗不會有太多作用。兵器大師,則是,將他的武器抓更緊。對媘蜜無言地威脅著。
「而你那個棒子屁端利用了地板磁磚間的黃銅,把電荷傳送到這區域弄成一個精美的電蚊拍。你是在今晚來之前就這樣安排好,知道地板會這樣組裝起來?」
他沒有回應。
「我猜不是呢。那麼,就為你組裝好的設備恰巧能在這妥善運用感到高興吧。」
又一次,沒有回應。她微笑又更寬了一點。她繼續說:「你能分辨出我在說謊,嗯?這簡直讚透了。」
兵器大師的武器轉向大略對準她的方向。她沒有屈服。
「所以你會知道,當我說你的隊伍恨你入骨時,我是在說真話。他們知道你對自己作為捍衛者第七位顯著成員的升職,比對他們更用心。」
一秒之中,那把戰戟的刀刃分成三片,重組,然後以抓鉤型態朝媘蜜發射。刀刃尖頭聚集,在飛行時組成一個鬆散的球狀,穩穩打中她的肚子。她倒地不起,雙手環抱她身體中央。
那把武器的頭刃被捲回,猛然閃回戟棍之上。
「混漲。」戰慄說。
「根據你的隊友所說,顯然我就是。」兵器大師回答,看起來毫不因此困擾。
我聚集起蟲子,將它們穩在靠近兵器大師上方,以免我需要它們快速反應。
兵器大師將他的頭轉向我:「掠翅?今晚,特別是妳,不會想讓我更惱火了。」
他的戰戟尾端按了下地板,蟲子們便死去。我在他那樣做時瞥了眼地板。我很確定,在寬大的地板磁磚間有小條金屬--銅--線分隔?
攝政和民軍小姐之間有一陣疾動動作。她看起來弄掉了那把機槍,攝政抓住這機會拉開距離。他沒跨出一步她重新掌控了平衡,蹲伏低姿勢踢擊掃過他身下雙腿放倒他。她的機槍在落到地面的半空中消解,轉變成深綠能量閃光電弧閃回她手中。它重新物質化為一把閃光金屬大砍刀。攝政在她將刀尖止在他喉嚨一側時,停止掙扎。
兵器大師看著事情這樣發展開來,連根汗毛都沒動。就算他不在意自己的隊友,也顯然相信民軍小姐能自己處理。
「戰慄。你表現過你能去除你的超能力。」兵器大師說:「現在就去除。」
「我不知怎地。」戰慄回嘴:「我看不出任何重大的理由解釋我該聽你的。」
「呃,我脖子這裡有把刀頂著啊,老兄。」攝政指出來。
「……不是重要的理由。」戰慄重複他所說過的話。
攝政失笑出聲:「幹你娘咧。」
兵器大師毫無情感地看這兩人來回說話,以極端嚴肅的聲音,說:「這樣看吧。如果有證人,民軍小姐會更難以自保為由,來捅你朋友的喉嚨。」
他瞥了眼他的大副的方向,民軍小姐小小地點了下頭。
她會捅嗎?我猜,大概不會。我們能冒險嗎?這個選擇仍在戰慄手中。
戰慄看了眼攝政趴著的位置。一秒後,他讓黑暗褪去。群眾中的人大都亂癱在地面上,試圖抵抗蟲群的螫咬。狗兒們在房間邊緣埋伏,而母狗正騎著安潔力卡。極迅--他紅假面服上,兩側有兩條筆直線條在他胸前合起成「V」--距離她並不遠。我猜他們正在彼此對峙。
我在人群中發現艾瑪。她爸依偎住他兩個女兒,就好像他能將任何危險從她們身邊抵擋開來,而艾瑪她媽也抱著艾瑪的肩膀。
不知怎麼地,這真的很讓我惱火。
兵器大師瞥了我一眼:「還有蟲子。」
我不情願地,將它們從人群身上拉開。我讓飛行蟲待在天花板上完好的部分。我往上看了一眼蟲子,嘆了一聲氣。接著我又瞥向艾瑪。
這真的不是我想要事情結束的方式。我被逮捕,我的計策失敗,艾瑪沒有得到她做過那些超級爛事後應得的後果,就和家人、朋友們回家?
「先生。」我說,試著聽起來有自信些。艾瑪會認得我的聲音嗎?「讓我看看媘蜜的狀態。」
「只要你們投降了妳就能那麼做。」他說。他轉動了下身體好讓他的戰戟指著我大致的方向。我皺眉頭我不想要受到媘蜜所承受的處置。或是說,他不會在有人看著時那樣做?
我的雙眼瞄向人群的方向,看向媘蜜,她沒有抬頭說話。我能利用群眾嗎?他之前在我和他於渡輪見面時,在不爽什麼?媘蜜一直對我們強調兵器大師的什麼?
名聲。
「我需要確認你沒有造成任何嚴重的傷害。」我說道,我語氣中僅僅暗示著責難。
「她很好。」
「我想自己確認。」我站起來說。我能逼到什麼程度呢?「拜託,她剛才就投降了,你又那麼重地打她。」
「妳在說謊。」
「我肏她最好是!」攝政加入了:「媘蜜走近你,準備要被銬上手銬,然後你就把她打飛飛過整個房間,你幹他媽的瘋子!」
我不敢看向群眾。兵器大師才是我們在這裡,需要被觀察反應的人。
「夠了。這是場污衊。」民軍小姐說道,她的聲音也許拉高到了房間其他人也聽得見的程度。
「為什麼妳認為我們這麼不情願投降,如果我們得到的處置就是這樣!?」攝政吼著:「又不是說我們沒徹底完蛋啊!」民軍小姐移動那把大砍刀提醒他刀的存在。
兵器大師頭轉向我。這是極重的賭注。他會怎樣回應?如果他直接戳破我身為暗地黨中的叛徒,會有人相信嗎,我的隊伍會相信嗎,或者那只會傷害他的信用?他不知道媘蜜是否能分辨這個是事實。
「民軍小姐拿著一把刀頂著我隊友的喉嚨。」戰慄打破沈默:「我認為這相當明顯,你沒有手下留情。」
兵器大師轉身面對他的隊友:「也許比較沒那麼致命的武器會比較合適。」
民軍小姐的雙眉擔憂緊蹙:「長官?」
「現在。」他不留下任何反駁的空間。接著,為了確保他們仍然掌控整個局勢,他轉向最近、能成為人質的人。
就是我。
我背脊打直,沒能夠快逃脫,特別我還得從背上強抑泡沫貯存罐的背帶中,將雙臂滑出來。他邁步走向我時,將武器的頂端指向我,他可能會發射戟刃的威脅性使我屈服。我瞥了眼戰慄,可是他也僵在原地,他兩個隊友正在城市領頭英雄的恩惠之下存活。媘蜜正掙扎著要爬起來,可是她沒多少用處。
在攝政之上,那把劍微微發光然後轉變成黑色綠色能量。在那時,攝政出了手,蹲下將雙膝靠在胸前,往上踢到民軍小姐胃的身側位置。一秒後,他將雙手塞進她的鎖骨上。
她能力的黑綠能量,在她的肚子激烈鼓動要吐出來時,能量持續在她周圍環繞,沒有實體化,嘔吐物噴在她遮住下半部臉的旗子頭巾裡,流到地板上。攝政滾到一旁避免被沐浴嘔吐物。
我利用這個分心的空隙把所有房間中的蟲,從天花板上叫下來,把很大一部分蟲派往兵器大師那。他抹了下臉弄掉蟲子,就舉起了他的武器。我在戰戟打擊地板前用雙手抓住末端,將自己滑過地板來檔在桿子和地面之間。
電擊,和我所想的感覺起來不太一樣。當戰戟末端接觸我的身體,就和某人將一團活生生的蛇放在我的胸口上,牠們就在那翻騰似的,我右手皮膚和指尖上一陣捲鬚麻感襲了上來。這不怎麼痛。
兵器大師周圍的蟲子沒有死去。甚至,在我身上也只有非常少幾隻死去。
我知道蜘蛛絲某種程度上算絕緣體。我真的很高興它夠絕緣。真的、真的很高興我的干預,足夠阻止電能傳導到這片地區,把空中的蟲子都電死。
「嗯。」兵器大師的聲音在我上方隱約籠罩,他發出了不贊同的噪音:「不怎麼聰明。」
「母狗!狗!」我吼道:「戰慄!黑暗我!」
這種時候我的文法竟然退化成山頂洞人。不過,他將我和兵器大師用黑暗掩蓋。
兵器大師成功從我雙手中把戰戟奪回時,我把足夠的蟲子放在他身上來分辨他將戰戟底部重重地,遠離我地打在地版上。我的蟲子依然沒有死去,仍繼續爬在他臉下半部、暴露出的皮膚,爬到他的面罩下方。他剛要引導的不管什麼東西,都無法穿過這片黑暗。
在他能擊打我之前,我前往另一個方向。待在兵器大師周圍,而我的能力又是長距離作用,就不是個好點子了,再說他也是個近距離戰鬥員。我感覺他走動遠離了我,從他的嘴巴和鼻子上把蟲子抓下來,走向黑雲的反方向,打擊地板,殺掉我放在他身上的蟲群,接著將他的注意力轉向衝刺著的狗兒們。
我離開黑雲後沒兩步時,極迅就出現在我面前。
電擊和極迅兩個人都算是加速能力者,讓他們有能力荒謬的步速。不過,他們也是加速能力者中非常不同的種類。從我在網路上讀到和從雜誌、採訪影片中所知道的,我的理解是,電擊可以充能,然後在非常短的時間中以加速狀態移動,有點像母狗灌大狗的能力,卻是集中於非常短的時間。那是種生理性轉變,扭轉她的生理狀態,在對她的身體造成太大負擔前轉變回來。這些人這樣高速移動,實際上對身體卻是難以置信地重擔。這星球上只有一、兩位超亞人類能不用任何特別措施或這樣的移動限制,電擊和極迅並不在他們之中。
極迅,和電擊正相反,更像是暗影潛行者。他會改變狀態,我還是沒有概念那是什麼意思,不管是他部分轉換進入另一個次元,或者是時間的物理法則對他自己來說,相對地不同,我確實知道,這讓他不需要像電擊那樣休息就能快速移動。他快到我的黃蜂真都沒辦法落在他身上,而那些有爬到他身上的,在它們能螫他前就被甩到半空中了。
不過,他能力的缺點是當他這樣移動時,他不會打得同樣重,原因大概和他不會在一秒十次踏步踩地時粉碎自己的骨頭,被空氣摩擦力撕裂成碎片,或是無法呼吸而氧氣短缺一樣。他的速度來自,減輕他對周圍的世界的影響以及世界對他的影響。他無法同樣重地打擊目標,沒辦法同樣輕易底抓住或移動事物。喪失了的力量的比例都有效地成為他能夠快速地移動的能力。
所以就算他跑得再快,讓他打我也不會比被八歲小孩揍還更糟糕。
問題是,他打中我很多次。他的感知也被提升了,也就是,說他有了感知中數秒的奢侈時間來觀察我的反應,計算最佳位置來擠入下一拳或踢擊,把我扳倒或施以痛楚。這比起搏擊,更像被捕進一陣想要搞我的狂嘯大風之中。
極迅強迫我後退,絆倒我,總的來說就是要把我引導近一個方向--朝向一扇敞開的窗戶。他會強迫我穿出窗戶,然後就留我掛在窗台上,無力避免自己被逮捕,或者我得取而代之地被揍倒在地,那時我差不多就完了。一旦我被擊倒,他會持續一直狂揍直到另一個假面能來解決我,或者他會關閉他的能力夠久到用張椅子或其他東西,砸我的頭好幾次。
房間另一端,戰慄正和兩隻狗與母狗努力包圍兵器大師,同時其中一隻狗和攝政正在保持民軍小姐無法干涉。
我自己贏不了這場架。
「戰慄!」我吼道。在我能舉起手抵抗極迅再次說話前,嘴巴就被打了三次:「需要掩護!」
他為我分出一瞥,射出他的黑暗。瞬間,我就成了瞎子和籠子,只有我的蟲能用。
但極迅慢了下來,我曾猜想他是不是得用他的手找到我之後才會打擊。戰慄說過,暗影潛行者的能力不知怎地在他的黑暗中比較沒有效果。這也能適用在極迅身上嗎?或者這只是戰慄的能力額外增加了普通空氣阻力,和極迅的弱力量互相加成?
我的蟲子現在成功地爬上了他,讓我比雙眼還更詭異地清楚感知到他的動作,而且我也沒引導它們去螫咬,這樣他就不會簡單發現它們。它們開始聚集到他身上,我不知道為什麼,感覺這讓他更慢了。
狂揍的趨勢減輕,他現在,不足剛才讓我讓我失衡時一半有效。他沒法有效地看到我的姿勢來得知最佳打擊位置,所以我也能穩穩地站在地上。我兩次揮出我的拳頭,但我的打擊沒有多少衝擊力。我猜,是和他的能力有關,還有他快到在感覺到有東西打中他時就能避開的能力。
所以我抓出了個他沒辦法反應的武器,我的防狼噴霧劑,朝向他的臉噴了一下。接著我就指示剛才聚集在他身上的蟲子螫咬。
效果相當快速,而且很激烈。你從不會真看見有人抓狂,直到你看過加速能力者抓狂。他跌在地上,站起來,撞在一張椅子上跌跤,下一秒又站了起來,撲向一張桌子,盲目猛拍,希望找到一些能用來洗他眼睛的東西。我感覺到他動作猛然慢下來,將他的力量增加到足夠讓他自己確認杯子和水罐的位置。
我在他搜尋的桌上也有放蟲,而且那裡唯一的液體是酒。我預計他會繼續找些能減緩疼痛的東西,我移動到最靠近我的桌子。
果真,他也衝向同一張桌子開始摸索。我朝左邊跨了一大步,向身後伸手,雙手抓住甩棒泡棉握把。我像揮一根高爾夫球桿似的,往上揮往他雙腿之間。
我的理論是,我需要妨礙他的活動性,可是我又不想造成任何永久傷害,而我若打中他的膝蓋或脊椎的話,就可能是那樣了。再說,捍衛者也有頂尖的假面服設計師,再說什麼樣的男性超級英雄穿了昂貴假面服,又不會不穿護甲就出來?對吧?
在極迅雙膝跪地時,有個想法穿過我的腦海:除非,他為了額外的行動能力和減少摩擦力而放棄了杯狀護甲。
我會找某些方法補償他,在這全部事情結束之後。
他衰弱地抵抗我把他左手和他右腳拉在一起,用兩條塑膠手銬緊緊綁在一起。接著我將他右手銬在他面前的桌上。從所有方面來說,極迅無法行動了。
雖然我所有本能衝動都告訴我,要離開黑暗,看清楚外面正發生什麼事,我卻待在原地,匍匐前進,用我的蟲子感知。用牠們的腳、身體當數千又數千個細小手指來感知我的周圍,我感知倒了整個情形。
不管攝政對民軍小姐做了什麼,他已現在經站著,看管著她。他將一隻手朝她伸出而她則在地上,現在正乾啞喘息掙扎著,她的四肢也正抽動。媘蜜在他身旁,一隻手仍按住她的肚子,可是她正站著,凝望人群中可能想站出來拯救民軍小姐的人。
這就只剩下兵器大師了。不過「只剩」並不是正確的詞彙。母狗,她三隻狗和戰慄將兵器大師圍困,而就算如此,我的印象仍是他正掌控著局勢。
他再次將戰戟刀刃形成了一顆鬆散球狀,把它用來當作拉升抓鉤的鐵鍊伸長,戟尖形成連枷。我的隊友們停留在原地,維持一種僵持狀態,保持彼此間的距離,正好在他武器範圍外。兵器大師,他則正散散地以戰鬥姿態站立,握住他拿來當作連枷約略八字揮舞的戰戟長桿。
布魯圖斯吼向他的獵物,半步走近,兵器大師便抓緊了機會。鐵鍊微弱、呼地伸長,連枷以驚人的速度撞上布魯圖斯的肩膀。從布魯圖斯的反應來看,我會認為他剛才被一顆破碎球擊中。可能是兵器大師比他看起來得更強許多,或者是他的武器給那一擊一點點額外的能量。考量到他是個巧匠,那可能是任何東西。
兵器大師並不止於放倒布魯圖斯。當他讓刃球本身的慣性消失,兵器大師反握戰戟撲向戰慄,將他武器的底部像根棒球棍揮舞。戰慄往後踏了一步彎腰躲避,卻來不及恢復姿勢避開進一步攻擊。兵器大師不斷向前進,他把長桿底部甩上他其中一隻手、以戟桿重重,打中戰慄胸膛的中央時,也沒停下來。戰慄撞在地板的力道強到幾乎彈起,當兵器大師將戟桿按下他的肚子時第二次被重重塞進地板。
我毫不思索,踏出黑暗,接著我阻止了自己。我跳出去能有什麼幫助?
母狗吹了聲口哨要一隻狗攻擊,可是兵器大師已經反應過來,將手肘扯住鐵鍊來控制連枷頭的動向。他將戟桿放下抓住鐵鍊將刃球拉向自己,用空著的手在空中抓住刃球,迅速扭動連枷頭飛行的慣性,將它全力砸進安潔力卡的耳朵。母狗得在安潔力卡倒向她方才站著位置時中途跳開。
他絲毫沒有往下看,兵器大師將一隻裝甲靴放在戟桿之下讓它抵地彈起,接著將戰戟直直踢上胸膛高度。他一隻手抓住武器拉起鐵鍊。連枷頭重連接回長桿頂部時,猛啪地閃回刀刃形狀。
兩隻狗和戰慄倒下了,而且他至此都看起來毫不費吹灰之力。
我剛忽然想到是什麼讓兵器大師,比其他巧匠更高一等,讓他在其他有能力發明東西、施行瘋狂科學的人之上,那並非他八成讓自己經過的瘋狂份量的訓練。巧匠通常都有一個本領,一個只在他們作品中出現的特質。據媘蜜所說,兵器大師的能力讓他把科技擠在一起卻仍能運作。其他巧匠則被限制於他們能攜帶的份量或在當時能入手的東西,兵器大師呢?他對每個他能想到問題都有答案,又不須擔心空間的有限、他的裝備硬體重量或者是他多功能腰帶的空間,或其他類似的東西。這些總和起來,他的主要裝備,他的裝甲和戰戟,各自也仍相當令人震撼又徹底可靠。
兵器大師將他的背後轉向她,我看見媘蜜悄悄地,踏到一旁。
猶大撲上,兵器大師同一時候反應過來,媘蜜則對著人群,拔出她的槍。
我瞥了眼兵器大師,我視線中的他被倒在我們中間地上的猶大擋著。透過蟲子,我感覺到他朝媘蜜伸出他的武器,也感覺到了戟頭發射出反沖的力道。抓鉤鉤住她拿槍的手的力道,強得使她沒法瞄準,抓鉤尖頭也緊緊繞過她的手臂。
他將抓鉤往回拉扯同時捲起鐵鍊,這樣做,將媘蜜從地面扯起飛去。鉤刃剛好在媘蜜斜斜撞上脆弱的雞尾酒桌時放開了她。兵器大師扯了下他的戟桿來控制抓鉤收回的飛行路徑,在空中擊打媘蜜的槍,將它粉碎。
「別抓人質。」他說:「別用槍。」
戰慄開始站了起來,跌倒,接著在第二次嘗試時成功站了起來。那三隻兵器大師放倒的狗兒們花了更久的時間才站立起來。安潔力卡猛烈地甩頭,又甩了一次,停了下來,接著又甩了一次。
兵器大師看著母狗,將他的戟桿,拍著他另一隻戴裝甲手套的手掌心。
「瑞秋.林德,又稱:地獄獵犬。」
「兵器大師,又稱:混蛋。」母狗回嘴道。
「如果這情況持續下去,我沒辦法保證妳的那些動物們不會受到永久傷害。」
我能看到她在面具的眼窩後方的雙眼,對她左邊的布魯圖斯斜眼瞥了一次,也看了眼安潔力卡。她和他的眼神對上:「你對他們任何一個做出長久傷害,我們會找到你,然後十倍對你奉還。相信我,老人,他們知道你的味道,我們能追蹤你。」
他在一次,戟桿打在他手套上,發出金屬撞擊金屬的聲音。
他問她時的語調相當慎重:「為什麼要冒險呢?你們已經輸了。我們有夠多妳的狗的影片,我能弄出一個牠們的戰鬥模式模擬。我知道牠們的攻擊,牠們的反應方式。我知道妳在戰鬥中如何思考,妳所給出的命令,還有何時下命令。這全都寫在我的裝甲,我頭盔面罩的顯示上面。我知道妳和妳的怪獸們在妳做出決定前,就知道你們會做什麼。你們都逃不了的。」
「我們不只有我和狗兒們。」母狗說。
「妳的朋友?我也許沒有為他設置一個模擬器,可是我比你的隊長戰慄,更強。我比較強壯,有更好裝甲,更完善地裝備,也有更好的訓練。如果妳的朋友攝政把他的注意力從民軍小姐身上移開超過二十秒鐘,她就會射你們其中一個或所有人,也不是說他那樣費心會有任何效果。媘蜜?失去意識。掠翅?不成威脅。」
他在做什麼?為什麼他這樣集中於,讓母狗承認這場架結束了?
又一次,是名聲。他需要挽救這個情形,最可靠的方法,要補償他的損失,要讓這全部看起來很好,就是讓我們之中最刻薄、最強壯、最惡名昭彰的人下跪,承認敗北。
不過,他真的不瞭解母狗。
她把廉價的狗面具扯下,丟到一旁。面具其實只是種禮節,因為她的臉和身分早就眾所皆知。她那微笑在她臉上擴張,不能說是最迷人的微笑。太多牙齒露出來了。
「龍也,低估了她。」她對他說,正看向我。
兵器大師,也轉身過來看。
認真的?我是說,真的,母狗?傳了球給我?我連計畫都沒有。我在這裡,沒能做多少事。
「極迅呢?」兵器大師相當隨意地,質問我。
我聳了肩,模仿他的隨意語調,然而感覺全然不是如此:「處理了。」
「嗯。我想想……」
在他說話時,我面向戰慄,將頭對兵器大師的方向一扯。兵器大師並沒有健忘,把我的暗示當作放棄戰鬥姿態的理由。不過,當戰慄第二次用黑暗覆蓋我們時,他也沒有任何東西真要防禦。
最糟糕的可能性,就是是兵器大師告訴暗地黨我在計畫的事,目前這樣就解決了。我懷疑兵器大師會繼續在戰慄的能力影響下說話。
我就只剩下要處理這傢伙的問題了。當他穿過黑暗,朝我而來,我能感知到自己放在他身上的蟲子正在移動。至少,如果我能把他從其他人拉開來,也爭取了時間。
我跑著前往其中一扇陽台外面的玻璃門。我往後看了下,果然,看見兵器大師從油膩的影子中出現。在猶大跟在他身後出現時,他踮在雙腳腳跟轉身朝猶大揮動他的連枷,將那隻狗打倒在地,接著迅速轉身再次面向我。我到了外面時,那個鐵鍊捲收了回去,讓連枷頭回到那把武器頂端。他停了下來。
為什麼?他會維持距離然後像那樣收起武器,而不拉近距離讓我進入他的攻擊範圍,只有一個原因。
我猜了下。從媘蜜剛才兩次的遭遇,我知道那道攻擊會比我預期的還要快,我將自己往陽台地板撲去。
刃球飛出他武器末端,我嘗試避開可是幾乎沒有任何效果。他抽了下鐵鍊改變球體的軌道,同時把它張成抓鉤型態。那東西打中我的身側,刃尖擦過我雙間然後穿過我的腋下。我在這陣衝擊中呻吟一聲,我嘗試站起來時,差點在抓鉤纏住我的多餘鐵鍊上滑倒。我感覺到抓鉤的鉤子在我胸口周圍縮緊。
陽台另一邊,兵器大師將他的腳抬起然後舉起武器,準備將我捲起來。
不,不,不,不,不。
我不要這樣被擊倒。
不要在艾瑪幹他媽的伯恩和她的混漲律師老爸在人群裡的時候。
我開始從衣服裡聚集蟲子,但我停了下來。這裡把它們拿出來也沒用,兵器大師可以用那裝進戰戟的加大火力電蚊器把一半蟲群殺掉。我把蟲子移到室內的位置。
我仍因那次打擊,身體動搖,對我裝進假面服的護甲心懷感激,我成功抓住自己底下的多餘鐵鍊,把它捆在我後方的陽台扶手上。該死的,如果兵器大師想要我,他得親自來抓我。
鐵鍊變得緊繃,兵器大師大力扯了兩次之後決定靠近過來,比增加對房子的傷害還要少麻煩。他走過來縮減距離,只在將他的鐵鍊從陽台扶手鬆開後停了下來。他將鐵鍊收回,把我和他之間的兩、三呎距離拉近。
「掠翅。我以為妳會更快投降。」
沒有其他人在可以聽見的範圍。「不管我在哪一邊,我真的都不想要進監獄。聽著,我的提案仍在。我幾乎有了我從這些傢伙們所需的最後一點細節。」
「某個妳幾週前曾說過的東西。」他回答。
「兵器大師,你沒有其他方式能挽救這個情形了。」我盡可能在抓鉤鐵鍊纏繞我的情況下站直。這該死的東西真重。媘蜜就算讓自己被打到無法行動,還是非常努力地,讓我們知道兵器大師的地位對他來說有多重要。我需要利用這點。「你唯一不會看起來無能的可能性是,如果你能說我溜走是因為你讓我走。今晚發生這一切是因為你讓這發生。因為讓我走,就表示我可以得到是誰在雇用暗地黨、誰給他們資金、設備和資訊來源的情報。然後你就來打掃乾淨,有兩個超級反派團隊就在短短一週內解決。告訴我這聽起來不好。」
兵器大師考慮了一陣子。
「不。」他回答我。
「不?」
「別期待妳提醒我要逮捕妳,和妳的同夥今晚的嘩眾取寵,之外的事。」他搖了搖頭:「再說,妳插翅也難飛……」
他搖晃了下我,好像確認著到底誰才是籠中鳥。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兵器大師,你是對的。」
「當然是了。」他心不在焉地,說道,一隻手把我推向扶手抵住。他的抓升鉤解開了我,重新改裝成,我猜是在我穿假面服的第一天,同一個將龍用不銹鋼鋼管固定在地面的設定。它的形狀就像一個矩形,有兩個發出電力弧的「U」形金屬帶在兩側,「U」的兩端發光灼熱得足以將任何被抵著的表面融化。
「這從我們踏進房間時就已經結束了。」我結語。
差不多有七百隻大黃蜂從我的護甲板底下爆炸,全爬到他身上,無情地又咬又螫,湧入他的面鏡之下,鑽進他的頭盔、他的鼻子、嘴巴和耳朵。有些甚至爬進他的領口,爬上他雙肩和胸口。
我將自己往他的戰戟尾端一擲,讓我的身體抱住戰戟。他一隻手提起我和戰戟兩個,把我們重重甩在地板。又一次,我感覺到電力的捲曲蘇麻感捲襲過我,又加上我的肚子夾在戟桿和地板之間的痛楚。我今晚第二次,對於加入假面服的護甲板十分感激。
他重複這個步驟,把我舉起離地面兩、三呎,接著再次把戟桿和我打下。第二次之後,我得要努力爭鬥才將自己擺在戟桿之下預期第三次衝擊,知道他承受大黃蜂的猛攻會比我承受這傷害還更久。
救援不能再更晚一秒來到了。
母狗、失去意識的媘蜜還有布魯圖斯是第一個越過陽台邊緣的。布魯圖斯在經過時撞了下兵器大師,把那男人擊倒失去平衡,給了我所需的機會把自己扶起,然後把戰戟從他手中拉出來。我雙手握著戰戟,而他被大黃蜂群干擾到完全沒察覺。
我把戰戟從陽台邊緣扔下去,回頭往裡面走的門跑去。我在猶大跳過時抓住戰慄他伸出來的手,好讓他能把我甩上他身後。
我們從陽台邊緣跳出去時,我往身後看,見到安潔力卡和攝政也跟著我們。戰慄正在消去她的黑暗,讓我們製造的混亂,與成功逃脫,對我們的觀眾而言更加清晰。再說,我的目標是要羞辱他們。
因為相同理由,也許還有一點點針對兵器大師的惡意「幹你娘」--他讓這整件事都變得比原本必須的程度還要困難,我把蟲子留在它們的位置,也把它們安排在那個陽台的右側牆壁和前面的地板。一半聚集成兩個巨大的箭頭指向陽台的門,一個在地板一個在牆上,而另一半則組合成粗體字母拼出「走吧」。
我將我的雙手繞住戰慄,緊緊抱住他,預期我們會落在附近的屋頂上,所以也把這當作告別的擁抱。
有很大的機會,這會是我作為暗地黨的最後一個工作了。
ns3.19.60.207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