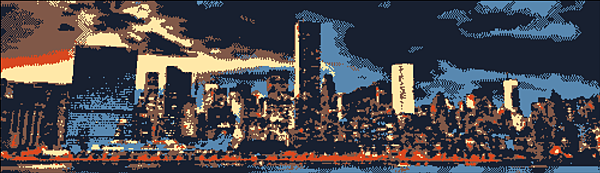 x
x
Disclaimer4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0yhpkz72py
【原作者贊助連結】
假若和議人不明事理,他就可能以為,在此處辦這場小聚會的唯一目標是要惹他嫌。
等等,他確實很明事理。是媘蜜。她這麼做就是要惹他嫌。
佛斯伯格畫廊。這棟建築曾有著閃閃發亮的、毫無對稱感的玻璃與鋼鐵建材。現在它成了粉碎後的殘骸。建築設計幾乎沒有韻律或理性可言,而要找到建築裡的房間,也很麻煩。
他走上樓梯時,右邊、六樓高處有隻翅膀突出大樓側牆,就像設計上的腫瘤。還有碎歌鳥的攻擊損傷,唯一殘留在大樓上的玻璃,有如冬霜散落於地板上。建築側牆那塊令人不舒服的生成物,也遭受了些損傷——那比較可能是震動造成的,而非玻璃本身損壞這棟建築——強化工程有撐起那隻翅膀,卻只讓它變得更醜惡。
毫不優雅,毫無平衡。
他的超能力會立刻開始提供答案跟解方。他在戒備中,最初想到都是進攻跟傷害。他就像能親眼看到般,能看到有個鐘擺藏在這棟樓的鋼骨中,在原地搖擺,他也能聽到金屬跟金屬的敲撞聲,有如劍身抽出劍鞘,只不過是十二倍響亮。
在恰當設計下,那股衝擊會很清脆,幾乎柔和。他的敵人被那隻翅膀隔開,也會發出更多噪音,在支撐整棟樓結構的柱子的強化桿與鉚釘都被切開時,大聲尖叫。結果,他就會看到敵人死去,這棟樓被改善——變得更平衡。
用十分鐘畫出藍圖。八十到一百分鐘的勞動——要看工匠的技巧有多高超。他自己做的話,就要兩百四十五分鐘⋯⋯而他自己做的話,成果會更堅固、品質更好、效率更高。薪水得付一千四百元以上。
不實際。讓他的敵人走去那片區域會很困難。假使他們有任何理解力的話,就不可能達到目標了。
他打發掉那個想法,但其他想法已經淹沒那個位置:他跟他進攻側翼位置的兩位使節,以鋼纜線連接附近建築。鐘擺不只一個,而是有七個。
一個鐘擺會切掉那團腫瘤翅膀。翅膀會拉出鋼纜線,掛在兩棟建築間。在正確角度下,翅膀會俯衝過最近的兩棟大樓之間。正確的機械、一條纜線,在正確時機脫落,會讓他們轉變俯衝方向。在地板的角度、向心力下,他們仍不會完全失去平衡。
他們若細心縝密,甚至可以踏開那個平台,就好像他們走下一個滑雪纜車。那片翅膀之後就會甩上附近大樓的殘骸之中,被乾淨俐落地處理掉。佛斯伯格畫廊會被撕裂開來,鐘擺的刀刃會將鋼鐵切開,機械裝置的重量跟運作也有放大損傷的第二目標,扯開個別零件、推動整棟建築的徹底毀滅。
不得體的佛斯伯格畫廊,被夷為平地,而他許多敵人都待在室內,他跟他的使節就會在下車的位置觀看它被剷平。
他痛惡髒亂,但不論是要擦去內臟,還是要看到平地清空殘骸,事後的清理都會十分讓人滿足。
三十二分鐘畫出鐘擺的藍圖,也要搞清楚最佳效果所需的機械序列。三百到三百四十分鐘設好裝置。他能預測到,不加上人員薪水的成本會超過一萬一千元。材料本身不會特別昂貴,他能從自己管理的任何生意裡,用大量折扣取得那些材料。
這樣會稍微更實際,但並非不可能。他今晚,沒有時間可以設置那東西。而就算那麼做不會有多少成果,也能打造出一個優雅形象,稍微更能撫慰人心吧。
他很快就轉離那個暴力的點子,然後其他想法便擠入他的腦海。那片向外延伸的翅膀,從一個人工囊腫,被轉變為一道橋樑,與此相仿的連接橋覆蓋整座城市,每道橋樑跟連結,將各個地方設計成一連串的斜坡。建築風格跟高度都會因為一陣搖晃而改變,被推動的坍塌進程會變成流體,成了一陣毫無縫隙的波浪⋯⋯
和議人稍稍閉起雙眼,盡他所能地擋開這個想法。這沒有幫助。他感知到建築的整體,也能想像自己重新建構這棟大樓,移除掉那突出的部位,以其填滿建築的中心質量。他用自己的能力看過各種意義的可行性:金錢、資源、時間、人員,但現在這種思考就只會造成損傷。
他睜開雙眼,搜索某些東西來將他的思緒轉開這棟建築的惱人設計,但他只看到玻璃碎片,碎片不和諧地,散落於建築內部各處。有些碎片被踢開,好讓人們能住到畫廊裡,但那些一堆堆、大團、大塊玻璃與塵埃與建築殘塊,都不會比較好。他瞥見那些,他但願自己沒看到的一團潮濕的睡袋,還有散在各處的救助物資。
畫面閃過他腦海。一片纜線網,被墜下電梯井的重量給繃緊;那與玻璃碎片的掃除跟電梯井裡生活跡象,完全一致。這些纜線也會抓住他的敵人,在撒下玻璃碎雨的時候嚴重扯傷他們。在漫長的墜落與鋁熱劑相配合下,就能將亂屍降解為細緻、乾淨的粉塵,連較耐打的假面也無法逃出生天。
不。這種思考沒有建設性。
在最高的樓層裡,將塑膠玻璃跟大量溶了高濃度二氧化碳的水,加上肥皂水的媒介,沖過這棟大樓。讓大樓搖晃,最高樓的水就會清掉肥皂⋯⋯
或將玻璃碎片排成一個萬花筒狀⋯⋯
「檸水晶,奧賽羅。」他說,打斷自己的思路。「讓我分心。」
「我對這個觀景點,感覺不是很舒服。」檸水晶。「這樣爬樓梯只會讓我們疲憊,而且這個地點也不適合我們任何一個超能力。這讓我們處於較弱的位置。」
「叫長官。」奧賽羅低語。
「⋯⋯長官!」她補充時已經遲了。
和議人爬到她正前方的樓梯。那普通來說,不可能發生,但這裡就能輕易做到:轉身、用他拐杖裡的折疊刀刃,靈巧切開她的喉嚨。安靜,有效率。
他停在樓梯一半處,面對著她,看到她沒有受傷、毫無傷痕。他的檸水晶,年輕、金髮,戴了一面有橘金色飾釘的面具。她髮型風格完美無瑕,化妝毫無缺陷,黃色口紅搭配她的穿著,不會過分搶眼。
和議人的左手彎向右側,兩手放上那根華麗手杖。
她停了下來,瞥向身旁的奧賽羅。「我很抱歉,長官。」
「所有人事物都在妥當的位置。」他說。「不只是物理上的位置,還有社會上的位置。禮儀與對各別地位的認知,都是至關重要。」
「我知道的,長官。我沒藉口可言,但我在走路跟爬樓梯時累了,我也在思考著,我們被襲擊時的策略。我會努力改善的,長官。」
「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做到更好。我們都要致力改善。而退步,就會是個悲劇、危險的過失了。」
「是的長官。」
他彷彿在看著底片上的自己,看到自己將她推下樓梯。樓梯沒陡峭到這趟墜落會殺死她,但那股痛楚會強化這個教訓,而且懲罰的這個行為,也能幫他強調重點,讓他能安靜沈思。
但在那些瘀青、割傷跟任何摔斷的骨頭下,她會間間斷斷嘗試壓抑痛苦的聲響,重新加入他的行列、走上樓?那樣只會更糟糕。有更多騷亂。
這些思緒都如此尖銳,讓他難以分辨現實與思緒。他換了握著手把的手勢,盯著她的雙眼。她仍站在他前方。
他雙手些微動作,她的肢體語言就變了。她脖子跟肩膀的肌肉變更緊波,呼吸頻率改動。她說:「長官⋯⋯」
「噓。」他說。她沈默下來。
他左手托住檸水晶的下巴,雙眼從未離開她的眼睛。還有更多反應:她雙眼閃動,在她繃緊著要維持視線時,僅僅動了幾公釐。他手腕能感覺到她在緩緩呼氣時的吐息中的溫暖,她在轉變重心、保持絕對靜止時,極其細微的動作都會碰觸上他的手。
他的拇指撫過她的臉頰。動作輕柔。他知道她每早晨都會花上一小時照料皮膚,另一小時保養頭髮。他與她不同——他的視線毫無動搖、清楚而確信。在他視野邊緣,他能看到她胸膛起伏。他生性無慾——沒有那種基礎、狂野的慾望。交媾的想法不會出現——交媾中會有髒亂。但不論如何,她也是個貌美之物。他能以美感視角,來欣賞她。
不過,檸水晶掉出了原位。一個方形釘子,正巧歪曲到它不會滑出那為這顆釘子所設計的洞口。衝突激發,讓她所有正確的其他部分,都被染上灰白死色。
他手指移動,追撫她顎邊的輪廓、划上她下巴,切開她喉嚨的想法侵佔了他的思緒。迅速、乾淨地割斷重要血流。他能看到她在伸直喉嚨、努力保持脖子絕對靜止時的緊繃線條。
不過,這又一次,會造成混亂、分崩離析。血是那樣雜亂無章,就算他可能會滿足地用自己一天中的三十分鐘,在一片更安穩的區域裡清理髒亂,其他人也會看見他,那也會將太多事物推出平衡狀態。
沒有正確答案,而這件事使他很不爽。
他若理性思考,會知道自己太過煩躁。這個地點——甚至連這座城市——都不適合他。他沒辦法行動,沒法行動就會影響到他對小事的回應方式。
他在考量著自己的選項時,手指一根又一根地,不再碰觸她的下巴。等到他放下食指,他就已經決定好了。
「檸水晶,妳是我最好的使節。」他說。
她的呼吸比她以為的還要更粗重一點,那股拉扯她全身的張力也被放鬆。潮紅碰觸她的雙頰:「是的長官。」
「我不想失去妳。」
「是的長官,我會竭盡所能確保你不會有理由失去我。」
「還請這麼做。」他說。他注意到臉紅已經散播到她袒露的鎖骨。不是出於恐懼或憤怒。而是另一種基礎的情感。「檸水晶。」
她瞥向他。
「冷靜下來。」
「是的長官。」她呼出這一句話。
他看向奧賽羅,後者穿黑色西裝、戴著一張乳白與漆黑二色分別開來的面具。他在和議人與檸水晶說話時,沒有作出評論或畏縮。
和議人轉身,再次開始爬樓梯。「加快腳步。我拒絕遲到。」
侵入性想法,持續在騷擾他。他將其描述為,十份近似於站在火車站台上:在快速移動的人流前方的月台上,頓時想向前踏出腳步、想看看什麼事情會發生。
然而那些想法本身會更為尖銳,更有重量,實際而毫不飄渺。他的超能力會解決問題,所有問題都會要求一個解方。不論他想不想要,那些解方都會出現,單一步驟或上百個步驟的計畫都一模一樣。這個超能力也永遠不會停止。
每個缺陷都需要糾正,每個不平衡都需要重新分重。中庸也能被抬升到偉大。
問題越大,解決的速度就越快。他花一個下午就解決世界飢餓。六個小時二十六分鐘,一手拿著手機上網,他就能理解那個問題的關鍵要素。他之後用九個小時只打字、追蹤明確的數據,就草擬出一份文件。一百五十頁,已經做好格式、畫面整齊,詳細闡述誰需要做什麼事,還有其中的成本。
那只算是份大綱,還有空間能擺放詳細講述細節的文件,但基礎概念都有了。簡單,慎重,無可辯駁。所有重要國家元首都已經被考量在內,考量到使他們配合的必要措施,考量到他們各自的天性跟所處區域的政治風氣。產品、分配、金融跟物流,所有藍圖都已經勾勒好,以清晰、簡單的語言提出草案。耗時十八年,耗資三點一兆。成本沒高到不可能達成。也要一小群人做出極大或中等程度的犧牲。
就算他交出那本資料夾跟所有成果,他的雇主還是比較在意他上班遲到。他老闆根本沒讀過資料夾,就說這不可能實現,然後要求和議人回去工作。他這種腦袋,待在PRT裡監管經濟的辦公室,尋找著那些試圖操作市場的預知、訊思能力者。
那只是其中一項不平衡,一項不規則,但那也是個很重要缺陷——這使他很煩惱,需要個解方。他必須證明這個計畫有可能實現。
所以他抽走了他的部門在管的資金。重新安排反派跟離群者試圖操作的資金,並不困難。這也是為了毫無否認的良善,作出一個灰色地帶的邪惡之舉。他也完美無瑕地掩蓋起自己的蹤跡了。
在這個過程中,他沒能算到他最新一位同事的所有才能——訊思型超能力會彼此干擾,而即使他的能力有特定缺陷,也能幫忙他們一起工作,那位千里眼就發現了他的所為。他被抓到,被關進監獄,之後也被他事先聯絡的越獄專家救了出來。
多之後,他就在這。他所接觸到的人都沒接受他的點子,一個個政府都無能讀完他送去給他們的文件。沒有人對聯合國或任何重要的政治組織提起他的工作。他們都太想要保持現狀。
他的諸多計畫,都沒顯著地靠近終點,但他已經有聯絡人,他也有財富,之後還有一長段路要走。他會走那條緩慢的路線,穩定前往勝利。那個跟世界飢餓有關的資料夾有被擴充,還有其他附加的資料夾寫了詳細細節。其他好幾個資料夾也被加進來,每個都會處理重大議題:疾病、人口、政府、能源跟氣候。他花了一小時跟半天,確保所有內容都更新到最近的經濟跟國際政治的情勢。
他們近日在波士頓與屠宰場九號交火,結果是一場挫敗,但他仍有信心。二十三年就能看到成果。二十三年就能為世界帶來秩序。每一步都會走向那些成果。
就算這裡的景象跟人們都會使他焦躁,也一樣。
他們抵達頂樓,與爪牙面對面。七位超亞人類,身著刀劍、尖刺跟脊針直豎的假面服。他們想辦法將自己打敗敵人時的戰利品帶在身上,看起來也不會原始。牙齒、眼珠、乾燥屍塊跟骨頭組成了他們的假面服——那些主題都預示著,他們對任何怠慢都會展現出侵略跟暴力。
和議人抓緊他的手杖。他渴望了結他們,渴望到手癢。他的心思燃燒出數百個如何動手的點子。陷阱、計謀,讓他們彼此對立,或要用房間裡的其他人來對付他們。
爪牙沒擋住和議人領著他兩位使節、繞過他們群體周邊。房間沒有窗戶,風卻將極其細微的玻璃碎片吹過磁磚地板,反映著房間周圍的泛光燈的光線,間歇閃閃發亮。
「和議人,歡迎你。」媘蜜跟他們打招呼。
他掃視長桌末處的那群人。他們在力量展示上毫無放水。他們身後至少有六隻狗被鐵鏈捆著,每隻狗都已被母狗的超能力給變形、漲到巨大體型。他們的數量,還有一隻巨大的蜘蛛跟蠍子——那兩者都裹著黑色布料。是絲線?掠翅的絲線?
攝政站在淘氣鬼身旁,他的假面服主要是白色,與後者的黑色假面服對比。他們似乎正在低語交談。
母狗戴著一個看起十分像她的狗的面具,她身上的黑色夾克兜帽與領口邊緣有著厚實、蓬亂的軟毛。連在較大隻的變種狗吼叫、在她頭部幾吋處咬著尖牙時,她也毫無畏縮。那隻生物的憤怒是指向和議人,而不是她。
瓷偶的衣著風格,從和議人研究她時所見的,已有改變。她的頭髮不再是金色,而是黑色,她的連衣裙也一樣配合黑髮。她戴的白色面具側邊有一道從上至下的裂縫。她跟其他人比起來非常小,而她坐在桌旁的方式——雙手交疊,彷彿她毫不想參與這場會議——就幾乎閑靜端莊。
媘蜜則正相反,她在一個大螢幕旁,坐在布料製的蠍子上。她漫不經心,頭髮蓬亂,歪斜側坐的肢體語言也十分無禮。
他得努力無視她。他將注意力,從那些人身上,轉向談判桌上的領頭。戰慄站在一張椅子後方,一手放在椅背上,惡魔似的臉龐被絕對漆黑環繞。掠翅坐在桌子末端,背對著她的戰力,看著房間各處。蟲子籠罩住她肩膀以下的身體,但和議人能看到一件披巾,還有隱約現形的保護性裝甲。她面具的黃鏡片,或那遮掩她臉面的大片黑布,都沒曝露出她的任何心情表情。他所見到的形象,不是在誤導人,就是她努力做出那張面具——她蟲顎般的裝甲突出、使她的下巴線條更清晰,輪廓更鮮明。
和議人打發掉媘蜜的問候,對掠翅說:「我們總算見面了。晚上好。」
「晚上好。」她說,嗓音被這區域裡的無數嗡嗡鳴響所擴大。「請坐。」
他在那十二呎長的桌子中央坐了下來,他的使節們則坐在他兩側。
終徒肯定在他後方不遠處——他們在他坐下後,不到一分鐘就抵達。華利弗跟埃力格斯。
華利弗戴了張外貌十分華麗、沒有眼洞的面具——那是張閉眼女性的上半張臉。在那面具底下,他有個淘氣、永久嘻嘻笑臉,刺青將他的嘴唇塗成漆黑、延伸他的嘴角。刺青描繪的尖牙,刺出薄唇,幾乎觸及他的下巴;尖端上下交替。他的假面服幾乎帶有陰柔氣質,白色與銀色羽毛濃密裝飾著那件緊掛在他窄瘦身軀上的、飄動的白色衣服,還有一件束腹拉緊了他的腰線。
那套假面服,無疑是要召喚希魔翮的形象。那太粗糙了。埃力格斯的假面服沒那樣細緻,比較適合跟人扭打,但一樣,是想召喚終結召喚者伯希魔斯。黑曜石鬼角彎下他的後腦勺,沈重裝甲的質地看起來像犀牛皮,他雙手手套也裝設了爪子。
「華利弗、埃力格斯、爪牙的成員,現在我們全到這裡了,我會邀請你們坐下來。」掠翅說。
「我們為什麼要聽妳的?」華利弗問,他嗓音跟裝備十分不相稱,些微帶有南方鼻音。他靠在一張椅子上,雙手交疊於椅背,姿態嘲諷。
「若有人在這種會議裡引發騷動,傳統上,會議將祭出暴力性報復。」掠翅說。「而那通常會牽扯入在場的所有勢力。」
「我又沒說我想搞起騷動啊。」華利弗說。「我是在想,我們幹嘛聽從那個女學生。我很肯定這裡所有人都有看新聞。劊子手【原文Butcher】,妳有看新聞嗎?」
「是啊。」爪牙的領袖回答。那個女性走出爪牙眾。她很優雅,脖子跟四肢修長,頭髮綁成高馬尾。她的面具跟裝甲都有著亞洲風,不過那套假面服妝刺上好幾條缺德的倒鉤刀刃。還有更多不和諧的設計:三顆褪色的頭顱串在她一側肩膀周圍。
那個假面服很不對稱,缺乏和諧,同時想做到太多事情。有武士風,頭顱獵手,血滴子。全都不符合她的頭銜:劊子手。
好幾道影像閃過和議人腦海。有好幾個方法能摧毀那件假面服,跟穿著那件衣服的人。考量到她的身份,實做起來會比表面看起來的,還更困難。
她好像要強調和議人的思路,毫不費力地抬起一把加特琳機槍,將其放上桌子。那把武器的質量,頓時直接使和議人納悶著長木桌另一端是否有被壓翹。
那個女人刻意地拒絕了坐下的邀請。她只說了一個詞彙,卻以行動成功表達了許多意義。
「真丟臉呢。」華利弗大聲地若有所思。「真的,我看不出妳為什麼能坐在這張桌子的首位。一個十六歲女孩,霸凌的受害者,那可無法召出一個非常強勢的形象,對吧?」
「假如所有人都同意暫時取消通常性的規則,我就十分樂意跟你的隊伍直接對打。」掠翅回答。
「妳當然願意了。你們人數多過我們啊。」
「就只有我。」掠翅回答他。
「是這樣嗎?」華利弗微笑,考慮著。
和議人審視這個情形。華利弗是個隱陌型能力者,較沒有隱藏的能力,而是有著詭計的能力。他只需要用裸眼看向目標,戰鬥就會結束了。他會讓自己的風格追隨希魔翮,真的不會讓人太驚訝呢。他們的能力效果十分相似——受害者通常在意識到時,就已經太遲了。
然而掠翅似乎不怎麼在意。她是個誘餌嗎?空的假面服?不對。
是陷阱?
和議人仔細觀察著華利弗周圍的區域。他會以她的能力做出什麼東西?
他看到了:那幾乎無法被看見,然而在正確角度下,它會反光。絲線環繞著華利弗,從他的束腹繞到他的手肘跟膝蓋。
絲線全部連往窗戶。假使它們一緊繃,華利弗就會被拖到室外。考量到絲線綁得有多穩,他不是會被吊在線上,就是會落到外面的街道。
「華利弗。」合議人說,他面具上的層層機械在移動、模仿他的微笑:「相信我,我會說,你已經輸掉這場戰鬥了。」
「是這樣嗎?」
「假使你想看看結果,我就不會暴露出結局。我會少一個威脅需要擔憂。但如果要提供我的建議,我認為,考量到這個情形,她給出的回答明顯十分合理。看到這會如何發展,我就對她有了敬意。」
「那你就是個蠢貨啊。」
「不論如何,我不會在此寬恕戰鬥。那會建立惡質的先例。」
「是啊。」劊子手說。
華利弗皺起眉頭。
「那麼,就這麼辦吧。」掠翅說。
和議人仔細觀察他。他能看到泛光燈後方陰影裡的蟲群,無疑是預期著一場戰鬥。它們的存在,幾乎就像蟲子直接爬到他身上,使他十分痛苦。他在看到那些玻璃時就已經有各種問題了,現在還要面對活物。他知道自己只要對他的使節團下達一道命令,就能讓它們停下來,讓它們走開。這也不是說,那是其中一個選項呢。
他瞥向掠翅。「我想,妳我都知道妳會在戰鬥中獲勝。但那個結果會多麼不可變動?妳坐在權力寶座上。每天都會有更多反派過來。妳有準備殺死所有人?」
「這是某種鬥智遊戲嗎?」華利弗問。
「這從任何方法來看都不是要鬥智。」和議人回答。「我只是很好奇。她的回答也會決定今晚這場談話到底有什麼樣的語調。」
「是的。」掠翅延遲給出回應。「但我希望維護那些不成文的規則——就算近日,那些規則已經被任意濫用。謀殺應該是最後的手段。」
「我懂了。」她手上還有其他陷阱嗎?是在房邊邊緣上的蟲子?「我可不可以詢問⋯⋯不,等下。別告訴我。我如果能自己找出來的話,就更好玩了。」
「非常好。現在,如果各位坐下的話,我們就能開始談了。」掠翅說,將雙手手肘擺到桌面上。
和議人注意到桌子並不正。桌子在房間裡被擺歪。好幾個解方閃入他的腦海:從站起來、將桌子推正的簡單方法到用平滑落錘砸入建築牆面,各式各樣的方法。
不行,他必須專注。他能以搞懂掠翅的保險計劃,來讓自己分心。
劊子手似乎下了決定,但這對她來說很普通——她會花些時間反芻深思。更好的說法,是討論。她坐在掠翅對面。她個子很高,高出那把巨槍一顆頭。她的追隨者都沒有坐下,而是半環繞著她,映襯著掠翅她的隊伍。
「華利弗。」掠翅說,她的嗓音變得更發不祥,暗示出潛伏在房間邊緣的昆蟲數量:「不坐下,就離開。」
華利弗環顧房間四周,聳了肩,好像他不再在意,便坐了下來。埃力格斯也跟著他的信號行動。
下一瞬間,和議人就理解了掠翅的保險計劃。絲線不只有連接上華利弗,甚至,還連接上他。她將絲線連上傢俱。
那張桌子。她可以用每一條擺在磁磚間隔裡、近乎無法被看到的絲線拖起那張桌子。她這麼做,就能將任何一組人馬夾在桌子與牆壁間,或是讓他們幾乎如同墜落般,想抓住某些東西。
那她會如何拖動桌子?還有另外一隻變種狗?用上秤錘?
不論答案是什麼,和議人都古怪地對自己感到欣喜。他卻完全不擔心這個陷阱的危險性。
「我們來談生意吧。」掠翅說。「不管你們喜不喜歡,暗地黨都已經有了這座城市的優先所有權。」
「只有一周半而已啊。」華利弗說。
「優先所有權。」掠翅重複道。「我們有規則,而如果你們打破這些規則,我們就會被迫出手。」
「我已經跟媘蜜談過妳的規則了。」和議人說。
「你當時可以接受我們提供的條件。現在我們要劃定的規則有些改動。不准殺人。越過那條線,我們就殺掉你。我們隊上好幾位成員都能做到這一點,也不會讓你們察覺到我們就在附近。幸運的話,淘氣鬼就會在你不知情時割開你的喉嚨,或是攝政讓你其中一位部下從背後捅你一刀,你很快就會死去。如果你不幸運,母狗的狗兒們就會把你扯成碎片,那是段漫長、拖沓而痛苦的過程。如果你非常不幸運,你就會獲得最糟糕的、兩種情形的綜合——你們會要對付我。」
「假使有人必須死呢?」華利弗問。「有些時候謀殺是必要的啊。」
「你來找我。我來決定。」掠翅說。
「那些都不是新條款。」和議人說。「媘蜜差不多提出了相同的內容,不過沒那麼多威脅。」
「我根本沒說完。財產。我們會找出你們地盤裡獲得的任何財產。你們買地付多少錢,就要給我們三倍。這也包括買地的價格、租金跟稅金。如果你沒繳房地稅或租金,我們依然預期你們繳出相稱的價格。」
「很貴呢。」和議人說。
「你先前可以接受我們的提案。」掠翅回答。「如果你們想要跳脫這些約束,你們任何人都能將自己的組織納入我們底下,直接聽從我們的指揮。」
「那麼,這就是場消極接管了。」和議人說。「妳是想壓榨我們,直到我們屈從吧。」
「我非常、非常倦於人們跟我說我的意圖是什麼呢。」掠翅回答他。「我們的地盤邊界各有標誌。運送任何非法物品,或傷害某位在這些區域裡的人,我們就會報復。瞄準我們任何人,我們就會作為整體報復。」
「這聽起來不會讓我們有多少活動空間。」和議人回答。「我還沒看過一片區域沒被你們標註成地盤。」
「那你就理解我的意思了。」掠翅補充:「下一個重點:在任何終結召喚者事件裡,或可能導致世界終結的事件裡,你們會派出一半的超能力成員,或三位成員來協助戰鬥——採用人數最多的選項。」
「這也太可笑了。」華利弗說。「妳要我們去跟終結召喚者戰鬥?」
「要你去?我沒那種期待。」
「妳是想討架打?」華利弗說。
「我是在給你們每人服從、離開或戰鬥的選項。」掠翅說。「使節團會接受這場交易。他們不會喜歡這麼做,和議人甚至會因為我的能力跟我不怎麼能被預測的天性而痛恨我,但他們會接受的。」
「是這樣嗎?」和議人問。
「沒錯。你會接受,因為你有資源能在他們偵察完傳送門另一端後,開始拉關係、做生意。你不會在大老遠跑來這裡之後,因為自己不喜歡這些條件而離開的。」
「我還有其他選項呢。」
「跟我們戰鬥?你只有兩個部下存活過波士頓的襲擊。就算他們再強,你也不適合戰鬥。你會加入我們,因為那是距離你真正想要的東西的最快路線。」
啊,和議人想著。媘蜜已經告訴她了。
這讓人生更輕鬆一點點,而在非常不同的方面,也變得更困難一點點。
掠翅靠著椅背,一隻手歇在桌上。「你是跟媘蜜說了什麼?所有人跟所有事物都有其位置?」
「多少就是那樣。」
「你的位置不是在戰場上,這與暗地黨正相反。你是要在城裡,建立基礎建設、為你的長期計劃收集資源。而在這個原因下,你就會接受一份昂貴的租金,跟犯罪活動的限制。」
「妳卻要我冒險讓好幫手,去跟不死殺人機器,打好幾場毫無結果可言的戰鬥。」和議人說。
「那也是其中一個代價。」掠翅回答。「有要跟終結召喚者戰鬥的限制,我就不認為終徒會接受條件,但我也懷疑他們會在城裡待太久。」
華利弗從桌旁站起身。埃力格斯也跟著他。他們一同沈默地,大步走出房間。
「那樣羞辱他們,」和議人評論:「是有點太草率了。」
「我沒在說謊。淘氣鬼跟天國很快就會處理掉他們了。」
「華利弗比妳以為的還要狡詐。他是個自負的年輕男性,很衝動、幼稚,但紀錄顯示出,他在努力思考時,會顯得相當狡猾呢。」
「不重要。」掠翅說。
「妳這麼認為的話,就這樣吧。」
掠翅將注意力轉向另一位領袖。「劊子手?」
「不行。」那個女人回答,從座位上起身。
「我也不認為可行。妳有其他事情,希望在我們全員聚集時提出來嗎?」
「妳會死。」劊子手說。「妳殺不了我。我就會贏。」
這是她到目前為止最長的一句話,她轉身離去。
「這些都不會是好敵手。」和議人評論道。現在,就只剩他的隊伍跟暗地黨了。
「我們會撐過去的。」
「第一代劊子手有超能力量、耐力,還能在遠距離時,對敵人造成大量痛楚使人心臟麻痺。他的其他能力只有在之後才變得更迷險。他被部下殺死,而那個男人之後才被認定為第二代劊子手,繼承他某些超能力跟部分的意識。」
「第三代劊子手也繼承那些東西,還有二代的超能力跟意識。」媘蜜說。「不過,他是個英雄呢。」
和議人難以不怨恨她這樣發言時不遵守說話順序。她的嗓音迴盪在他耳裡,就像每個音節都是一次鐘響,每次敲響時都愈來愈劇烈。不遵守順序,沒有同步,跳出了自身的位置。
他咬住舌頭。「是的。在那位英雄腦袋裡的兩的聲音,一起將他逼瘋。他早在自己死去的那場戰鬥以前,就已離開這個世界了。爪牙收回那個超能力,此後的那份超能力遺產大都是留在隊伍之中,每個繼承者都會承繼所有前任的超能力。而那些意識嗓音,只會跟正統繼承者合作——必須是他們隊伍的成員,在正當的挑戰中擊敗領袖。」
「這一隻是哪一代了?」攝政問。
「十四代。」媘蜜說。
「這個是十四代?」攝政問。「也就是說她有十三組超能力?」
又一位,跳出自己位置說話的人,和議人想著。
檸水晶在斜眼看他。他與她對視,些微搖了頭。
媘蜜回答:「只有每一代的一小部分能力。別忘了,她腦袋裡有十三個聲音,會給她建議協助她搞清楚事情,再加上所有她能使用的超能力。她的攻擊一定會擊中目標。子彈會在空中轉彎,刀劍也會彎曲,她在攻擊飛到夠遠處之後,就鐵定能打中喔。」
她從蠍子頭部跳下來,走過談判桌,直到她正面面對和議人。
掠翅身後的暗地黨,一個接著一個坐了下來。現在,其他隊伍都離開了,他們想讓自己更舒坦些。攝政將靴子翹上談判桌,擺到淘氣鬼正對面,後者則將他雙腳推開。
過度親密。太放肆了。
和議人一陣子緊閉雙眼。那張桌子現在,從比喻的意義來看很是不平衡,但這感覺十分真實。「我不記得有任何人給妳坐下的許可。」
媘蜜抬起眉毛。「我不記得有任何人給你抱怨的許可。我們的地盤,我們家,我們的規則。」
我能殺掉妳。用汽車炸彈,或其他陷阱。我能操縱英雄去追殺妳。在我指揮我的使節團時,他們就會在戰鬥裡獲勝。妳會在面對我能做到的事情下、在我能施加的壓力下崩潰,全世界的所有人事物都會忽然變成你的威脅,而我則在拉動絲線操引那些威脅呢。
他深呼吸一口氣。說出那種事情,就會有太多風險。他以自己最有耐性的語調,就像在對一個滿心好意但誤入歧途的八歲小孩,解釋道:「我是在說事情應當的作法,媘蜜,妳懂嗎?」
媘蜜就像她被甩一巴掌似的,怒氣衝冠。
「夠了。」掠翅說。她的嗓音很安靜。
那股緊追而至的沈默,同時很令人驚訝跟放鬆。她能掌控著她的部下。很好。要控制住這樣心神不定的人,會需要天份。
他仔細觀察著那女孩。就算在她的身分被公諸於世後不到十二小時,她仍十分冷靜。她的蟲子⋯⋯它們這麼毫無秩序、使人煩躁,但現在他看它們,那就像她正穿著第二層衣服——他能看出它們全體的陣型,有著秩序。
掠翅很冷靜、鎮定、合理,但也願意在必要時下重手。很聰明呢。她有向一位真正的領袖般,在不同尺度上思考。
「你會接受這場交易嗎?」掠翅問。「我最好現在詢問,因為你的回答會決定接下來的對話的語調。」
「我接受。」他回答。她是正確的:他在這件事上真的沒有選擇。他之前有接受過更糟的交易,以及更惡劣的情況。「我預期我們會有摩擦,會有意見不服,但我們也會找到共通點。妳跟我是非常相近的人呢。」
她沒有回答。那股沈默裂展;他指尖不由自主地抽動,危險地靠近那個,能將他的手杖轉變為武器的扳機。
「我這麼說。」他說,盡自己所能地保持冷靜:「是在邀請回應。」
「而我也在花時間,思考要如何回應。」她回答。
以連接詞開始一句話。他咬緊牙關、微笑,面具移動、模仿那個表情。「不好意思呢。」
「我們來談細節吧。」
■
這座城市太骯髒。太混亂。那些想法再次侵襲,堅持不斷地壓抑著。壓抑到了它們開始重複、來回循環。他得做某些事情來打破循環——他能在工作桌前,花時間整理資料夾裡的企劃,或消除掉某部分的混亂要素。
謀殺不可行,但還有其他選項。他之前有把假面送給樣板【原文Yàngbǎn】。那比謀殺還要有建設性。也會更乾淨。那樣,也能跟中聯帝維持合作關係呢。
「說話。」他在數分鐘的沈默後說。
「長官,我們可以打倒他們。」奧賽羅說。「任何一隊人馬,都能被我們處理掉,但不能同時對付兩隊。」
「我同意。」和議人說。「假使事態惡化了,你認為,你能處理掉他們?」
「長官,不會麻煩的。我唯一會擔心只有媘蜜、淘氣鬼、華利弗跟十四代。」奧賽羅回答。
「淘氣鬼跟華利弗⋯⋯你的隱陌型能力對付他們,會讓戰鬥變得十分麻煩。淘氣鬼是我最先擔憂的人。太無法預測,不可能被追蹤。」
「長官,我推測我的能力會取消她的能力。我的分身有看到她走近劊子手。我認為她之前,手裡有拿著一個武器。」
「有趣。檸水晶呢?」
「長官,我不確定。還請原諒我這麼說,但很多人都以為自己能處理掉暗地黨,然後他們全都錯了。我不知道我的能力會如何跟他們互動。」
「非常正確。很合理呢。不管我們會不會跟他們戰鬥,都需要招募人。目前就先專注爪牙跟終徒吧。」
「是的長官。」那兩人回應他。
掠翅跟媘蜜,他想著。她們對他來說,才是真正的問題。媘蜜的能力可能跟他的能力很像,但幾乎是反向操作。他聽說自己是被歸類於訊思型跟巧匠之間的類別,也許這種分法也很適切。那就是他使用超能力的方法——從最終結果向後建構,他設計出的東西會十分近似於巧匠。但他真正的能力是訊思型,包含了遠超沒超能力的人的計畫力、覺察力跟點子。
他希望事情不會走到那一步,但他也得有所計劃、作出保險。
他們來到住處——一棟新蓋成的辦公大樓。他擁有最上面的兩層樓,也在屋主同意價格後,買下了下方樓層。他很快就會將其設置好,加上逃跑路線跟能瞄準他的敵人的陷阱。
「奧賽羅。」他說。
「是的長官?」
「把最高階的員工裡成績最好的五個人送來我的房間。我預期在十五分鐘內見見他們。」
「沒問題,長官。」
「你們事情做完,今晚就離開。好好休息。」他說。「重要的事情已近在眼前。」
「是的長官。」兩位使節應和著他。
只有兩位。這可不夠。
他坐在自己的房間裡。這裡有太多傢俱是由工廠生產。他比較喜歡自己做的東西——那樣會更簡潔、簡單。讓他知道所有東西的來歷,也知道它們被如何組裝。他自己製作的住處,有著外面世界所缺少的宜人感。
那五位員工準時過來。他對此很滿意。打開房門,邀他們進來。三位男性,兩位女性,全員都穿著恰當的工作服裝,毫無瑕疵。
他的審核過程很嚴厲,要更上一階,就同時需要他的邀請跟員工的贊同。每一階都需要他們證明自己的價值,要面對更多壓力、更沈重的工作量,也要在他逐步提升的完美準確標準下,能夠自持。
假使這條道路沒有流血——流出他們與其他人的血——這就能登上電視實境秀了吧。
「你們都升遷了。」他說。「明天之後,你們就會成為我的使節,我面對世界時的代表人。」
他們的情感都被充分隱藏,但仍散發出了情感。他們十分欣喜。
「這就是所有事情了。」
那五人無言地,大步走出他的房間。
和議人抽出手機,撥打一通長途的號碼。
他對此稍稍微笑。他沒多少幽默可言,但幽默也有其位置。
鈴聲停止了,但電話另一端沒有聲音。
「和議人。布拉克頓灣。」
他房間末端有個通口打開。在兩個平台氣壓平衡時,他的頭髮便被吹起。
數運人站在通口另一端,就在那條白牆間的白色走廊上。
「五管。跟前一組的程度相同,同樣價碼。」
「成交。」數運人說。「我們情況如何?」
「很有前途,但我不會做出任何保證。」
「當然。那麼,所有事情都會按照計畫走?」
和議人點一次頭。「就如我們能希望地順利進行。我們喪失了蛇蜷,但暗地黨能在他缺席時作為表範。」
「聽起來很好。我會告知博士的。」
通口關閉。和議人坐在床邊,然後躺了下來,盯著天花板。
蛇蜷曾經是測試的重點,卻毫無察覺。那男人曾是和議人的朋友,也是賣給他PRT資料庫的人。他的去世,在許多層面上都很是悲劇。和議人能認可為朋友的人並不多。
現在,關鍵就落在暗地黨身上了。他們以某種方式繼承了蛇蜷的遺產,而他們也跟蛇蜷一樣,野心與大鼎相同。那個組織的希望被寄託到他們身上,驅動著他們的決定。和議人的希望也落到他們身上:他的二十三年計畫,要將世界從最糟糕的災難中拯救出來。最終,他們都得對數十億人負責。
不是說他可以告訴他們這件事,或在對他們的敬意中改變自己的行動。那樣就會錯失重點了。
所有人事物,在大局中,都有他們各自的位置。對一個十六歲女生來說,她在近期未來所做的決定,會比她想的還更有衝擊。
所有事情都會要看她能否接受這個新角色,或這個城市能否接納她。
和議人飄入夢境,他的疲倦心智在那無盡襲擊下,感恩地暫時歇止。
#和議人 #母狗 #檸水晶 #埃力格斯 #戰慄 #奧賽羅 #淘氣鬼 #攝政 #媘蜜 #泰勒 #華利弗4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JGX3UGh4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