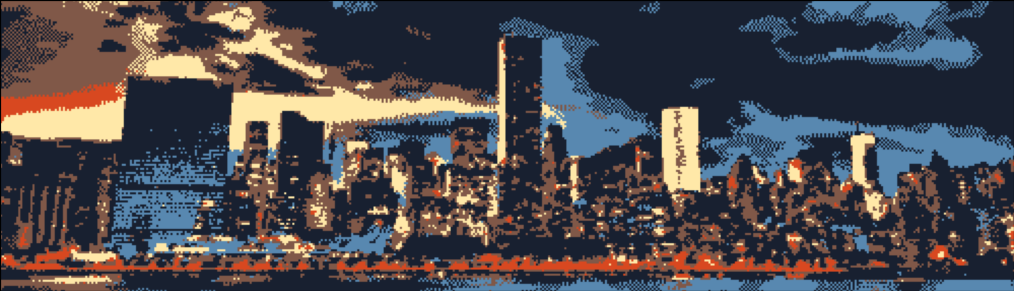 x
x
夜晚的人潮開始流進醜鬼鮑伯,大批大批人來買啤酒,他們將桌子移動並起來,好容納這無法分開的群眾。
在一群人開始拖著桌子成一長條露臺時,就在我們不遠處,布萊恩問道:「想走了嗎?我會在路上講我的部分。」
沒有人對此有意見,所以我們便付帳離開了。布萊恩親切到,願意拿一些我和莉莎的袋子,減輕我們的重量,還加上他自己的東西。市場本身已經差不多沒人了,各式各樣的商人和購物客離開去吃晚餐。只有賣食物的攤販和小販還留著。布萊恩顯然認為這裡已經足夠安全,能開始說了。
「背景是這樣的,我在十三歲時父母分開那件事,我猜那應該很重要。」布萊恩和我們說:「我跟我父親,而我妹愛紗【原文Aisha】則是跟我媽走。愛紗和我還算是有保持聯絡,但我們年齡相差四歲,興趣也完全不一樣,沒什麼好聊的。我有給她發過簡訊說我在學校過無聊得很痛苦,然後幾天之後,她會發給我電郵聊她喜歡的卡通。或是,她在拼音考試中不及格時會向我問些建議。
「我們沒有很親近。自從我生活在城市南端而她在這邊生活,我們就不太可能親近。可是有一天,我從她那收到一封簡訊。就兩個字:『幫我』。我打了電話,她卻在忙線。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把這件事看得如此嚴肅,但我盡自己所能地趕到了我媽的住處。衝出前門,衝刺了兩個街區到鬧市區羅德街,搭了計程車。我衝進我媽住處的前門時就丟下喊著要他的錢的計程車司機,找到了我妹。
「她正在哭,但是她又不說發生了什麼事。我也懶得問第二次。我抱了她一下後,就把她接離開了。之後一個我不認得的男人擋住了我。是我媽的新男友。
「從我看到她的反應的瞬間,我就知道他就是她向我求救的原因。我猜測,也許在這之前就有些事情發生,從她電郵和簡訊語氣的轉變就能看得出來。這也能解釋我的直覺,讓我盡快趕到那裡。我看到她退縮,又往後退,感覺自己把她抱得更緊,接著,我的裡面就變冷了。
他停頓了一秒鐘,就只是沉默地走著。不知怎地,直到他突然轉頭面向我,我幾乎以為他已經說完了:「我想我說過,泰勒,我父親在他還服役時,是個拳擊手?」
「是啊。」我回答。
「說起來我父親是個很堅毅的男人。他不是那種適合獨自養兒子的男人。我不會說他很粗魯,可是他從來沒表現出任何溫情,沒有迷人的趣聞,沒有父親般的智慧,也沒有後院的投接球遊戲。我們建立關係是在體育館,他把拳擊袋抓住、固定住位置,吼著我告訴我說哪裡做錯了,如果我的姿勢、動作時間、打擊力道全都完美無缺,他則維持那嚴肅沉靜。或當我們在拳擊場上,戴著拳擊頭盔和手套,一個三十五歲、處於最佳體能狀態的男人幾乎不對他十五歲的兒子手下留情。他就是期望我跟上腳步、承受打擊,而我對此也沒多少選擇。
「所以,就算我當時只有十五歲,我比同年齡的人還高,而且我知道該怎樣揮拳。那時我沒說任何一個字,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我把我妹推到身後,把我媽的男友揍到瀕死為止,我媽全程一直尖叫哭嚎。我結束了之後就把我妹帶走,回到計程車上。我們那天晚上在我爸家,隔天早上我們就去警局。」
「你赤手空拳打架時,你的雙手沒辦法不受傷。你揮幾拳,穩穩地揍上某人的臉、某人的牙齒,而這會把你的指關節皮膚給削掉。在我爸住處那晚,我正清洗著雙手,那時便看到了。不只有血流出我指關節的裂口,也還有那股黑暗,像非常漆黑的縷縷煙霧。你聽過觸發事件,你也許想著這全都是憤怒或恐懼。可是我就是正好相反的驗證。我連個他媽的東西都沒感覺到。」
「哇。」我說。
「這就是我的故事。」他說。
「呃,我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說法,可是你痛揍了那個人一頓之後,沒被關進監獄?」
布萊恩嘆息道:「那還真有點危險,可是我揍的那個人已經違反了他的假釋條件,沒有去麻藥匿名互助會,而且愛紗也支持了我的說法,好吧,是他徹底應得呢。他比我看起來更像壞人。他被判六個月牢刑,我則是三個月的社區服務。」
「從那之後你就乖乖生活了,不是嗎?」莉莎薇笑。
布萊恩對這評論微笑。「他們已經知道了,可是我想自己還沒和妳說過。」他對我說:「我是為了愛紗才做這些事。我媽在兒童保健介入之後就失去她的撫養權,所以愛紗現在是和我父親住。問題是,他不是個育兒理想人物。現在差不多三年了,而他依然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女兒,所以他們大部分時間都無視彼此。但她很孤獨離群,惹上麻煩,而且她也需要某個不是他或我們母親的人來照看她。我六月時就十八歲了,等我成年,我計畫要終結掉我母親和父親的撫養權,成為愛紗的監護人。為此,我需要錢。」
「因此就是現在這個--較有利可圖的--受雇形式。」莉莎指出。
布萊恩將雙手插進口袋裡:「我父親只要我接手那蠻族妹妹就會給我祝福。我母親講得很清楚說,要每一步都和我爭。這就代表我需要律師費用。這代表我要付錢請私人調查員取得我母親還沒有改掉毒品,和交些幹她媽爛男友的惡習。我需要一個能通過審查的公寓,留出一個空間為愛紗預備。在這些之上,我還要將自己呈現為一個經濟安全、足夠負責任來補足愛紗的母親作為另一個選項的事實。」
「老闆會幫忙最後那部分。」莉莎說:「零用錢還有布萊恩從其他收入分到的部分,會從一個合法的公司交到他手上,而且那個經理說公司願意,也能夠以他的名義提供一份閃亮亮的推薦函。」
「這我就沒那麼高興了。」布萊恩承認:「這……太方便了,我不知道自己怎麼做才能成功,可是我不喜歡依靠完全不認識的人。他能隨時拿著四萬元離開,我能接受。可是如果他這樣搞我……」
「你自己之前有說。」莉莎再次對他確認道:「他沒理由那麼做。」
「沒錯。但這不會讓我感覺更好。」
「我認為你所作的很高尚。」我說。
「不。」布萊恩聽起來幾乎被這個想法冒犯了:「我只是做我得做的。她是我家人,妳明白嗎?」
「是呀。」我說:「我瞭解。」我能理解將家庭擺作優先的想法。
我們一兩分鐘陷入了沉默,一部分是因為一些推著過大的嬰兒車的媽媽們轉過彎,來到我們面前,正好在能聽見我們的距離內。另一個原因是,沒有什麼好說的能加入對話。
在兩個媽媽將她們的嬰兒車停了下來,看著商店櫥窗時,我放鬆了心,因為我們能超過她們。一群群人擠滿了整個人行道,所以你得走到馬路上才能繞過他們,這真的很令我厭惡。健忘的人們擋住了整條人行道,還會慢慢走到你被迫拖延腳步,也快得你無法走過他們?他們讓我產生召喚數群蜜蜂爬上他們腦袋的幻想。當然,不是說我真的會這麼做。
我們再次能自由說話時,我發現自己掙扎著要想出一個新話題。我看了眼布萊恩,試著估量他在說完自己的故事之後感覺怎麼樣。他真的還好嗎,或者他只是十分善長壓抑自己的情感?他看起來完全普通,就像某個和他一樣拎著數個購物袋的人似地放鬆。
「嘿,你買了什麼?」我問他。
「一些要放到我的公寓的東西。幾個地墊,一個我得要放到框裡的藝術品。這些有點無聊。我找到了一個還不錯的塑像,賣的人說那是他為了某個從來沒拍成的電影所作的概念雕刻,我在考慮用那個塑像當作新面具的靈感。別繼續用骷髏了。」
「你得要讓我看看喔。」我說。
「事實上呢,」他頓了下:「我最想讓妳看看呢。妳的假面服看起來滿酷的,而我也想著妳有沒有意見告訴我說該去哪裡找?」
「哪裡?」
「假面服。」
我什麼都沒想地盯著他幾秒鐘,試著將他所說的話拼湊成形。
「有些時候,有我的能力真的很讓人挫折。」莉莎抱怨道:「這就像在眼盲者的領地上成為唯一一個長眼的人。泰勒,布萊恩在問妳,妳在哪買妳的假面服。布萊恩,她沒買假面服。她是從頭開始做的。」
「沒唬爛?」他雙眉高聳。
「那是蜘蛛絲。」我說:「所以它的伸張強度只比鋼鐵弱一點點,但重量卻超輕。蛛絲沒和克維拉一樣強,可是能伸縮,也就是說它能作為普通衣服,也比普通鋼鐵、克維拉或塑膠假面服的撕裂口更小。製作起來有一點複雜,因為我需要管理蜘蛛,還得親自織它,但我基本上都在我專心時讓蜘蛛工作。」
布萊恩點頭:「這真的很酷欸。妳能幫我做一件嗎?」
這讓我頓了下。
「我不會期待妳免費幫我做的。」他補充道。
「我們在說多少錢?」我問。
「說個價碼吧。」
我想了下:「兩千?」
他笑了下:「沒有給身為隊友和朋友的我折扣下嗎?」
「這已經有折扣了。」我說:「這很花時間,得要在它們工作時待在它們週圍,也就是說我沒辦法花所有時間來作,因為我爸在家的話就會看見我把它們留在那裡。加上我得讓蜘蛛輪班,好讓我不斷有新鮮的蛛絲供給,可是我也不能讓鄰居家附近有太多隻,以免有人注意到……這作起來並不簡單。」
「如果這麼麻煩的話,就換個地點啊。」莉莎提議道。
「換到哪?這得要是一個我會待很長時間的地方,有空間工作,還能累積幾萬隻蜘蛛又不會有人注意的地方。」
「我們的閣樓?」莉莎聳肩:「或更準確來說,在閣樓底下的區域?」
這個點子讓我說不出話來。這實在太合理,莉莎提議換地點時我沒立刻想到這點子,讓我想踹自己一腳。
「哇,哇,哇。」艾利克插進話來:「幾萬隻蜘蛛?」
「如果我想要工作起來更快一點的話。」我說:「沒錯,我們說的大概就是那麼多。因為我想,布萊恩會特別想要更重一點的布料。閣樓底下那層樓絕對能行。我是說,假使任何人探頭進來,多一些蜘蛛網也不會引起任何注意,對吧?」
艾利克用手梳了下頭髮,我將這視為壓力和擔憂的徵兆。這很罕見呢,看到他除了無聊和半分心以外的情緒。就像證實我的想法似地,他說:「我不想要幾萬隻蜘蛛潛伏在我住處下方,發出一些蜘蛛的噪音,然後還在我睡覺時爬上樓爬到我身上。」
我試著讓他放心:「黑寡婦通常不會流浪,而且它們更傾向於互相殘殺而不是去咬你。我是指,你不會想要刺激一隻……」
「黑寡婦蜘蛛?」艾利克呻吟了一聲:「這時候妳應該要說妳在捉弄我吧。沒關係,我能接受惡作劇。」
「它們有你能在這附近找到的最強牽引蜘蛛絲。」我說:「能得到更強的種類的話我會很高興,像達爾文樹皮蛛。它們有全世界蛛形綱和蠕蟲之中最強的絲線。它比克維拉還要強五倍。如果我認為他們能在這種濕潤氣候生存的話,就會跟我們的老闆要一些了。」
「妳在說黑寡婦的時候不是在開玩笑。」
「你還記得我帶到銀行搶劫時的那些?我就是從家裡帶它們出來。」
「我肏。」艾利克說,然後又重複地說:「肏。現在布萊恩又堅持要那個假面裝,所以這大概真的會發生了。
」 「你有蜘蛛恐懼症?」我問道,只是對他反應這麼強烈,有一點驚訝。
「沒有,可是我認為任何人都會被幾萬隻黑寡婦蜘蛛在他們住的同一棟建築下方的點子嚇到。」
我想了一陣子:「我能弄籠子,如果這會讓你安心一些的話。不管怎樣,裝籠子都很合裡,因為它們有地盤意識,而且我不在週圍時,它們大概會自相殘殺。」
「我們之後會想好的。」莉莎微笑:「妳能操作細微到,也為我做一件嗎?」
認真考慮為幾個反派作出高品質假面服的想法,重擊了我一下。我不確定自己對這件事感覺如何。
「當然,我對我的蟲子確實能細微操作到同時作兩件……可是這真的很麻煩。我做完自己的假面服時感覺總算能放鬆了,我不期待未來再多做兩件的想法。」這些都已經足夠真實了。「讓我想想?」
「一千五百。」布萊恩說:「我最多就出這麼高,現在我們已經想出了該怎麼解決物流問題。我認為這樣出價很公平。」
「好吧。」我說。錢,真的不是影響我的因素。我是說,高額價碼能讓我雙眼瞪大,可是到最後,我沒計畫要花費那以不正當手段賺得的錢。
總而言之,我們也許花了一個小時回到閣樓。我不怎麼在意。我的訓練讓自己不會那麼容易疲倦,而且他們的陪伴也很宜人。
當我們進到建築物裡,其他人上樓時,我留了下來看著一樓的工廠區域。我也許能強化些運輸帶之間的膠板結構,這麼做就代表我能有幾個長條平台讓我的蟲子能工作。加上幾個在背後的籠子,作為它們的住處……可是我能從哪找到網格籠子或容器,來給幾千隻蜘蛛當房子?
這是我能想清楚的事。不管我是用蛋裝紙盒或利用蟲子的幫助來把整個東西蓋起來,不知為何,我已經知道這是可行的。
問題是,我想要這麼做嗎?
我走上樓,深深陷入思考中。
「瑞秋在哪?」布萊恩在他從閣樓另一端轉身過來時問,布魯圖斯和安潔力卡匆匆來回走著,搖著尾巴:「只有她兩隻狗在這裡。」
「我們比她說要到的時間還晚二十分鐘。」莉莎指出:「也許她先走了?」
「你們先準備好。」布萊恩指示我們:「我們之前和我們的雇傭人說,我們今晚某個時間會交出錢,而如果我們弄得花太久,會讓我們看起來很糟糕。我來打電話給瑞秋,看看發生什麼事,我穿好裝備不會花太長時間。」
艾莉克、莉莎和我前往我們各自的房間裡。關裡門來,我從床邊桌最下面的抽屜拿出我的假面裝。我把它鋪在我的充氣床墊上,然後把要放進我的多功能空間的武器儲備堆起來,排列成行:胡椒噴霧器、刀子、伸縮戰鬥甩棒、筆記本、艾比腎上腺素注射筆,一袋裝著零錢和二十元紙鈔在內的零錢包,以及一隻即可拋手機。每個我能想到的,想要帶在身上的東西。
還要筆,我現在才發現。這是件小事,可是筆記本沒有筆,對我而言幾乎沒有用處。我走向衣櫥,腳步卻很快停了下來。
衣櫥上,有一個水晶。不過水晶並不是正確的詞彙。那是一個淚滴形狀的琥珀,光滑打磨過了,幾乎有一呎高,直直地站在一個石座之上。在那裡面有一隻蜻蜓。蜻蜓大得讓琥珀幾乎裝不下--甚至,如果雙翅沒有在琥珀底部向內彎曲的話,就不會合襯。閣樓窗戶的光線碰觸到琥珀,將衣櫥頂端和牆壁一部分映照出黃橘色深影,在穿透蜻蜓透明翅膀之後還沾了點深色的藍。
旁邊有個紙條:「看到這個,很有妳的風格。把這當作遲來的歡迎禮物吧。 布萊恩」
我完玩全全震驚。他一定是當我還在樓下時留下的。我趕緊穿上假面裝,在衣櫥裡找到一隻筆,把多功能空間的內容物放好。都弄好後,我又穿了件牛仔褲、汗衫和一件夾克蓋住假面服頂端,再用一個差不多空了的後背包蓋住在我背上稍微凸起的護甲。
在剛完全準備好之後我才走出房間,看到布萊恩坐在沙發上。當我確定他不管如何都會很高興,可是我推測他會欣賞我準備好之後才來謝謝他,而不是反過來。
他仍待在客廳裡,在一件保護性背心上再套了他的摩托車皮夾克。「我……呃,不知該說什麼。」
他額頭皺了起來:「妳覺得OK嗎?我是在想,給妳一個有一隻死蟲在裡面的石頭也許不是最好的……」
「那個很完美。」我打斷了他:「真的。謝謝你。」我從來不知道得到裡物時該說什麼。我總是擔心我的感謝聽起來很虛假、強迫或諷刺,甚至在我是真心說出來時也是。
我衝動地,給了他一個非常短暫的擁抱。我認為這是自己唯一一個能讓清楚表達感謝的方法。
「嘿!」一道在我背後的聲音把我腦子中的機智全嚇出來了:「不准在工作場合搞浪漫!」
我轉向看著艾莉克和莉莎站在走廊上,微笑著。莉莎她,比平時微笑得更燦爛。
我臉一定像甜菜一樣紅:「這才不是,不是,我剛剛只是在謝他給……」
「我知道啦,呆瓜。他買的時候我就在他旁邊。」
莉莎仁慈地轉換了話題:「我們當地的反社會成員有任何消息嗎?」
布萊恩皺了眉:「沒有。她的手機在訊號外,但這不應該發生,因為我是那個把它轉開機的人,今天早先才開機交給她。事情有些古怪。」
前一瞬間自然的好心情現在全沒了。我們交換了個眼神,然後沒有人現在還微笑著。
「我認為……」布萊恩小心翼翼地估量他話語的重量:「確認錢的情況會是個非常好的點子,而且越快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