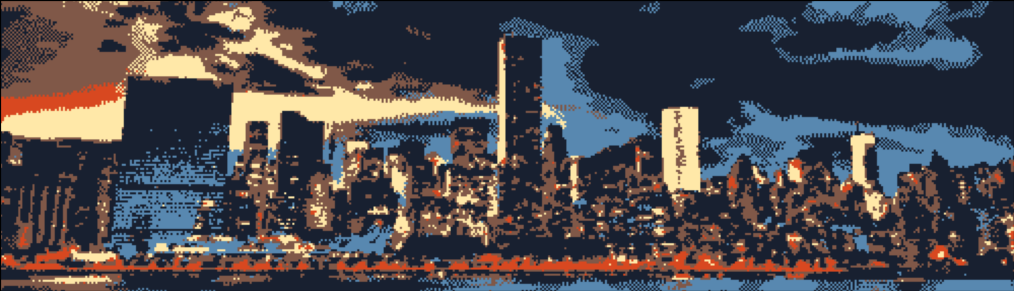 x
x
偶人撲向我,他刀刃腳趾咬進地面以求摩擦力。他移動迅速到足以使雙臂甩到身後,如強風中雙股緞帶。
他站在我幾步之外,轉動身體用右手臂和其上連接的三呎長刀刃揮向我。假使我沒比較理解戰鬥,會以為他根本不擅長戰鬥。他手臂延長於鐵鍊,揮動時正足使刀刃飛上與我腦袋撞擊的路線。
我用甩棒格擋。衝擊十分沈重,比我想的更像擋下大錘。甩棒幾乎脫離我的掌握。
甩棒彈開刀刃時,他就像陀螺扭轉上半身。連起的手臂在他周圍猛衝,使他朝我一躍。我猛後躍退開,僅逃出揮擊兩寸之外。
他轉動上半身,右手臂纏繞而出,使鐵鍊捲上身體。他開始將手臂捲回,手臂和刀刃在他周圍畫出慵懶圓圈。我退開,想到自己總算有機會穩住體態。
他脫離的手臂被捲回時,手指往後方翹、繞過其中一隻腳,緊抓自己。他收回另一隻腳趾刀刃,將那隻腳平放到地上。這動作看似使他失去平衡,他蹣跚,幾乎倒地。他接著猛然一動,校正自身,刺出另一條腿及連接在腿上的三呎長刀刃。
我沒時間躲開、舉起甩棒護衛自己或甚至做更多事,我遲緩察覺到他在假裝幾乎要倒下。他以之前那同樣使人驚訝的力道打上我肚子,接著向上斬我的鎖骨,力道足使我雙腳被抬離地面。我重重摔在背上,裝甲吸收最烈的衝擊。我裝甲側板向身體彎曲之處,戳進了我背部肋骨。
我記住了與戰慄對練時所學到的功課,想在偶人糾正身姿時逃開,他也將前臂與連接起腳的手掌放到正確位置上。在我能站起來前,他就開始大步朝我走來。
我引蟲子到身邊,在滾到一側時隱藏自己的動作,將雙腳踩穩,朝他左側衝刺。
我仍在蟲子的掩護之下,身後被擊中,臉向下地摔倒。驚訝與痛楚同樣糟糕。
我透過蟲群,感知到他走近,直到他雙腳各在我兩側。我感到他手指絞起我的頭髮,將我的頭向後、向上拉扯。我掙扎著,想用甩棒抓住他膝蓋,但他把我猛擰到一側,我感到一把刀抵上喉嚨。
就像他對那白髮醫師所做的,將刀子長長一劃、平順地重重抵住我喉嚨,調整了我脖子的曲角。
一次心跳後,我想到一個計畫,也開始執行了。我咕噥一聲,發出一道哽咽,因他正將長片金屬壓住我的氣管而變個更加逼真;我確實想要咕噥,而我也確實要窒息了。接著我癱軟,這區域每隻蟲子都停止動作,有如雪花,蒼蠅開始從空中飄落。
他放開我的頭髮,我的面具重重嗶剝地撞上地面。我聽見有個女孩尖叫,聽見其他每人發出的噪音和吼叫。
我吞了口氣,部分要確認自己喉嚨沒真被割開。假面服救了我一命。我希望聚集在這的旁觀者沒見證這場面。如果蟲子在他們的恐懼、恐慌聲響引起他注意時,有擋住他們的身影,就好了。
我只是需要一秒來思考。偶人能毫無限制繼續進攻,直到他成功割開我喉嚨或打出致命創傷。這就像和布萊恩的對練,只是各個方面都更加糟糕。偶人更強壯、更迅速,他攻擊距離更長,不會疲倦,他很厲害,又想殺了我。他有普通人類不可能企及的靈活性。他沒辦法被關節技抓住——他四肢會直接脫落或扳向不可能的角度。
他不知為何能感知我。怎麼辦到的?我假定他靠視力行動,這是很魯莽,在他面具上沒有眼洞時特別魯莽。他沒注意到我在裝死,表示他沒依賴視覺,或是他的視覺有夠多限制,無法在我們周圍的蟲雲裡看出地上缺乏血流。如果他沒聽見我呼吸,我就懷疑那並非超能聽力。
他是用雷達嗎,就像蟋蟀女那樣?這會是我第一個猜想,然而我的蟲子並沒有聽見任何這類東西。
不對。這條思路無法成就任何事。
我聽見他將刀刃彼此磨礪,發出鋼鐵碰上鋼鐵的聲響。我能以飄落到他身上的蟲子,感知到那動作。人群中一個男人低聲抽泣,偶人轉身面對他。
刀刃刮上刀刃的間隔之中,金屬高吟。偶人靜止、站立,觀察局面。
我得想出攻擊計畫,不然其他人就會付出代價。我認為,自己的截止期限是到,某個人喪失了鎮定、想逃跑的時間點。
假使我要攻擊,就需要找到弱點。但他很聰明。災難將他變成這東西前,他就處於解決許多世界危機的邊界之上了。包括人口過多、可再生能源、高效率回收、世界飢餓。就算有巧匠能力提供方法,仍需要某位特別的人來經營,來真正做出改變。
眾所皆知,他不會有任何醒目弱點。任何他自己沒想到的措施,因著作為屠宰場久駐成員的福利,現在都早已有所準備了吧。他曾與比我更強的英雄與反派戰鬥,他在這過程中會學習、進步。
他在這方面,也許和我也沒多少不同。我也以同樣的方法成長。不同的是他有數年經驗。這一點,還要加上他瘋狂到無可比擬。
我若是他的話,會怎樣使用他的超能力?
我不會不覆蓋住重要孔洞。這很合理。我的專注點——偶人的專注點——會是要把自己徹底設計成封閉系統。這不僅相當明智,也是他的變態的重點全部所在。他完美回收所有排泄物,將多餘的能量轉移成機械動力來排放,藉由吸收熱能來攝取能量。
那可能會是他感知周遭世界的線索嗎?熱量?或者可能是某些完全不同的東西?輻射?無線電波?電磁場?
將我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就得思考到他的動機。為什麼選這個形式?我讓自己變成一具玩偶或是店裡的偶人是因為⋯⋯這是道永久的提醒。他妻子與孩子在希魔翮攻擊時去世?這裡面有個故事呢。
但還有什麼?為什麼要表現得像個人類?
為了誤導人?也許「我的」器官和部位絲毫沒有人類的結構了。我也許走向神盾路線,為每個能省略的部位都裝設內建的備品。我不需要心臟、腎臟或傳統的消化系統,或骨髓或任何這類器官。每個我能拆掉的東西,就會成了更多擺裝備的空間,也有更多空間來一起協助「我」,來把身體各個部位變成永久自存系統的裝置。
他的軀幹是身體裡的最大部位。那裡不會裝他的心臟、肺臟或任何這些東西,因為他不需要血液循環系統。那裡更可能,裝著他的腦袋、他的感知器官/系統,還有他用來遙控雙手、雙腿、手掌和腳掌的東西。除非他沒想將所有東西都放進一個籃子裡呢。這些東西的某些部分,也很可能被放進他雙腿或雙手裡面了。
如果我是他⋯⋯我會花好幾小時仔細平衡我身體每一部份的「生態系統」。某些如此精確、細緻調校的事物會十分敏感、脆弱。它們得抗衝擊,如果生態系沒有抗衝擊的話,我就不會四處找人打架了。熱量與寒冷呢?他的外殼一有裂縫?那就能造成大浩劫了。
好吧。我也許,是有點理解他了。這麼說來,如果我一開始就沒辦法傷害他,這就都沒有意義啊。也許我思考的東西全錯了。
蟲子也很常將自己包裹在硬殼內來面對威脅,不是嗎?比如它們在要面對其他種昆蟲的時候。如果我願意找的話,這裏有一百種解決方法。
這就是我所需的靈光一閃了。幾秒鐘內,我就有了個計畫。
這不算是好計畫,但也算是點東西。作為以防萬一的應急措施,我能試試其他幾個較小規模的計畫,也用上它們也許能分散注意力或甚至可行的機率。如果沒其他效果的話,我還有這些選項,這使我感覺比較好了。偶人在十五秒內,殘暴而又無懈可擊地痛揍我一頓,而就蟲子從我基地那裡運送來物資所花費的時間來看,在我甚至可以開始計畫前,至少還有兩分鐘。
我想好的這一瞬間裡,也開始推動事情。每隻靠近我基地的飛行昆蟲都到室內,聚集起我所需的東西。
我在心底記下,要為基地開個更容易進出的通道,好讓我未來能加速完成這種事。
我在心裡記下另一道筆記,要設置有指針的時鐘,好讓我待在地盤裡時,能讓蟲子搭在指針上,當作精準追蹤時間的方法。我猜因為碎歌鳥毀了所有東西,就得是個老派時鐘。
我得要猜測。直到能開始計劃前我大概還有兩分鐘。
我面朝下、趴在工廠地板時,試圖控制呼吸,好讓他不會注意到我依然活著。胸膛心跳如此劇烈,我害怕自己會因心跳而洩漏心機。
保持不動,是我必須做的事中最困難的事情之一,而我以前可是也經歷過艱辛事件。知道他可能會跳向某人,然後在任何瞬間中了結他們的性命,這令我十分緊張。我在此能拖延的每秒鐘都很重要,因為我沒必要與他戰鬥的每秒都是關鍵。
「媽咪。」這個詞彙被喊長。一定由某個年幼的人喊出來。是個孩子?「我不想待在這了!」
鋼鐵割刮鋼鐵的急促韻律停下來。偶人靜止不動。
該死的。我的緩刑就只有這麼長了。
我將自己拉起身,攪起這區域的蟲子。它們像股黑暗旋風般從地上升起。我收起刀子,雙手抓住甩棒。
「偶人!」
他停下來,上半身轉過來面對我。他頭歪向一側。
「是啊。」我說。「你沒幹掉我。」
他轉回去,開始走向那個母親和那個小男孩。那兩人畏縮在一個空鋼架和工作桌之間。
「喂!」我吼道。「來啊!和我打啊!你是沒軟蛋來對付一個青少年女孩子?還是你把自己的軟蛋也割掉了!?」
他沒慢下腳步或因我的話語而遲疑。
「混漲!」我衝向他。他百分之百在誘導我,強迫我進入自己必須幹出蠢事,或允許那個媽媽和孩子受傷的情形發生。如果我是個更強硬的人的話,就能允許他傷害他們了,我知道長遠來看,那是比較聰明的作法。但我無能做到這點。
還有什麼是我能做的呢?我得在衝過工廠地面層的三、四秒鐘裡做出決定。他有我一倍高,我的武器也對他起不了任何效用。
我猛身撞上他雙腿後側,撞上他膝蓋和小腿後側。他那搖晃不穩的平衡感不全是在演戲。他蹣跚、身後倒在地板上,雙腿落到我上方。
「去啊!」我對那母親尖叫。「跑!」
她跑了。偶人延展開刀刃、刺入她大腿後側,她倒了下來,但有其他人趕緊跑來幫助她。
偶人的左腿纏繞過我喉嚨,形成了個即興鎖喉。我想溜出去,強迫拉開他的腿。就算我能移動他的身體,也沒辦法將頭擠過空隙。
沒算入我躺在地上時的話,要爭取時間,我還能撐多久?不到三十秒?
四柄刀刃從他右腿小腿肚彈出。他將刀刃高舉到我頭上,刀刃開始旋轉,最初緩慢,接著加速,如同刀刃風扇。或像個廚餘處理器。
他將我頭鎖住,但我身體其他部分都能自由移動。我雙手抓住甩棒,用上槓桿作用所提供的力量,揮向迴旋刀刃。
我的甩棒飛出手中,但刀刃也停了下來。我在看見刀刃再度開始緩緩旋轉時,我心一沉。
它們還沒回到與先前相同的轉速。幾秒過後,刀刃被收回進他腿中。
我可能會鬆了口氣,但我依然在他掌握之中。
他將我向上抬起,靠兩隻手和一條腿在地上穩住自己,另一隻腿將我高舉。我腳趾亂踹、想接觸地面,卻碰不到。脖子上的緊縛也並不完美:他沒切斷我的血液循環,也幾乎沒影響我呼吸,但這還是很痛,而脖子也被全身體重拉緊。
我抽出刀子,抓在手中。接著我將刀子塞到喉嚨上。或說是抵住偶人那繞過我喉嚨的腿。概念上相同。我瞄準球關節,擊中我臉周圍兩寸旁。擊打一次、兩次、三次。
我在他調整姿勢時打了第四次。我不確定他是否希望要緩緩勒死我,讓我吊著,直到我開始求情,或他要換姿勢做其他事,但他顯然改變主意。他翻過身子,將腳從我喉嚨邊展開的同一瞬間,用巨大手掌罩住我的臉。
他將我緊緊繞過身體而甩出,也讓他手臂從肩臼脫落,鐵鍊迅速捲出的呼呼響,在我飛過房間時變得遙遠。
我撞入佈滿釘子與螺絲的木板堆。金屬尖端刺痛我,卻沒有刺穿假面服。我試著站起,腳只滑過木板。他的手依然附在我臉上。
他開始將我拉向前,無疑是要重複這過程。我被他手掌抓住而半盲,我在一次心跳中反應過來,把刀尖砸入他手掌和我臉之間的空隙。
媘蜜說過這把刀強韌到足以當成鐵橇。我很高興發現她是正確的。在鐵鍊收回的拉力和刀子的槓桿間,我從他的掌握逃脫出來,他指間重重刮過我頭皮。他的手臂飛回他身邊,接回到位。我想將自己視野中的模糊處眨眼消去,卻只發現自己用刀刃緣刮花了面具的右鏡片。
被四處扔擲的痛楚,遲緩地讓自己彰顯。瘀青,我可以接受。只要身體在我需要時能移動到我需要去的地方就沒差。我感到逐漸增強的晦暗頭痛。是我被鎖頭時,被抓住的地方嗎?
好吧。或多或少,還算全身而退。我爭取到多少時間?一分鐘?一分半?我能撐夠久嗎?路人們呢?蟲子抵達的時刻才是計畫開始之時。我在那之後仍得存活,而也沒保證計畫可行。實際上,我的直覺告訴這計畫不太可行。
三十秒到一分鐘。我大口喘氣,他沈默瞪著我的每一秒鐘,我都應該重視。
那面無表情的面具背後,是什麼呢?他也要想出戰鬥計畫?也許吧,也許不是這樣。他也可能正在計算最好摧毀我的方法:不直接殺掉我,而是摧毀我。他有很多方法能做到這點。施加終身傷疤和傷口。他也能走相反路線,謀殺那些平民,留我作為最後一位站立的人。兩個都是非常真實的可能性,兩種都各自十分極具破壞性。
也或者,在那硬殼背後,他正處在精神苦痛的劇痛之中。也許他正耗費每天每秒重新活過他在幾近無可阻擋、邪惡力量之下,喪失家人與夢想的那一天。
我對他的過去無能為力。不管他曾是什麼樣的人,他現在是個怪物。我必須全力阻止他,再傷害其他任何人了。
是時候啟動戰鬥計畫一號,那是我想到、幾乎不會成功的兩個點子其中一個。我讓蟲群撲上他。在這時間點之前,我保留大部分蟲子,只用追蹤周遭情況的必要最少數。現在我就悶住他,將它們堆上他身體所有表面。
當然,這沒成就半點東西。他開始跑向我,準備好武器。他動作中毫無窒礙,而他的感知——視覺或其他東西——也沒被減弱。
我在他靠近第一次揮斬底下躲過,但我無法避開後續追擊。他第二斬刮過我肩膀的裝甲、擊中我胸膛。我在短瞬的痛楚之外,幾乎對此感到感激,因為這一擊把我打飛出他範圍外。
我某些蟲子成功擠進他的武器所彈出的縫隙。那個空間並沒有完全吻合刀刃柄部,而蟲子體型很小。刀鞘中也沒有任何有機物。就算是內部也被徹底密封。然而,我仍成功讓蟲子進入機械,將它們身體打入精細運作的機制,或殺掉彼此來噴出膿水與身體內臟到任何感覺很精巧的東西上。
偶人後退,我看著他收回所有刀刃,刺出的縫隙也閉合起來。一波高壓與熱度殺死每隻蟲子,也可能燒去大部分我想辦法抹進去的噁心東西。
是啊,我沒想過這會成功。一號計畫不成。
至於二號計畫,我需要甩棒。我只能希望甩棒還很完整。我用超能力和雙眼搜索過工廠地板,同時也保持腦袋不動,好讓他無法看見我正在做的事。
我的蟲子幾乎到這裡了,群群抵達。
我發現甩棒落在靠近我被偶人定住的牆壁附近。我得繞過他才拿得到。
拿來。我命令蟲子,偶人再次撲向我。我沒一秒時間思考要它們如何拿過來。現在,我需要存活。
這次,他攻勢癲狂。如果我不夠了解的話,會認為他被惹怒。我向後跳出第一擊的範圍,在他上半身旋轉中追打出一連串迅速揮擊時,我也快速後撤,他頓時變成了炫風刀刃攪拌器。
我太忙於不被刀刃擊中,錯過他傾身的時機。他重心放到一條腿上,另一條腿大開踢出,放出鐵鍊延長腿七、八呎向我飛來。我第二次被打飛到木堆上,落在木板邊緣,也是第二次倒在地上。
他停止轉動,收回腿,顯然對像陀螺旋轉後也毫無暈眩。我看見蟲子努力抬來甩棒,但偶人也在同一時間看見蟲子。他停下來,一條腿踩了上去。他一踢,將甩棒滑過地板,踢遠離我。
肏。我得採用比較沒那麼有效率的路線了。我在自己站起來時,抓起一塊頂面二比四吋的結實木條。這根木條很老舊、滿是塵埃,數年暴曬陽光下而有些受損,聚集在一端的螺絲釘也都生鏽了。
就武器來說,這比什麼都沒要還要好。
他的刀刃互砥磨利時發出刺耳聲響,磨過一柄刀刃的刃緣,再磨下個刀刃。這樣磨刀久到正好使我落入虛假安全感之後,他一猛跳,數柄刀刃刺向我胸膛與喉嚨。我那片木板同時擊出。這看起來讓他措手不及。我太快揮出而沒打中他,但他也不是我的目標。
我朝最高處的刀刃揮打,讓其往下砍向地板。我試圖避開刀刃,也擊向刀刃平面,但我沒打中。我沒看到自己是否達到任何預想的效果,因為他倒在我身上,兩柄刀都擊中我胸口的裝甲。痛楚爆裂於我鎖骨和肋骨,但我沒體驗到任何刺透傷的明顯劇痛。我的裝甲救了我一命。
他發現刀尖卡在我裝甲較密集的材質裡,就將雙手揮甩到一側,將我扔出足足十、十二呎外。我落地時四肢大開。
我噴出一口氣,每個動作中都感到胸膛的痛楚。接著我微笑了一下。
我的蟲群總算抵達了。
蟲子作為一整個群體流進房間裡,它們約略有半數都掃過偶人。他晃了一下,接著將注意力轉向我,絲毫不關心。
這是件好事。他不要太注意才比較好。
他身後,蟲子以一種幾乎像萬花筒般的模式移動,緩慢地從中心點向外擴張,排列均勻對稱。
他頓了下,轉頭看向蟲群。
他顯然能感知到我放在地板上、在空中漂浮的蟲子。這點很明顯。同時,他無法分辨我沒有在地上流出一灘血,或是我之前趴在工廠地板上時仍在呼吸。我的計畫取決於兩件事:不管他感知事物的獨特方法會不會讓他捕捉到我在此所做的事,以及他是否能對此有所行動。
隊形停止擴張,再次掃過他。偶人又一次,晃了一下,踉蹌了一步。
他衝過現在坐落於我們之間的蟲團。我成功用木條格擋了他刀刃一斬,接著跳閃過第二道斬擊。我想用二比四吋木條擋住他的踢擊,然而,木條飛出我的手掌而落地。他重重,踢了我第二次,我向後縮,手放到肚子上,嘔心感在喉嚨裡累積起來。我控制住呼吸,壓下我的晚餐。
蟲群第三次通過。它們集中在他腿上,差點就令他失去平衡。
我能看到他頓住,看到他的頭滑稽傾斜。我咬住嘴唇。
他的右側,我左方,蟲群再次緊緊聚集,又緩緩擴張,動向有所調節。
蟲群由飛行蟲和蛛形綱相相成對。我基地每隻蜘蛛都攫著一隻蜜蜂、黃蜂或更大隻的蜻蜓——它們各自抓住蜘蛛。一百對昆蟲。
這些蟲子彼此相連,迅速拉出五百多條絲線。大部分都是拖曳絲,這張「網」有夠多黏蛛絲來黏上他,覆蓋上他的人造身體然後留在那。
我沒有帶夠多隻黑寡婦到工廠裡,是怕他會察覺我在做的事,並且在我真的能滾動雪球前就抵銷這個策略。現在我把它們聚起來,也加進來。我用上所有已經放到他身上的蜘蛛,集中於他的關節,強化已經留在那、較結實的蜘蛛網。他們的蛛絲和黑寡婦相比,什麼都不算,但那也有點作用。
他毫無窒礙地移動,一點也不注意或關心。一條條蛛絲拉長,在他伸展手臂時便斷裂,而在他走路時則有更多蛛絲脫落。其本身,蛛絲微不足道。綑起來才會強勁。就像我的假面服。
他想收回右手臂的鐵鍊,卻纏上了蜘蛛絲。他將關節壓上地板,將其扳至校準。他下一次嘗試時右手就捲了回來。我的二比四吋木條之前就沒做出多少事呢。我第二個以防萬一的措施也沒成功。
同條斷開的手臂在他試圖抓住我時,朝我伸來,我轉向即時轉向一側,避免被抓到。他以幾近爆炸的力道打出另一條手臂,而我也成功在他勾住我假面服前捕上他的手臂。
我的蟲群穿過第四次,集中於他延伸出的手臂的鐵鍊,還有他身上蜘蛛絲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的雙肩、手肘、胯部、膝蓋關節。五、六十隻蜘蛛停在伸出的鐵鍊上,噴出大量最黏稠的絲。
他正在試圖移動我抓到我身上的手臂,他的手指想抓住我的手掌和手腕時,彎曲向不自然的角度。他轉換戰略,讓手臂中的刀刃隨機刺出,盡所能讓手臂不可能被抓住。這樣做後仍是失敗,他甩起鐵鍊。我即時放開那隻手,避免被鞭擊末端捕中。他捲回手,在四分之三長度收進去前,他就遇到了一個小問題。
最後四分之一的抽回過程慢了一瞬間。我希望,是絲線黏住了機組。我看到他望向自己手臂,接著活動手指,就像要測試身體。
他分心之時,我讓蟲子隊伍第五次經過。我想要更隱密,小心地把絲線繞到他身上,不要又以足使他失去平衡的集體力量來讓蛛絲緊緊纏上他。
他攻擊了,伸出我沒黏住的手臂。方才擊中我肚子的痛楚讓我慢了下來,他的拳頭砸上我,似乎如第一百次地把我敲倒在地。我在他能做任何事前,擋開那隻手,趕緊站起身。
正當那隻手臂半伸長時,我想辦法將幾隻蜘蛛放上鐵鍊。它們立刻開始在允許鐵鍊收回的機關上緊繃身體、製造出蛛絲糊。一隻蜘蛛不算多少,但全部一起,就會累加。
我可以精確指名他察覺我在做的事的瞬間。他伸出鐵鍊,將手臂揮過房間,刀刃切出長長一道斬痕。我躲避開來,但兩個路人被擊倒,尖叫。等他要收回鐵鍊,機關卻動彈不得。
他的身體很像兵器大師的動力機裝,但加入的每塊器材都迫使他切掉一磅血肉。我傾向如此猜想:他如此瘋狂,現實逼使他走向更雅緻、更有效率的設計過於粗糙技工。他腳踝裡的刀刃推進器建得十分輕量,也使用最少量能源,同時完成最大效果。
他偏了頭,看著頑固拒絕收回原處的手臂。
我讓蟲子掃過第六次。蟲群通過時,他頭一甩,看向我。反正,是他沒眼睛仍能有的神情。他理解正在發生的事了。
比我更厲害的假面在這時,可能會說諷刺妙語、一句污辱。我身上太多處發疼,我肋骨、肚子、雙肩、脖子、背和雙腿的一些痛楚十分劇烈,如紅燙燙的撥火鉗連續、毫無停歇地按壓這些身體部位。我無法多騰出氣息。
鐵鍊從他的手肘臼掉落,我看著他踏步走過自己落地的手臂,撿起手,扯出多餘的鐵鍊,然後把手臂喀嚓一聲壓上原處。
「來啊。」我喃喃低語。
刀刃刺出他全身的夾縫,有些我根本都沒猜到有刀子。接著他開始狂暴地旋轉,身體每個部位各自轉起刀刃,力道足使蛛絲穩穩落上他之前便被切斷。
換個戰略。蟲群這次,花時間經過他身上,一次用上三、四十隻蜘蛛,它們延續、不懈地工作著。每隻蜘蛛都切斷了蛛絲,好讓絲線如風中細繩飄落。
溫柔落下而不是被緊緊扯上,蛛絲會覆上旋轉刀刃,與其他拖曳的絲線相連,然後形成一朵鬆散幽雲。
我預期過這情況了。
讓我猝不及防的部分是他也換了戰略,第二次攻擊平民。
「喂!」我在他身後吼道。
我希望自己第二波攻擊更隱密一點。
我從基地帶來的一半蟲群也仍在等候指示。我在奔跑追逐偶人的同時也派上它們,停留在其他二比四吋木條堆旁。
某人在偶人開始切進人群時尖叫。三人中有兩人,被那個怪物逼進角落。其中一人已經受了傷。
「混漲!住手!」我吼著,言語無用。
我繼續進展到攻擊第二階段。在弄過原子筆、簽字筆、蠟燭和消毒藥劑罐子時,我也指示要蟲子帶來我手中的物資。
有些蟲從我在做假面服時的作品中,帶來絲布碎片——我試做的面具、皮帶和帶子。絲線飄落於空中時,它們鉤上刀刃,而沒被切斷。偶人上半身很快就有了道深色糊影刀炫風。
其他蟲子也載來我假面服設計物資的殘餘物。一管管足夠堅硬到被刀刃切斷的顏料,創造出小團、潮濕而又五彩繽紛的爆炸。一大罐糨糊被送到我手中,我趕緊扯開蓋子後,讓一大群蟲子把糨糊運送到他那裡,在他頭上倒下,好讓那一團團糨糊能噴上他腦袋和肩膀。一袋袋染料被刀刃斬半,擴散出朵朵黑色、棕色、灰色和淡紫色粉末霧團,黏到他身上的任何液體,也填起他武器穩穩嵌合的隱密狹縫。
我把二比四吋木板低揮,將其舉上到偶人這個電鋸最寬處。我運氣與急切之下,成功掃過刀刃末端,把它頂上天花板。他旋轉的動量也勉強被停下來。他一倒,撞上身側,正如字面上地,在落倒的過程中四分五裂。鐵鍊連上所有東西,但右臼槽裡沒任何東西。是某種抗衝擊的內建保衛機制嗎?
我的蟲群落到他身上,到能拉出更多絲線、噴灑黏液之處——從我蜘蛛而來的有機黏液和品牌黏液全都有。
他開始緩緩地,拉回各個身體部位。我趕緊抓住一隻他從鐵鍊切斷的手臂,把它猛力扔走。接著我就抓住他的頭。
我知道他腦袋裡面不會有特別重要的東西。腦袋作為標靶太明顯。但我的手也能簡單抓住他腦袋,他腦袋沒連接上太多其他東西,也有他想保留頭部的機率。
我抱著那顆頭,往後一拉,從脖子裡拉出更多鐵鍊。重重一拉,就將他身體半扯向我,這樣費勁也使我身上每道傷口都尖叫抗議。又一次拉扯,我將他身體往後拖半呎,但我也拉出一、兩呎長的脖子鐵鍊。
就算有東西塞黏住機械,他的胸口裡顯然有比他其他部位更強力的機械。鐵鍊開始慢慢收回。
有人出現在我身後,他雙手抓住鐵鍊,正好有些在我身後。他將自己的力量加給我,偶人的身體又被拖後了兩、三呎。
「哪裏?」他問。這位魁梧路人有著濃厚黑鬍子、帶著厚鏡框眼鏡,穿了件紅黑條紋的T恤。我的人的其中一人。
我轉身,放開手來指。那是個曾繞了些設備的金屬框架。現在它空出來,就只是金屬條相連。
「後退。」他說。我放開手退開。沒我擋著路。那位路人就能搬偶人四、五呎,到鐵架那。又搬起一次,他們就和鐵架夠近了。
我趕緊上前,抓住那顆頭,把它繞過金屬條底下,綁起最粗糙的死結,在這過程中也把它纏上鋼條。他頭吊著,碰撞天花板。十五呎鐵鍊在它與偶人的身體間垂下。
偶人才剛勉強捲入鐵鍊,重新接起他的手臂,然後用手來將雙腿穩穩接上。
我只有數秒鐘。
我有蟲子在這區域裡,準確知道要在哪找出我想要的東西。我趕緊跑到角落,舉起一塊燃渣。
看見偶人站起時,我回頭還沒走到半路。我放棄計畫,放下那燃渣塊然後退開,繞著他,在我與他的頭之間拉出距離。他的注意力顯然是在我身上。
我惹惱他了嗎?
他沒再轉動,我也能看見蟲子加工後的損傷。他身體四處都是濃厚的蛛網和積起的碎布塊,只有一半刀刃在絲線、黏膠和其他垃圾之下成功收回。顏色在他身上留下條紋,有顏料的液體和染料的粉末。
我聚集起蟲子成另一波隊伍。我們快用完蛛絲了,但我得要應付才行。
他走向前,動作比平時更笨拙。很好。這可能表示求關節不再處於頂尖狀態了。
他又移動了,切斷鐵鍊,將自己從我把他脖子鍊綁上的鋼鐵架所解放出來。他不再專注於我。我用蟲子感知,企求他的目標。
他的手臂。它軟弱地爬向他,用指尖向前刮爬。
我察覺到他想要什麼的瞬間,就重新引導一部份織網蟲群到那條手上。接著我蹣跚走到左邊,將自己放至他與他的目標之間。我的蟲群流過他。第七次低空砲轟。他在蟲子飛過時斬切,令人驚訝地展現出了情緒。
他伸手進他脖子和頭原本應該在的地方,抽出一把小刀。
我調整了姿勢。他是個巧匠,那把刀可能是任何東西。
他按下開關,小刀很快就環起一道灰色糊光。我認出那是兵器大師的科技。
有同樣視覺效果的那把武器,在利魔維坦身上造成了可怕的傷害。
他向前踏步,我向後走。那條手臂在我身後,跳起來。偶人用伸縮刀刃協助手臂飛向正確方向。它正要採取迂迴路線繞過我。
我的蟲子第十八次掃過無頭的偶人。
他再次撲向我。而這次,我不格擋斬擊,也不讓裝甲吸收衝擊。他的動作很難看,缺乏一隻手臂而失去平衡,但他站高仍有九呎,通常,不論他拿什麼武器,都表示他攻擊範圍很長。
我後退,迅速踏開,清晰意識到蜘蛛工作得不夠快,無法在他擊中以前阻止他。我迅速撤退,跑出房間。
有一道沈重衝擊的聲響,隨之是金屬敲鳴的噪音。偶人停止腳步,原地迴身,大步走回他撲來的方向。
那道聲響又傳來了。我追上去,試圖不一瘸一拐,也知道我幾乎做不了什麼事來阻止那個怪物。我跑過半棟工廠地面層前,看見那引走偶人的注意的東西。
那幫忙我對付偶人的男人,手中拿了塊水泥,他第三次將其砸上偶人的頭。那顆頭從鐵鍊上脫落,掉到地板上,稍稍翻滾。
那男人再次舉起燃渣塊,看見偶人靠近,改變了主意。他把渣塊扔到頭上就逃跑了。
偶人沒追上那攻擊他的人。他反而,停下來撿起頭,接著站直。我停在自己所在之處。
長長一段時間,偶人手平舉那顆頭。頭接著落到地上。
在他手臂噗地爬向他時的數秒被拉長。我的蜘蛛擠滿在那隻手臂上,將其用絲線纏住。現在,只有刀刃才能讓它移動,手指在絲線中掙扎,要移動到,能使刀刃下一波猛刺推進的位置。
偶人將注意力轉到自己的手臂,我將蟲群覆蓋上去。千條絲線,每條都由盡我所能找來的數隻飛行昆蟲所抓住,全部將那條手臂搬起升空。我將其載上天花板,開始固定,在手臂周圍築起一張繭。我的敵人將注意力轉向我,身體正姿面對我。他沒了腦袋,我發現他的肢體語言加倍難以理解。我這麼做,讓他煩躁起來了嗎?
他向前一踏,好像要撲擊,而纏繞住他的絲線妨礙的他動作的幅度。他的腿沒辦法像他所想要地移動,而他喪失了手臂、撤銷了平衡感。他倒下了。
「還想打嗎?」我問他倒塌的體態,心臟跳在我喉嚨裡。我站立,準備要在任何瞬間警覺中跳開。
他緩緩地,再次振作站起。他第二次用刀子閃過絲線。而在第二次嘗試時,我也第八次用絲網掃擊中他,希望使他失去平衡到他會捅了自己。沒這樣的運氣呢。
偶人站直,轉換他手握刀子的姿勢,舉起一根手指。左至右地擺著,同樣不贊同、譴責的手勢。
接著他轉身要離去,大步走向門口。我沒想阻止他。我身體也沒力氣了。
我用蟲子看著他離去,用超能力感覺他離去三、四、接著是五個街區外,之後他落到我的範圍外。他一離去的那秒鐘,我雙腿全沒了力氣。我在房間中央,雙膝跪倒。
我全身發痛。如果偶人沒打斷我肋骨或鎖骨之類的東西,他也打裂了某些東西。而痛楚卻只是一部份。身體上,我精疲力竭。情感上,更是如此。
夏洛特出現在我身旁,伸出手要拉我一把。說話的低語聲開始環繞我響起。我無視了。我接受不了批評,我也不值得任何稱讚。在我與偶人戰鬥時有多少人受傷?有多少人因為我沒戒備,就死去了呢?
靠著夏洛特的幫助,我站起身。我對她要協助我站立時搖了搖頭。我緩慢而小心走著,不想讓自己丟臉,我走到那被拆卸的腦袋。
十分細微,但看起來是鐵鍊穿出的脖子處有一滴黑色液珠流下。顯然這算是偶人願意拋棄這一部位的缺陷呢。我把它留在原處。
接著我跳走到那白髮醫生的屍體旁。雙膝跪下非常痛,但我仍跪了。我輕柔地將她的頭轉正,看著她睜大的雙眼。淡藍色,很詫異。
「我很抱歉。」我對她說。
我想不到任何其他東西要補充或說的。一、兩分鐘後我才放棄。我讓她雙眼睜著——用指尖闔起她雙眼,看起來很傲慢也很陳腐。
我用蟲子切斷絲線,讓手臂從天花板落下。不只一人被這猛然墜落和衝擊所驚嚇。
「把那顆頭和手臂扔進海裡。」我說,沒對特定的人說。「如果你們能找到一艘船,就把它扔進深海。」
「好的,」夏洛特說,嗓音沈靜。
「我要走了。我會用蟲子監看有沒有更多麻煩事。」我在自己開始朝門口跛行時,說道。
可以這麼說。我贏了。
#夏洛特 #偶人 #泰勒
ns 15.158.61.5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