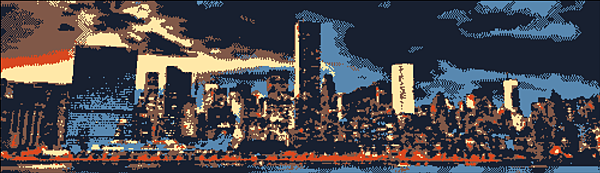 x
x
Disclaimer1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P4ZCMXl0n
【原作者贊助連結】1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WZXEElhzfj
在城市裡生活,就表示要在生活裡要處理一些重複發生的問題。犯罪率高、必須鎖門、路上塞車、人群擋住道路——我們如此經常面對的事,成了我們的日常。我們認為那些事情是背景噪音,或對其想都不會想了。施工則是我們無法如此輕易毫不考量的事,也不斷引人呻吟抱怨。也許是因為噪音如此公然喧囂,如此令人煩躁,其音調、位置與分貝如此頻繁變動到我們無法適應。
今天仍無法適應。
不,在推土機與打樁機開進我地盤裡施工時,我感到某程度的滿足與安全感。每輛車子一開上路,就有十台卡車載著建築殘骸出城、五輛卡車載入建材。
我知道有很多事情都是蛇蜷在做。我整片地盤裡到處是施工、清理工程,每塊街區上都有監工,就算有人警告說這裡有無法預測、大壞人掠翅出沒,依然有這些所有工程在進行,那就是因為,他有行賄或是施工公司都是他的人。
該死的,我很焦躁。我想去蛇蜷的地盤裡談黛娜的事,假使魔閃師沒先直接宣布說他要去和蛇蜷對峙的話,我可能就如此做了。我猜蛇蜷不會這麼快放走黛娜,而假使他在聽魔閃師的說法時受到太多壓力,他也肯定不會聽我說話。假如他確實有東西能提供給魔閃師,他更不會歡迎我去干擾他的心思。我得要等。我討厭等待,但我也認為那是合理的路線。
魔閃師的焦點是在諾埃爾,我能看出的跡象都沒顯示出蛇蜷在她的事上有任何進展。我所知的所有事情,真的只有媘蜜告訴我的小事——我們跟行旅人談論戰略時,在簡略談話中提起的資訊。她也許是個,健康狀態不佳的女孩呢。
魔閃師可能想拯救諾埃爾,跟我想拯救黛娜一樣。情況顯然有所不同:蛇蜷是行旅人在諾埃爾的事上的最佳選項,但他也是黛娜的困境的強加者。
不過,這讓我開始思考了。
我照官方說法,沒有管我的地盤。我現在也沒要違反命令、冒險讓蛇蜷不爽。這表示,我不能穿假面服,不能展現出我的臉,也不能介入管理面的事情。
這讓我的思緒轉到希瑞菈。就我的蟲群感知來說,希瑞菈比許多人都更容易被我找到。她的髒辮讓她的外型很顯眼。
我卻找不到她。
我能找到夏洛特。那不成問題——她在陪孩子們,就在一個半街區外給每個孩子六包塑膠瓶,要去拿給各個施工現場。
「我醒來之後妳就躺著,半睜眼,發著呆。」
我重重眨眼,之後揉了揉眼睛。「嘿。」
「嘿。」
我看向布萊恩。他起身坐著,被子遮在他大腿上。我瞥過他上半身。我之前看過的舊戰鬥傷口都已經消失。蟋蟀女在他胸膛上鑿出的淺傷疤也消失了,他雙手和手臂上的防禦傷和舊疤都一樣。他的身體處於完美狀態。也只有身體完美呢。
但我昨晚有點算是探索夠了。那並不是完美的夜晚,也根本稱不上很棒,卻很是美好。考量到所有其他丟臉、尷尬的可能性,我對美好已經夠開心了。
想起那件事情就讓我察覺到自己所做的事。我把被單拉上自己的鎖骨。「你有睡嗎?」
「睡了一點。半夜時醒來。我有發出一點噪音。很驚訝我沒弄醒妳呢。」
我皺眉。「你該叫醒我的。」
他搖搖頭。「妳太累了。我一看到妳在這裡,就讓我察覺到自己所在哪裏,才能把夢境當夢境。我花了點時間才放鬆,但是待在這裡,並不糟糕。」
我真討厭這樣,討厭他這樣掙扎,我卻幫不了他。
「你需要和人談嗎?找個心理科醫師?」
我可以看出他對這句話畏縮,上半身以近似於反射地僵化。
我等著,沒要逼他。
他嘆口氣。我看到那股預備戰鬥的感覺緩緩滲出他體外,那股緊繃離他而去。他放鬆了一點。「我們不都需要嗎?」
「大概是吧。但你才是我擔心的人。」
「我會自己搞清楚。得自己來,不然就感覺不算數了,那不會算是真正的回復。」
我並不喜歡這個回應,但那種說法也很難反駁。
「我不會拿這件事煩你。但你能至少告訴我這會持續多久你才會尋求協助?」
「這會好轉的。得好轉才行。我感覺自己有在前進,強迫自己放下戒心,在這裡和妳待在一起。」
我緊繃起來:「強迫你自己?」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是指,妳知道的。我⋯⋯我無法放鬆。沒辦法靜靜待著,也沒辦法不注意身後或讓腦子停止回憶那些場面。不過我可以做到這些事,假使我有在活動的話,假如我在做著像是對抗理龍那些裝甲的事情,或假如我跟妳在一起,我就在這裡,躺在妳床上,試著不讓妳被驚醒。之後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太激動,這也讓我在心裡,有了能強迫自己努力的界線。」
我的眉毛被憂愁拉緊。「你聽起來像是長期下來會有更多壓力吧。」
「不。」他說。他伸出手,雙手抓住我雙手。他緊握著我。「來嘛,不是這樣的。那真的是妳現在想談的事?」
「我非常想聊聊其他的事。」我說。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在說實話。把事態暴露在日光下的話會比較尷尬。只過了幾秒鐘,我就提起心理醫生的幫助,戳到他的痛處。冒犯了他。假如我不清空自己的腦袋、讓自己集中精神,我就不確定我會相信自己避免再次說錯話的能力。
「但是?」
「但是我跟我爸有約。時間⋯⋯」我頓一下,閉上雙眼:「現在是九點二十八分。我想我需要沖個澡、穿衣服,那可能會花一小時,還要吃飯、穿平民衣服快走過地盤,然後出發。我想花點時間跟你待在一起,但是在前一陣子的激烈活動之後,在今天早上放緩事情,就會感覺是個很好的點子吧。」
「妳怎麼知道時間的?」
「時鐘指針上有蟲子。」我說,指向廁所。
「啊。妳想要人陪嗎?」
我雙眼稍微瞪大。「陪去廁所?」
他微笑了。「陪吃早餐。假使妳想要的話,也能跟妳走走,我可以學點東西。我們共用淋浴間的話,就會忘記時間了吧。」
「是啊。」我說。「我們會吃早餐、散步的,拜託了。」
我爬下床,拉起床上其中一條被單,好讓我再走去廁所的時候有東西可以裹著自己。
我靠著蟲子,能感知到布萊恩在我拋棄床單不久之後也下床了,我走入淋浴間,把臨時的淋浴簾拉起來。他則走下樓,開始煮起早餐。他放下兩個盤子,之後對空房間說了些話。
我走下樓時,稍微有意識到那個場面。我現在已經穿上衣服——我穿了背心、牛仔褲,還有件綁在我腰間的汗衫——我用毛巾擦乾了頭髮,但頭依然是濕的。「你有跟我說話?」
「我說,有家蠅飛到餐盤上的話,恐怕不怎麼衛生。」
好吧,所以他沒在發瘋。
「它們是在盤子邊緣降落,而且它們是我的家蠅。從樓上的飼養箱拿出來的。它們跟你會要求的消毒環境一樣乾淨。」
「好吧。就說說而已。」
「說起來,我沒辦法用蟲子聽見你說話。這已經不是你第一次這麼做了。」
「是呢。我不是很確定,因為媘蜜說妳有在練習。」
我搖了搖頭「沒有進度啊。」
「我也很習慣對空房間說話了。有些時候還會嚇到愛紗。早餐?坐下吧,我會煮水。沒想在妳還在沖澡時就上茶。」
「謝謝你。」
我們心照不宣地,沒有聊起「工作」的事情。我們沒談論蛇蜷、黛娜、行旅人、理龍或屠宰場。我們的談話反而是轉到我們最喜歡的電影和電視劇,我最喜歡的書,還有我們童年時的記憶。我們聊起自己看過、幾乎忘記的節目,以及學校的回憶。
在我回憶時,艾瑪就很常出現。我的雙親也經常出現。他們三人就是我的世界的焦點,其他所有都是遙遠的次要優先事項。艾瑪討厭了我,我媽離開了我,而我爸⋯⋯我承認,是我離開他。
我沒提起沈重的話題,但我有談到艾瑪最後成為其中一位我還待在學校時就一直煩我的霸凌。
布萊恩,他則是講起自己成長的生活。那確實碰觸到了沈重的話題,就算我想知道更多他的生活細節,我也很高興我們繞到武術話題。他解釋時,說他自己對較為寬廣的手法、特定風格的理念更感興趣,沒有談到特定細節。一當他感覺出某個風格的追隨者處理戰鬥方式以及基礎技巧,就能看到他會如何實踐,他就因此經常失去興趣。
我能看到我們周圍各處,大家都在辛勞工作。我的人被進來工作的合法施工團隊指派出去,將焦點轉移到附近的區域。我可以看到大家把物資移出附近的建築,好讓施工團隊可以清除廢樓,其他人則幫忙卸下卡車的物資。當我回到這裡工作、開始下達命令時,我就得為他們找出不會讓礙事施工的工作吧。我沒辦法追蹤在我的地盤裡工作的人數,但他們比之前還要多。
我感覺自己每次要與重大威脅戰鬥時,都會失去人心。我在偶人與烙疤女站的手,是有失去人心,但我有從偶人第一次戰鬥之後緊接著做事,避開了餘波,我也預期看見自己的人在理龍出手後就大批離去。然而那並非現狀,我不全然確定原因為何。
我們的散步繞了圈,背對基地,然後我回去我爸那,布萊恩回到我的地方沖澡。
我對此的感覺很怪。整晚相依之後,如此隨性分離。怪異的地方是,我把他留在基地裡,我卻不在那裡,他會經過我的房間,看到我的東西。考量到晚上發生的所有事情,又想把自己用床單遮住、對隱私感到有防衛心,我知道這就會很矛盾吧,但那並沒有改變我的感覺。我不會因為這樣就拒絕讓他用我的浴室,然而這種感覺還是會存在啊。
從一方面看來,我們算是將所有事情反其道而行。我們從長跑的關係開始。假使我想以這種意義上思考,算是從「家人」開始吧。而在這過程中,我們經歷過大風大浪,支持、幫助著彼此。所有婚姻中可能要面對的負擔都有了。之後則比較近期、昨晚才發生的事,我們談論了關係的定位,之後是更隨意的約會,在今早更了解彼此。假使那不是百分之百反其道而行,也算是滿雜亂無章了吧。
或許我是以不成熟的視角觀看事物,然而那種視角也告訴我親密關係更簡單、更常規、像童話書般的進行方式。
我走到我爸那,同時思考著一千件事情,不想特別思考任何事。
有車輛停在我家門前。車庫庫門打開時也能看到室內有一輛奇怪的車子,另外兩輛停在車道上,我爸的車則在最外面。我靠著零星幾隻家蠅,隨意地注意到十幾人待在我家裡。我爸也在那群人裡。
我立刻想到蛇蜷。他推測出我今天做的計畫了?想策劃某種反擊?
我放棄穿自己的假面服,所以我在緊要關頭裡,不會感覺自己必須用上超能力,我也拆掉假面服上的刀套,將其戴上我背部腰帶,讓衣服蓋住刀子,也遮住了各品種的黃蜂與蜘蛛。這種安排可能對其他任何人造成不便,但我在過去幾週、幾個月以來,都靠蟲子幫忙引導我的手,我就對自己在衣服皺褶中立刻拔刀的動作,相當有自信了。
有個男人來開門。我讓自己放鬆下來。
「不會吧。」他說。「泰勒?」
「嗨,柯爾特。」我向我爸的同事兼長期好友打招呼。
「是有一陣子沒見了。孩子,我幾乎認不出妳了。」
我聳肩。「你過得怎麼樣?」
他大大咧嘴一笑。「還行。還過得去。比大家都還要好。這,進來吧,還是妳要在接下來五分鐘裡都站在車道上?」
我跟著他進屋裡。
我爸待在客廳,被熟悉的面孔所環繞。他們是我在去他工作的地方時,或是他們來訪我們家時,曾經看過的人。我只能認出我爸稱為朋友的人:柯爾特、柯爾特的妻子蕾西,還有亞歷山大。連蕾西都比我爸壯,身形很像瑞秋加上了肌肉。那三人對我來說是很眼熟,但我也不怎麼認識他們。房裡,我爸和我自己之外每個人都靠苦力活維生。光看我爸的話,他在服裝、體型和風度的各方各面都是異類,但他以我好幾年都沒看過的方式放鬆著,一手拿著啤酒,被朋友所環繞。
我爸看到我,嘴型說著「抱歉」。
柯爾特看到他的暗示。「別怪妳老爹。亞歷山大從城外買來一卡車啤酒,我們就開喝了。我們想說要把丹尼也拉進來,拉他一起來喝,就不請自來了。不知道他已經有約。」
「沒關係的。」我說。沒有人能構成威脅,也沒有蛇蜷的人。我讓自己放鬆下來。我剛是在想什麼?他會暴力要脅我爸?
「嗨呦泰勒。」蕾西說。「從葬禮之後就沒見到妳了。」
差不多是在事後兩年,這個話題依舊重重痛擊我。
「老天,蕾西。」柯爾特說。「在妳把那件事砸在這女孩身上前,給她一秒鐘讓她習慣家裡有人拜訪吧。」
我瞥了眼我爸,他手肘放上膝蓋,雙手抓二十四盎司的啤酒。他垂下頭、盯著酒罐。他看起來並不絕望,或甚至也沒有不快樂。那句話沒有讓他猝不及防到跟我一樣被重擊。我認識這些人,我也能猜出那件事常出現到,他已經習慣了。
「啊寶貝。」蕾西說。她朝我舉起一杯啤酒。「就只是有一點點醉了。想說,妳媽是個好人。她沒有被遺忘。抱歉這話說出口時有點太直接。」
「沒關係。」我回應。我雙腳焦躁不安。我從來沒在自己家裡感覺像個陌生人。不知道要去哪,不知道自己會從哪引來注意力,還有人問我問題。有我爸和我之間的距離,就已經夠難了,但現在還有其他人加入了計算的應變因素。
柯爾特開口道:「我們幾分鐘後就要離開了。很難到處走,所以他們就把活動安排在一起,這樣我們就不需要跑兩趟。最後一場辯論會在下午舉行,之後立刻就是市長選舉。你們昨晚有看辯論會嗎?」
我搖了搖頭。「連有辯論都不知道。」
「那麼,假使要說起之前的事件的話,這場辯論會就肯定會很糟糕。所以我們就會喝酒放鬆。假使妳爸喝超過一杯啤酒,我感覺好更多,好讓他可以稍微放鬆,不會跑去掐死這些拍馬屁的混帳們。」
「不會做那種事啦。」我爸說。
「希望你能放鬆。但如果你被關進牢、讓妳女兒孤身一人的話,就不值得了吧。這樣才都好。我們一起渾身酒臭,在旁邊講些醉鬼的評論,罵幾個下流髒話吧。」柯爾特微笑。
「請別那麼做。」我爸說。他沒將眼神從手中的啤酒中抬起,但他在微笑。
「妳想坐下來,讓他們說說他們自認為好聽的話嗎?」柯特爾問。
「我是在想,假如我們有機會的話最好先問困難的問題啊。一大部分會是從北邊來的人。他們好一些人都從碼頭出身。那我們為什麼不先問問渡輪發生什麼事了?」
「他會避開不談的。」蕾西說:「其他所有事情也一樣,那不被算在成本之內。」
「那麼,那就是噓聲和醉酒叫罵的好時機了。」我爸回答,微笑著。
柯爾特爆出笑聲。「丹尼,你想鬧出一場暴動嗎?」
「不。但也許會讓猶疑不決的人看到我們有多麼不被那個人感動吧。」
「所有人都很不爽克里斯特納市長啊。」亞歷山大朗聲說。他是比較年輕的男性,身上有很多刺青,濃眉也讓他有一對永久怒目。每次我看到他,他的髮型都很狂野。今天他將左側三分之一頭髮剃光,炫耀出新穎的老派比基尼女郎刺青,女郎的手肘出現在他耳朵上。
「是災難造成的。」我開口說。「我們想怪罪人,而管事的傢伙就成了簡單的目標。」
「他是應該成為目標啊。」柯爾特說,他坐到蕾西的椅子扶手上。她將一隻手臂繞過他腰間。他繼續說:「華盛頓裡也發生了事。說他們應該要在城市周圍建起牆壁,擋住街道、關閉設施,把所有人弄出這裡。」
「他說不要,是嗎?」
「他說不要。真是混帳。八成是因為這樣做會賺更多錢吧。收下振興、幫助這座城市的幾百萬元,也順便讓他收一趴的錢。」
這很讓我驚訝。「你不想拯救這座城市、不被譴押?你想被踢出城?離開家鄉?」
「那會很糟糕,可是報紙上談論的方式,說會有一大筆資金分出來要擔負他媽的終結召喚混帳造成的損傷。那個就是他們要撈那些資金,給所有他們剝削的人一點點錢來支付整修的帳單。」
「不可能是那樣吧。」我說。「那在要疏散時,留下來的人呢?」
「不知道。」柯爾特說。「我只是說報紙上說的東西而已。」
我有種不好的直覺。「然後他們會給我們房子曾經的價碼?」
「他們會給我們房子現在的可能價位。」他說。
「所以不會有多少錢。」
「那還是比房地產在接下來幾年內的價位還要好,之後老鼠會住進房子、任何黴菌問題都會惡化。把物資弄進城裡也會很貴,也表示修理、整修都會很花錢。也不盡然值得整修。」
「我看到有施工人員在工作。」
柯爾特大口狂飲啤酒,清了清喉嚨:「當然。好幾家公司買了所有的材料,用低價買地,所有人都希望全城一起行動,希望土地最後會有些價值。」
「是可以有價值的。」
「來嘛。」他把這句話說成呻吟:「我們處於超亞人類的專制之下。英雄也沒能做事。他們之前在數量上被壓制,但還是有在努力,在一些小地方上做出改變。現在他們數量被壓制,然後也輸掉了。這還有什麼意義呢?」
「就只是個假設性問題。」我說:「但反派統治的城市,讓街頭生活有運作的話不是更好嗎?反而要讓城市失能,相同的這些反派處於較不顯著的位置?」
蕾西呻吟了一下:「甜心,我喝太多酒,沒辦法弄清楚這個問題了。」
「也許是時候別再喝了,蕾西。」我爸說。他轉向我,說:「我認為妳問出了個經典問題,泰勒。妳比較想當天堂的奴隸還是地獄的自由人?」
「地獄的自由人。」柯爾特回答。「媽的。你以為我工作,在這裡生活,是我願意討好、拍管事的人的馬屁,想聽令行事?」
其他一些人點頭,包括了蕾西和亞歷山大。
我看向我爸。
「丹尼,你的答案是什麼?」柯爾特問道。
「我寧可不要當奴隸,或是待在地獄。」我爸回答。「但有些時候我擔心自己同時處於兩者之下。也許我們沒有選項?」
「你是我朋友裡最令人憂鬱的混帳啦。」柯爾特說,但他說話時帶著一抹微笑。
「泰勒,妳為什麼會想問呢?」蕾西問。
我聳了肩。我能說多少東西,同時不讓他們起疑心呢?「我有在避難所裡看到一些東西。有些很病態、很不快樂的人。是在事態開始有點好轉的前一陣子,然後就我所理解的,是反派先行動、修正那些事情。」
「為了他們好。妳不能統治地上的那個大洞啊。」亞歷山大說。
「也許吧。」我說。「或許壞人可以因為想做好事而做好事,至少偶爾可能如此。他們有在管事,想讓事態或多或少保持安靜、和平。比之前的情況還要好吧。」
「那樣的問題是。」我爸說:「我們若讓那種事情發生,就會讓人類退步三千年。退回鐵器時代的心態與領導。有人數和武器的人會透過純粹的軍事武力佔領一片區域。他們持續領導,直到他們能透過家族血脈,與其他有軍事武力的家族聯合。這樣持續到掌權的世族逐漸消失,或有某個更聰明、更強壯或武裝更強的人來奪取控制權。這聽起來也許不壞,可是妳遲早會發現,獲得控制的人就會是某個像凱薩一樣的人。」
「凱薩死了。」柯爾特說。
「是喔?」我爸抬起一邊眉毛。「好吧,但我是從通泛來談。那可以簡單換成竜或快斬傑克,不過現在是相對仁慈的反派們在管城裡。我這樣說是想強調,那只是時間的問題。」
在我們輸掉——我輸掉——然後有其他人宣稱布拉克頓灣屬於他們之前,就只是時間的問題,我想著。
「你比較希望什麼事情發生?」我問。
「不知道。」他說。「但我不認為滿足現狀就是正確答案。」
「上一場辯論。」科爾特說:「大家一直提假面,主持人一直叫他們閉嘴,跟他們說應該要談經濟和教育。今天我們會聽見有人談起那些在經營這城市的壞蛋吧。聽見候選人得要對這個話題所說的話。」
「假使我們想要座位,而不是站著聽。」蕾西說。「我們應該要盡快出發。」
我爸抬頭看向我:「泰勒,我能給妳任何食物嗎?我答應妳說要吃東西的。」
「我沒關係。早餐吃得很晚。也許等我們回來時再吃?」
「我會給妳酒。」柯爾特說,輕笑著:「但那會違法。隨便啦,妳幾歲了?」
「十五。」我說。
「十六。」
我轉頭看向我爸。
「今天是十九號。」他說。妳一週前就過生日了。
「喔。」我那時候是有一點分心。一週前,就是我們正在了結屠宰場九號的對抗戰。這樣可真好啊。
「那可是我聽過最他媽的讓人傷心的事啊。」柯爾特說,從扶手起身,幫忙蕾西站起來。「女孩子像這樣錯過生日。那,我猜妳也沒駕照,嗯?」
「沒。」
「該死。剛我還在期待妳可以成為我們的指定駕駛,讓妳爸能再喝一杯。」
「我只喝半杯高腳杯。」我爸說,稍微晃了下他的罐子,讓我們聽見杯中物攪晃於杯壁的聲響。「而且我們不管怎樣,都會在這種路面上開得很慢。誰要開另一台車?」
亞歷山大舉起手。他只喝了一杯水。
「那麼我們就出發吧。離開我家了。」他說。我可以看到他用椅背協助自己站起來時,因痛楚皺眉,但他有在恢復健康。他開始把那些壯碩的碼頭工人趕出門。「去。到車上去。」
我們開始魚貫而出。柯爾特和蕾西爬進了我爸車子的後座。其他人則搭亞歷山大的卡車。
「你腎臟有傷還能喝酒嗎?」我在關上門時,問道。「你站立都有困難了。」
「我昨晚確定過了。我會回復正常飲食。任何痛的地方都只有肌肉和縫線。謝謝妳關心我。」
「我當然會關心你啊。」我說,皺著眉。
「妳變了。」我爸評論道,將手肘歇在車頂上。
「嗯?」
「不久之前妳碰到那種情形就會沈默寡言。」
「那感覺像一年前的事了。」
「不管怎麼說,我都很抱歉。」他說。「我希望今天只有妳和我,有機會聊聊。他們就不請自來了。」
「沒關係的。我很高興你有這樣的朋友。」
「他們是有點太專橫了。」我爸說。
「窗戶有開一點喔。」柯爾特從車裡,說。「我們可以聽見你說的話。」
「他們太專橫了。」我爸重複說道,拉高了一點嗓子。他最後,以普通的音量說:「但他們也還行。」
我稍稍微笑,爬進副駕駛座。
「喂,泰勒?」蕾西問。她的嗓音過度溫柔,我頓時間以為她又要提起我媽。我稍微皺眉。
「幹嘛?」我在座位上轉身,盡可能係上安全帶。
「就只是想說感謝。謝謝妳那次的警告。妳跟妳爸說碎歌鳥就在附近,不是嗎?」
我點頭。
「他有跟我們說了。我們也很小心。我不知道那有沒有救到我們一命,但謝謝妳為他留心危險,也謝謝妳幫了我們,算是間、剪接⋯⋯」
「不客氣。」我在她繼續說不清話以前,說道。
我是很高興他有跟他們聯繫。從我所看到的事情來說,我很擔心我爸全然孤身一人。像他這種——像我們這種——內向的人,最好跟全世界的柯爾特搭配。或跟莉莎搭配。可以說是,要感謝有那些不會被無視或不重視的人、推展疆界的人把我們從甲殼裡拉出來。
我在我們前往鬧市區時,享受著兜風車程,我比自己想的還要更享受於其中。我爸和柯爾特認識彼此到他們的對話輕鬆交通,而蕾西與柯爾特也同樣如此,那兩人談著自己的婚姻的事。我感覺,柯爾特最後感到自己來不及跟兩人交談。
市鎮廳存活過了海浪。那棟石造建築有著槍眼,還有著美國國旗掛在門上。我們加入了排隊的人潮,經過有候選人海報、照片、議題小冊子以及鄰市報紙的攤位。我爸和柯爾特各自拿幾疊報紙,放入攤位發送的塑膠袋。將那些東西發出來的這個想法是很不錯。現在沒有任何電視,我們也得想出辦法持續肩併肩合作。
路標領我們經過古舊的歷史縣府大樓,到了觀眾席。我們預期座位會被坐滿,讓我只能待在站立房,但那裡恐怕也一樣滿員。觀眾席背後以及座席邊緣都滿是記者和攝影團隊,剩下的人群填滿了排排長椅。五、六百人。稍微比我以為的還要少。
這算是一場奇怪的選舉吧。城市一周半裡都沒有能運轉的電腦,也沒有電纜殘存。選舉中沒有媒體廣告。有很多人在這裡,是在他們投票前第一次聽到候選人對一些議題的立場。這就是過往的作法嗎?比較貧窮的家庭沒有新聞報紙,也沒有電視或無線電?
我看向候選人。有位穿深藍色套裝的黑髮女人,有個金髮男人,還有較年長的現任者,克里斯特納市長。這個觀眾席裡多少人有意識到呢?一段時間以前,蛇蜷告訴我們競選人裡有兩位已經被買下來。克里斯特納市長⋯⋯嗯,我能想起自己站在他的後院,他的槍指著我,懇求我插手拯救他兒子的性命。
辯論會會轉向,要他澄清自己為何反對譴押這座城市,這樣,克里斯特納會怎麼解釋自己所做的決定呢?
我被困在罪疚感以及對即將發展的事件的真誠好奇心之間。我大部分是感到罪咎,但我無法對此做任何事。我已經做了必須做的事。
我在好奇之中,頓時納悶蛇蜷的市長候選人有沒有軍事背景,或他是親自挑選政客,就像他挑選自己的菁英士兵嗎。
有某件事引起我的注意時,那道思緒便頓止住。
現在我習慣性地,讓蟲子掃過周圍,讓我永久感知到三、四個街區半徑內發生的事。當幾輛小貨車在建築附近停下來時,那並沒有引人注意。而當士兵們開始走下貨車,我輩嚇了一跳。男人女人們拿著機關槍、身著防彈裝甲。不是PRT的人。
不。絕對不是PRT。
裝甲的大轎車停靠在接到正中央,就在前門門外。等到蛇蜷走下車,他的士兵正好經過建築兩側的門,或是站著準備陪他走到前門。
蛇蜷,在這裡?這不合理啊。他不是那種會公開現身的類型。這不符合他工作的方式。老天,假使市長在這裡的話,他的兒子也會在這。威揚會在人群中。
我瞥向我爸,他握緊我的手:「沒太無聊吧?」
我搖了搖頭,試圖在我的思緒奔馳時讓表情無動於衷。
蛇蜷現在,要在這裡出牌了。
#夏洛特 #蛇蜷 #戰慄 #泰勒 #泰勒她爸1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IGjD20Y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