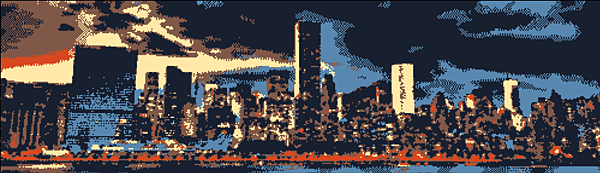 x
x
Disclaimer2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1ET7AfIWpE
【原作者贊助連結】2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8cCrJGObs
沈重。我身上的重量使我呼吸變得很困難。在身體想呼吸卻無法吸入空氣時,我感到撤退的應對機制被觸發。我無意識、半茫然地甩出手。我成功讓上半身掙脫出來,奮力無視我抬起身體上方的屍體時,我每個關節、每根骨頭的痠痛。
這股感覺不像睡眠,或失去意識時的黑暗,但我也沒在思考。我頓時感到混亂與疑惑,納悶著自己是否有腦震盪。我的思緒感覺對腦震盪來說過於清晰。
屍體。我爸呢?我睜開雙眼,卻只看見濁白色?這是塵埃嗎?這很近似於我睡眼惺忪的時候,但不管我眨了幾次眼睛,都只能看見模糊的亮光黑暗。眨眼、讓眼睛移動時,我臉上的眼皮就感覺到燒灼疼痛。更煩人的是,我眼睛裡有東西,不管眨幾次眼都沒有幫助。我眼睛受損傷了?
我筆直看向爆炸是很蠢呢。我以為自己會在轉頭、閉眼前,有半秒鐘可以察覺到剛發生的事。顯然那麽做也不夠好呢。
我爸。對。我伸手要找到他的喉嚨。他還有脈搏。我將一隻手放到他嘴上,發現他有在呼吸。
我四肢健全,他也還活著。其他任何事情都會很難確認了。
我被迫要用蟲子視物。它們的眼睛所接收的資訊可能無法在我的腦子裡妥當轉譯,但這就是我能做到的解方了。我不想要移動蟲子、聚集起蟲群。那樣的話,要追蹤我、找出躺在傷者之中的掠翅,就會過於簡單。
不,我只有觀看,將蟲子留在原處,只用一撮蒼蠅用以感知必要的事物。我能感受到微風。建築前方有個洞口。大廳被摧毀,大片屋頂被開了個朝天大洞。停在建築周圍的黑色麵包車車頂上有著閃亮的燈光。警鈴。他們是現場應急人員。
我注意到建築損傷。我試圖拼湊起自己最後瞥見的情景。那裡有什麼東西?有誰在那裡?
記者在房間最後方,也是最後從走道下來的記者群,那群人之中也有離席的觀眾。有些人留在後方,想保護儀器或拍攝這個場面。我小心翼翼移動一隻蒼蠅飛過那片區域,感知到殘破的木板、滿是血灘的地板、燒成炭的血肉。
好幾位監護者在幫忙照料傷員。吊擋鐘顯然救了監護者們,但太晚照料自己,現今他趴倒在地上,接受其他監護者的照料。戰車已經不見了。
之前有上百人在現場,太多人在爆炸時仍待在建築內。那位爸爸與兒子被綁在大廳裡?市長、候選人和主任都有被打傷、被留下來,之後爆炸炸傷了那些留下來照料他們的人,把他們炸飛了?
我不引入蟲群的話,就沒辦法掌握這場面的所有狀態,而那樣做的話,我也可能會在處於脆弱位置時,暴露出自己的存在。
我感知到周圍,發現了柯爾特還有蕾西。
「嘿寶貝。」蕾西說。「妳醒了。」
「妳受傷了?」
「就只是一點輕傷。可能有脫臼。八成沒什麼大不了,但我還是痛到必須盡可能待著不要動。我有照看妳爸,看看他是不是真有在呼吸,還是我想像他有呼吸。妳沒有被嚇到,所以我想丹尼是沒事?」
「我想。他是沒事。」
「很好。柯爾特失去意識了但他還好。妳有在什麼地方看到亞歷山大嗎?」
我眨了幾次眼。她沒發現我看不到?「沒有。」
「好吧,甜心。妳應該盡可能不要動。」
我搖了搖頭。「不。我會去看看有沒有任何人需要幫忙。」
她抓住我的手,開始說了些話,之後皺了眉頭。
「怎麼了?」
「就只是,很痛而已。待在原地吧?這樣做最安全。」
我搖搖頭。我沒辦法說清楚,但我感覺自己經歷夠多場危機、承受夠多苦痛,我會意識到痛楚使我察覺到的事。我幾乎肯定自己沒有處於緊要關頭之中。這就是我的直覺所說的。
只有幾隻小蟲領著我,我就留下我爸、柯爾特還有蕾西,爬上階梯到破損的舞台上,摸索找尋其他傷者。我幾乎只能從觸碰、從我雙眼與蟲子給我的模糊景象,推算出粗糙的狀態。有個女人,和我爸一樣失去意識。有個男人,他雙手抱住他的下腹部,在無止境的痛楚中扭動。
市長。我爬到他那邊,將手指壓上他的喉嚨。他有脈搏,但心跳很纖細。我將蟲子從我頭髮裡的隱藏處拉出來,命令它們爬下我手臂,我也試著彎起手,好讓頭髮遮住我在做的事。一等它們爬到他身上,我就將蟲子派到他身上各處,注意到了他身上的血跡。我用雙手摸索也不會有用處的。我不想碰到飛刀、將其推到重要部位或塞進動脈裡。其中一把刺穿他臀部的刀子有被移動,八成是爆炸時移動的,而這些武器也無法阻止血液流出。
我拉起自己綁在腰間的汗衫,把刀子留在腰帶上,折起一隻袖子,將其按在刀子所穿透的地方。這樣仍不夠,感覺不像是有達到任何效果,但我也不確定自己可以做到什麼事。我沒強壯到可以做胸部按壓。
「救命!」我喊道。「我這邊需要幫個手!」
沒有人過來。任何待在這棟建築裡的其他人,都太忙著照顧自己的傷口,或是仍失去意識,或是正要走到室外。
去他們的。
去他媽的蛇蜷。我會要他對這種做法說出個解釋。
是啊,我看到「蛇蜷」死去。我幾乎不懷疑其他人也有看到,連新聞攝影機也有拍到那個場面——新聞的攝影機特別會拍到吧。蛇蜷策劃這場襲擊,利用記者們的攝影機,而在沒有通訊系統、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出席的這件事上,這一點就很明顯了。他理解能力過強,在計畫上有太多投資,無法將所有變因都算進來。我知道他的能力,就讓這整個場面的意義被翻轉。他不可能在毫無後備、沒有另一個版本的自己留在安全無憂的地底基地,在沒有防範事態惡化的措施時就那樣衝進來。
不。我可能看到那男人死去,但我越多想,我就越不相信那男人就是蛇蜷。
應急隊伍停在外面,就在建築邊緣。我透過蟲子聽著這片區域,但我也沒辦法追蹤任何對話。就連追蹤說話的人也近乎不可能。
不論他們在談論什麼,都大步走入室內。有些我猜可能是警官的人員,移動到受害最嚴重的區域、記者曾經待著的地方,以及大廳裡。醫護人員繼續走下走道,確認傷員,他們的腳步對我來說太慢了。
「救命啊!」我喊道,但我的嗓音幾乎被其他傷患淹沒。在醫護人員看到市長、趕到我身旁的時候,已經過了一、兩分鐘。我能從自己放到他身上的蟲子來辨認他,但我無法確定他的職務。
「我接手了。」她說。那個醫護人員是個女性。
我感恩地退開。就連拉扯臨時繃帶的力道,都讓我在急速放鬆時,使全身每道痠痛、痛楚變得無比清晰。
「妳名字是?」她問我。
「泰勒。」
一小段距離外,我爸呻吟出聲,就像他聽見了我的聲音。我注意到他的聲音,是因為我放在他頸動脈上的蚊子,而不是我耳朵真的聽見他了。我表現得像自己有注意到任何事情。
「泰勒,妳不應該移動的。」
「我身體很痠,但我不認為我有受傷。我想幫上忙。」
「妳有哪種疼痛嗎?」
「瘀傷、刺痛。我爸受得傷比較重。」我指向他大致的方向。「我的臉很痛,而且,呃,我也看不到了。」
「別擔心。等我們盡快照顧好嚴重受傷的人,我們就會來看看妳了。」
「我還活著。」我說。「我是說,我沒事。我寧可你們去看看我爸和他的朋友,確保他們沒有受傷,幫忙其他候選人,還有主任。他們在爆炸之前就有被捅傷。他們都有受傷。呃。他們在炸彈爆炸的時候有想要起來。我認為幫忙他們的人被爆炸轟走了。」
我在胡言亂語了。我真的沒事嗎?
那位醫護人員吼道:「布魯士!史登凡特!曼利!這女孩說MSW傷患在這邊舞台上!」
我可以聽見跑動的腳步聲,一隻蟲在他們跑過來時掃過其中一人。
我在這裡沒多少能做的事。若是使用我的能力就能幫助人的話,我會很高興地揭露自己的身分,也許那才是最重的傷,我也很擔心那會造成更多傷害——從在短期和長期來說,好處都不會超過壞處。我就坐在那,盲了眼,醫護人員確認了我爸,之後找其他人幫忙把他抬離地面。
在醫護人員確認了還活著的人時,其他人醒過來了。我可以聽見痛楚的尖聲、吼聲還有尖叫。
蛇蜷會為此付代價的。為了他自私自利時所傷害的人,為了在知情之下,仍將我擺到火線上,為了他像花錢般消損的人命而付出代價。
「泰勒,是吧?」那位醫護人員問我。
「是的。」
「妳很安靜。妳的呼吸很重⋯⋯」
「我很生氣。也有一點痠痛。但我沒事的。真的。還有其他人需要幫助。」
「其他人有幫助了。我們這裡有很多人,也很少人有重傷。妳臉上有燒傷,我們得要照看這個傷口。」
「還有記者,在觀眾席後面⋯⋯」
「我以為妳看不見。」
「我記得在爆炸之前,我有看到他們在那裡。」
「非常少數人有嚴重受傷。比妳可能認為的還要少。保持冷靜就好。」
假使我沒用蟲子看見證據,我還能夠分辨她是否在說謊嗎?
她要我保持冷靜。這很怪,但我感覺非常冷靜,我也沒感覺自己像在震驚之中。我很不爽,我很擔心我爸,也很擔心我會錯失蛇蜷總體計畫的某個關鍵點,但我沒有恐慌,我也沒很在意燒傷,或眼睛之類的任何損傷。
就傷來說,我面對過更糟糕的情況。我不會被這種事情嚇壞呢。我很喜歡能看到正在發生的事,不必擔心永久眼盲,但我不會過度擔心,直到我能確認眼盲有多糟糕——確認這就是永久狀態。
我有點感覺像自己正看著世界可能面臨的終結。我不會擔心那種事情,直到我們耗盡所有能用的資源,確認我們這時代裡,有能力打破現實基礎法則的無數人們都無能阻止這件事發生。
「我很冷靜。」我在確認自己的心神後,說。我想深呼吸展現出這一點,卻對瘀傷的痛楚皺起眉。我之前可能有被爆炸的衝擊力推上欄杆。「但我不想要妳擔心我。我爸⋯⋯」
「階梯旁的禿頭男性?」
「那就是他。」
「我的夥伴在照顧他。我們要先確定妳沒事。假使我們無視脊椎傷害或是內傷的話,妳這樣移動,狀態會比現在還要更惡化。」
我閉上雙眼,注意到模糊的白色逐漸被黑暗浸染。我可以記起利魔維坦打中我的方式,以及萬癒如何注意到我全然沒察覺的內傷。我嘆了口氣,睜開雙眼盯著那個模糊的人影。「好吧。」
「我們會要把妳放到擔架上,但我們一陣子裡都不會把妳抬出去。我們沒辦法把妳自己留在這裡,但我會需要去幫我的夥伴把妳爸抬出去。我們會把妳放到某個人旁邊,好讓有人可以同時看著你們兩、三人。」
「好的。」
我被抬離,接著被帶到一小段距離後就被小心放下。醫護人員正在對其中一位傷患談話,讓我能自由思考了。
為什麼呢?
這就是讓我不解的地方。整件事——傷害這些人、將我放入伙限——都幾乎毫無意義可言。為什麼要襲擊這場活動?這會引來全國各地英雄們的注意,讓這座城市更難被掌握。他放棄計畫了?或者是有我沒察覺到的細節?
這事件發展的方式,是刻意為之嗎?他想解決市長。但候選人呢?他們不是他的人嗎?
我是從錯誤的角度觀看這件事。戲團。她從一開始就是這場計畫的一部分,他是為了明確的理由才雇用她。她的超能力包含個人儲存物品的次元口袋。我想不出那能怎樣被使用。她有較弱的操火能力,那也不會適用這場事件。她還有平衡感與肢體協調的強化能力。
平衡感在這裡並不重要。但肢體協調?她能隨興朝身後扔出刀子,還能瞄準皮戈特?假使我得猜測的話,戲團的刀只殺了蛇蜷想殺死的人。其他都沒擊中重要區域。她的強化手眼協調會讓她確保刀子精準擊中她想擊中的目標。
上人呢?黑客文呢?雇用他們的理由是什麼?當我們離開籌款會時,蛇蜷揭露出他的雇主身分,蛇蜷身邊有車骸,但車骸加入商團——八成是聽從蛇蜷的指令行動——而商團也被消滅了。他死了。
這就讓我納悶,蛇蜷將上人拉進來替代車骸,穿上另一套沈重的鋼鐵套裝。
那就是蛇蜷想這麼做的原因嗎?
戲團、上人、黑客文、戰車、候選人⋯⋯都是我沒察覺到的巨大機械的零件。記者、我、我爸,還有這裡任何人,我們都是旁觀者,也是傷亡人員。
我也無法理解原因。是要攻擊或刺殺市長和主任嗎?要將自己的候選人標註為超能反派攻擊下的生還者,給他們更多公眾眼光下的立足點?這不合理。假使這就是他的目標,為何還要花這麼多心力把暗地黨與行旅人部署到城裡?他從我們佔地盤時能擠出的滴點好處,會被他在這種恐怖行動後引起的混亂與國家的關注,全被反制吧。那些焦點不會指向他,因為他的替身在襲擊時被殺,但那也不會有幫助啊。
思考一下,我就幾乎相信炸彈是刻意之舉。我無法說明他怎麼安排的,但事實是,他想要有個替身男人死去,「蛇蜷」便直接從每個人的雷達上消失,這看起來有點太巧合了。
我得反覆思量的這件事。幾分鐘過去了,我只剩蟲子可以移動,而被分配來照看我的醫護人員會偶爾檢查我的狀況,確保我還活著、保持清醒。我將蟲子引導到殘骸之中,跑到從觀眾席被拆下的階梯底,爬到人體下方上方。我能緩慢地,拼湊出更完整的場面——蛇蜷所造出的形貌地勢。記者被化為粉塵,四肢與骨頭被扯碎、零散在走道兩側與下方椅子上,我就無法數算屍體了。
「我們現在要搬動妳了。」一個男人說。
「我?」
「是啊。待著、不要動就好了。」
我被抬到空中,被搬過觀眾席後方的殘破墻壁。我能聞到死亡的氣味,混雜了鮮血與糞屎的氣味,有人體被大大扯開、燒傷,玻璃體液與所有人們體內的噁爛穢物都暴露在空氣下。這似乎跟我臉上的微風與溫柔暖和陽光毫不相合。我得轉頭,好讓太陽不會曬到我的燙傷。
這種災難不是該搭配雨水?或陰鬱的天空嗎?這天氣是如此沈靜、冷靜,許多人死去、損失愛人或遭受重傷的這一天卻如此寧靜,就不太對了吧。我咬著嘴唇,集中在蟲子上,在救護車開到醫院、後車廂的醫護士小心確認我的生命指數、詢問我的疼痛程度或哪裡僵硬,他們也確認了我身上可能有內傷的僵硬組織,我在這時就把蟲子掃過這片區域。
我被載到自己在跟利魔維坦戰鬥後的同一家醫院,這是很怪呢。我保留幾隻蟲子用來感知——假使我不礙著人的話,一隻家蠅或蚊子就不太可能引人注意。這裡沒有假面,遮簾竿上也沒有藍標籤或紅標籤,沒有PRT制服人員保持秩序、告知員工說他們應該先照顧誰。
他們帶我到一片簾子遮起的區域,非常近似我曾經待過的地方。然而在這裡,我是泰勒,而不是掠翅。我沒被銬上手銬、粗暴對待或被揭露出我最沈痛的秘密。他們徹底檢查過我的身體,朝我雙眼照了光,問了我太多問題。乳膏被抹上佔我臉部四分之一面積的輕微燒傷,護士也從我皮膚底下挑出幾顆砂礫。那個過程很痛,但那在十級痛楚中只有二級吧。我之前面對過十級痛。
我無法視物的事實,開始緩慢在我身上生效。我的左眼比右眼嚴重,但雙眼都無法看到細節,只能看到污點。只有光與黑暗。我太習慣自己擁有不自然廣闊的周圍感知,但我已經有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感知被剝奪走了。
在醫療專業人士們離開時,一位年輕女性溜進拉上簾子的隔間裡。
「喂。」她說。「妳還活著?」
「莉莎?」
「是啊。」
「蜜蜂T。」
「螳螂R。妳眼瞎了。該死的,那樣很糟糕欸。」她說。
「是啊。」我嘆了一聲。「我爸呢?」
「他沒有事。我有去看他。他醒來說要找妳。他看起來不怎麼喜歡我了。」
「妳把我從他身邊拉走。他會怪罪妳,我猜是因為,那比怪罪我還要輕鬆吧。」
「我猜也是。」我將一隻蚊子放到她兩片肩胛骨之間,好讓我能追蹤她走近、彎腰將雙手擺到醫院床鋪扶手上的種種動作。她說話時,聲音低靜,只有我能聽見她。「我們可以給妳弄到一個醫療能力者之類的人。綁架奧哈拉那種人,讓攝政或戰慄使用她的能力。」
「奧哈拉不在這裡。她出城了。」
「那麼,我們會雇用有治癒能力的人。」
「正因為妳對奧哈拉做過的那種事,他們就不會想過來這裡啊。特別是在我們踢出選民、斷層線他們那樣的隊伍之後,關於我們統管這座城的消息八成已經流出去了。他們會跟人們說我們有多危險,說我們會使用攝政或戰慄的那種戰略。」
「我們還有其他選項啊。」
「我知道。我不擔心自己。讓我不解的是那件事啊。有好多人受傷或被殺。」
「從我看到和聽到的事情來說,很多人受傷,沒那麼多人被殺。但那現在並不重要。妳的優先次序是?」
我眨了眼。「我爸⋯⋯」
「他沒事。」
「我的地盤,火災呢?」
「是策略性散播,根本沒接近真正的基地。沒有人受傷,但我認為他燒掉了妳一棟工房,把火燒在高處,讓大家有機會逃脫。」
「其他人,戰慄⋯⋯」
「他們完全不在火災附近。我們很快就要跟他們會面了。」
「黛娜。」
「現在妳上正軌啦。我們要談談計畫。而蛇蜷⋯⋯」
「他還活著,對吧?」我問。
「哼嗯。」莉莎證實道。「對我們來說更好的事情,是他八成很高興。對他來說,所有事情都湊合在一起了,就如他所想要的那樣。也就是說現在,今天,是我們跟他談話的最佳時機,在他心情好的時候讓他解放小淘氣。來吧,起床了。」
我的腦袋暈轉,但那不是腦震盪的效果。在我做的所有事情、付出所有辛勞之後,我們就這樣靠近目標了?我接受莉莎的協助,爬下醫院床鋪,她手臂勾起我的手臂,領我離開。
「所以我們就直接問,然後希望他心情好到會答應我?」這也表示我要閉嘴不指責他,不說出他在辯論會上所做的事。
莉莎以比較普通的音量說:「他給我的感覺不像是那種會被情緒嚴重影響的人呢。他八成在好一段時間以前就已經決定自己要不要放棄那個女孩了。但我會說,我們應該要利用我們能利用的東西,那也包括,在好日子裡跟他商量。順便說,妳也要小心說話。這裡有路人。」
我點頭,但我沒有跟上時,她拉了下我的手臂。「我們可以在離開之前看看我爸嗎?」
「他們在我探頭看他的時候就要移走他了。我有看了下他的表單,看起來他們要給他排個MRI,確認到他在碎歌鳥襲擊之後的內傷近況。」
我皺起眉頭。
她繼續說:「我跟他說,假使妳可以轉診的話,我可能會帶妳到我爸的診所,那裡傷患量沒那麼高。而假使我確實帶走妳的話,那也表示妳的情況沒很糟。他不喜歡這樣,但他也同意了。假使妳想留下來,不是說我們不能留啦。像我說的,我們想現在跟老闆聯絡,或現在的之後兩小時再聯絡,都不會有區別。」
「但這還是有區別?有一點點差別?」
「我是這麼認為的。」
我回想自己早先的感覺,又一次留下我爸,可能會表示留下某種斷裂性終點。
不過,將那件事疊加上我為了救出黛娜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也不盡然是只為了黛娜才行動。我幾乎不認識她。不,我必須承認,這個動機是很自私。我想照料自己的罪咎感,只想著我的責任以及我一路走來時所犯的罪行——那就是我在當掠翅時,我所引發的恐怖、痛楚與憂傷。
我跟我爸一同生活的十五年半以來,與當掠翅的兩個月,在重要性上相抗衡。不過,我爸會在那裡。他一直都在,而他會離去的想法就只是我的模糊感受罷了。
那就像我們現在去找蛇蜷,會對他在解放黛娜的這件事上所造成影響,那種極模糊可能性呢。
「我爸會沒事吧?」我問。
「他很好啊。沒有深層問題或疼痛的跡象。」
「那就走吧。」
我們走出醫院。我可以聽見痛楚的呼喊。
「我們要為這件事承擔罪責嗎?」
「不。妳可別走上那條道路啊。我們不知道的他的計畫,也不可能知道,我們在任何層面上都沒與他共謀。」
「我有在那裡。我能挺身而出做某些事情的,而我卻沒有行動。」
「要做什麼呢?反擊嗎?幫忙監護者?」
「是啊。」
「不行。最好的情況是,妳可能讓他跌個跤。但那不值得妳出手的。注意腳下。有階梯。」
我在認出自己應該往下走的地點時,沒有碰上困難。階梯底側有蜘蛛,我也有把幾隻蒼蠅往前派到每個台階上,確認了落足點。
「這可好笑了。」莉莎放低聲音,低語:「我之前想建議妳多訓練。妳應該矇住眼,看看我們能不能強迫妳用超能力視物,讓妳的腦子變得能真正處理那些資訊。我猜妳進度比我更超前了。」
「這沒那麼好玩啊。」我說。我不喜歡想到,假使在下一個災難發生時我還是眼盲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到室外。」她說。我感到門打開時暖空氣流過我身旁。「車子就在這裡。這算城裡處於這種狀態的好處之一吧——很簡單就能找到停車位。」
她聽起來是如此愉悅、明朗。我完全沒有她的樂觀。
她讓我倆到車子那邊,幫我開了車門。「我們會路過妳的地方,讓妳拿假面服,之後再跟其他人會面。之後我們就會去找蛇蜷。」
「找他?他不在基地裡?」我拉高嗓音,好讓她在走道車子另一側、打開駕駛座的車門時能聽見我。
「他不在他的基地裡。目前來說,蛇蜷已經死透了。他保留著他的平民身分。和他見面、談話也就有點困難了。」
我頓一下。我考量過這個情況,計算了蛇蜷的整體目標。「他是基斯.格羅夫嗎?」
「不是。」莉莎說。「等下。」
車子啟動,在她撈著某個盒子時,發出了唰唰聲。
錄音從車子的音響系統中播放。莉莎發動引擎,到退出停車位。我則在聽著。
「今天,上百位布拉克頓灣居民參與的市鎮會議進行時被當地反派的恐怖攻擊所打斷,可能是場刺殺的行動,因著超能英雄製作的科技產品意外爆炸,釀成淒慘悲劇。
「這次事件是布拉克頓灣近日所面臨的無數其他悲劇之一,這座近期成為全國熱門話題的城市,使全美激辯是否要譴押全城,疏散剩餘居民、坦然接受失敗。當地的罪犯頭領掌握了一小群超能反派,試圖刺殺克里斯特納市長、市長候選人基斯.格羅夫與市長候選人卡琳.帕迪羅。然而,在當地英雄介入時,當地監護者成員『勝利小子』的故障儀器,最終於市議廳建築大廳裡爆炸。在傷亡人員數量仍未被證實的當下,我們能証實我們WCVN台的記者和攝影團隊都在那場爆炸中身亡。更多資訊將在之後公布。
「在場的最初報導宣稱,年輕英雄隊伍內部有位已知的間諜,進行了破壞行動。布拉克頓灣PRT、捍衛者或監護者團隊都沒有成員能對此評論,在內部資訊報導說愛蜜麗.皮戈特主任——本城PRT以及政府贊助的英雄團隊經理——正被迫放帶薪假,等候全盤調查。
「填補其職位的是湯瑪斯.卡爾維特指揮官。在PRT被問及這位新替任的人員時,他們將卡爾維特指揮官描述為,已光榮卸任的PRT戰地特務。他在過往幾年裡,將自己的專業作為紐約超亞人類事物的職業顧問,為PRT服務,之後他也作為PRT襲擊戰隊的戰場指揮官。PRT對卡爾維特處理布拉克頓灣超亞人類事務的艱鉅任務,有著滿足的信心⋯⋯」
錄音被切斷。是莉莎停止了錄音檔。
「湯瑪斯.卡爾維特。」我說。
#媘蜜 #泰勒 #泰勒她爸2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xa5u3jXl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