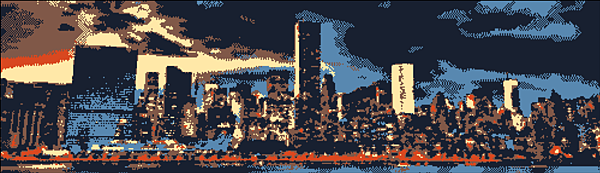 x
x
Disclaimer1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Cp1bKux9X
【原作者贊助連結】1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ZylD4OtXTl
「我是凱文.諾頓,我是全世界最強的人。」
凱文打個手勢,杜克便輕吠一聲。
「我拯救了幾十億人的性命。幾十億啊。」
另一道手勢,命令杜克再次小聲低吠、同意了他。
他端出馬克杯,但是周圍的路人直接繞離他、無視馬克杯。
在幾天前,凱文.諾頓的舊鞋鞋底脫落、使他露出腳趾,鞋尖也過度下沈、刮上卵石道路。他失足、近乎跌倒,杜克也跳開來,雙耳豎起而警戒。
凱文抓住一位路人來穩住自己,她幾乎推開他,臉上忽然深鏤著作嘔。
「抱歉了,小姐。」凱文在她加快腳步趕緊離去時,對她說。他拉高聲音,好讓她能聽完他說的話:「像我這樣的沒錢買鞋的人,是很可悲,不是嗎?」
凱文調整走姿、避免讓鞋子使自己失足時,他的步伐近乎踉蹌。這裡的道路很有古風,圓石路面在數年裡被上百人踏過。他周圍的區域則沒有那樣古舊。整修過的店面與新建築都不斷出現,模仿古老的大不列顛風格,但也保持著流行、煥然一新的建築面。
「杜克,我們沒辦法在一起了。」凱文說。「城市這裡的人施捨得這麼少,是不想讓乞丐待在這吧。但我只想去拜訪我的老巢,看看那裡變成什麼樣子了。」
他看到一家人走近,就端出馬克杯:「為全世界最強的人,給個幾便士?」
那些孩子盯著他,但那雙親避開了眼神——那位母親手繞過較小的孩子雙肩,好像要保護著他們。
凱文聳肩、繼續走著。馬克杯裡只有幾枚硬幣,在他揮動手臂時咯咯鋃鐺轉動。
「你不太記得這片區域吧。」他對杜克說:「我在找到你之前,已經搬出這裡了。是逃走的。我在你還小到可以放在我手掌上時,有經過幾次這裏,但我都特意避開這裡。我不會說我很想念這地方。老店老闆之前都會留給我一些剩菜剩飯。」
他指著:「之前在那裡,有一家烘焙坊。他們會丟出店裡擺超過一天的東西。丟出好幾袋麵包卷跟點心。還有香腸卷、油酥餅。當他們察覺到我會去拿食物、補充我貧乏的營養時,他們就開始把袋子放到垃圾箱一側,讓食物不會被糟蹋,他們也會留其他東西。都是些小東西。有些沙拉,好讓我能吃些綠菜。還有梳子、牙刷、肥皂、防臭劑。都是些溫柔的老鄉。」
凱文將手伸下去,抓抓杜克的頭。
「不知道那裡變成什麼樣子了。希望這裡的變化不會讓他們過得太差。假使他們被迫搬走,也沒獲得店面的價值的話,那就太不像話了。他們至少應該有些像樣的待遇吧。他們值得更好的。」
杜克打了個哈欠,哈欠音最終也成了細小的哀鳴。
「你是問,我嗎?」凱文說。「不。我不值得多少東西。那台詞是怎麼說的,能力跟責任?作為全世界最強的人,我就是有他媽的超多責任啊。確實,我會餓著肚子睡覺,體虱騷擾時我也睡不好,但真正會讓我睡不好的事情是,我可能逃避了自己的責任啊。」
凱文向下一看,與杜克的視線相接,杜克也疑惑地偏著頭。
「小子,我是被嚇壞了。因為我就是個懦夫。人們有三種方式能淪落到我這種人生。不是說世界上最強的人的事情。而變成我這樣,無處可去,在全世界裡連一個朋友也沒有。變成這樣的其中一個方法是缺乏支持。有關照你的家人、朋友,你就幾乎能撐過任何事情。沒人支援你?假使沒有人抓住你,就算是最細小的事情也會打趴你的。」
那裡傳來了一陣昏暗的隆隆聲響,之後大雨,便開始傾盆灌下。
「杜克,這是夏雨啊。也是時候了,不是嗎?」
街上有幾個人跑去躲雨;在一分鐘內,這小段人行道就近乎無人了。凱文伸展雙手,讓雨水濕浸自己。他將手指爬梳過頭髮、將頭髮推向後方,抬起頭面對天空。
杜克甩了幾秒鐘,將水濺到四處。讓凱文從自己的白日夢中驚醒。
「我剛在說什麼?喔,對了。變成我這種情況的第二種方法?是生病。有時候是腦袋有病,有些時候是身體的病,有些時候是用酒瓶或煙斗搞出的病。第三條道路則是我走過的路。懦弱。從人生裡逃跑。逃離自己。有些時候也會逃進酒瓶。還有,從你對自己所做的真相終逃開吧,我不知啊。多虧有你,我才能避開那種過錯。」
他感到一陣冷風,便走到嶄新修裝的大樓的屋簷下,找到了他在傾盆大雨下走路時的短暫庇護。
「我太固守自封、無法改變,沒辦法活得更勇敢。而回到這裡,就耗費我能湊齊的所有勇氣了呢。」
杜克強把自己的頭塞到凱文的手底下,凱文也忍不住微笑了。
「好小子,好小子。我很感激你的精神支持。」
他們得再次走到雨水下,穿過了街道。凱文加快腳步,杜克也大步走在他身旁。
他走到隔壁街區時,躲到另一個屋簷下。「杜克,我搞砸了。我知道自己搞砸得有多慘。我繼續活下去時也得承擔這件事。我做了很多事。我想,是比大部分人還要多。但那還是不夠啊。假使我的直覺是正確的,就根本不夠啊。該死的。」
就在街道遠處,有一家店門被打開,一位年輕女性走到室外。她個子嬌小,很漂亮,年齡二十幾歲,她剪得像小精靈的黑髮上有著一頂深灰色的貝雷帽。她穿了黑色緊身衣,短袖,還有灰色褶裙。很有時尚感。她轉向他那邊,一手拿了把雨傘。
他對她微笑,走入雨中,好讓他倆交會,也讓她不必走入雨中。
「先生?」她喊道。
他正要回到屋簷的避雨處。「什麼事?」
「這。」她說。她拿出自己的皮夾,交給他十磅紙鈔。他瞥了她一眼。
他收下紙鈔,說:「謝謝妳。」
「完全不用客氣喔。」
他古怪地看了她一眼。她正正直視他的雙眼。「我通常會遇到兩種人。有些人會給我錢,然後根本不看我第二眼。還有那些會看著我,肯定會教訓我說我該如何花錢的人。所以妳可以對我搖搖手說,我不該花錢買毒品、酒水或香菸。我也能理解的,而且我能讓自己非常妥當地,做出感到難為情的樣子。」
「你要怎麼花錢都行。」她說。她有一點法語口音:「你的情況也許困難到,那些東西或許能給你一點點安慰,就算那些東西對你來說,是很不好呢。」
「那麽說,確實很真實呢。放心,我會先餵飽杜克,才會餵飽自己,我之後也會買一點點給我自己的——像妳說的——安慰。我承認假使我能買的話,是會想抽根菸呢。」
「很高興你這麼說。」她微笑著,說。「哈囉杜克。」
「他是個好小子,但我不會建議妳摸他。」
她收回了手。
「他沒有跳蚤或之類的東西。我有確保他很健康。但他也是隻工作笨狗。在我需要時會守望著我。我們照顧彼此。所以他可能會想保護我,不怎麼希望有人太快、太靠近我。」
「是你給他命名的?」她問。在他點頭時,她問道:「選杜克是有理由?」
「我想得很久、很努力。杜克似乎滿相稱的。英國裡最高的爵位,正好在國王之下。這對服侍著全世界最強的人的狗來說,是很合適。」
他這麼說著時,正看著她的雙眼,看到她神情之中的悲傷。「全世界裡最強的人?」
「那是真的。別以為我沒發現。妳不相信我。」
「先生,那是個非常美好的說詞⋯⋯」
「凱文。凱文.諾頓。別在意我的胡言漫談。」
「莉絲忒。」她說,伸出了手。
他握了她的手。就算有那傾盆大雨的濕度,她的手仍很溫暖。
「你還好嗎?」她問。
「嗯?」他抬起頭、抽回手。
「你臉上有個神情。」
「只是在納悶著我上次接觸到另一個人,是什麼時候的事。也許是幾年前吧。在我離開一個牧師的避難所的時候,他有給我一個擁抱。」
「凱文,那聽起來很寂寞呢。好幾年沒跟人接觸?」
「沒那麼寂寞。我還有個朋友。」他說,抓了抓杜克的頭。
莉絲忒點頭。
「但妳應該沒忘記。那些小事。就連地震?那也是特別的事。是很有意義的。就算妳每天都會碰到地震,也要重視其價值。」
「我會記住的。」她微笑。
「我說不清我有多感激。」凱文說。「這樣為我花了時間,這對我來說很是重要的。也許就是我需要的推力了。」
「你為什麼需要推力?」
「我回想起來,是很久都沒有好好回顧了。可以說是我正在拜訪家鄉。思考著自己過去十二年來,就連對杜克都不曾說過的事。妳給了我我所需的打氣。謝謝妳。」
「很高興我能幫上忙。我希望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天啊,這個擔子真重。我⋯⋯我不認為妳還有一點點時間?妳願意與我散步一下嗎?」
她瞥向身後,看向她剛走去的方向:「我的火車⋯⋯」
「假使妳不想來的話,我也會理解的。但假使妳稍微縱容下我這個老人,這就會讓我今天,全然不同了。幾分鐘就好。」
「你沒那麼老。」她頓了下。「我想我是可以留幾分鐘。」
「那麼,來吧,那裡並不遠。妳可能會想撐傘的。」
她半信半疑地瞥了他一眼。
他搖搖頭:「不用。我沒期待妳跟我打傘。我最近都沒怎麼洗衣服。不會想讓妳困擾的。而且杜克也可能會嫉妒妳呢。」
她點了頭,跟在他身旁,一同走向他前去的方向。他沒忽略她仍離他很遠、待在幾步之外,她只跟在後方,正巧足夠盯住他,就好像他做任何事情時就預備好能逃跑。她也許是個好人,但她也不傻。
「我最初出發的時候,是在二十出頭。」他說。「我生在倫敦,雙親在我還是青少年的時候就去世,我就沒有親人了。我從這裡搬到約克。遇到了個女孩,搬進她的公寓。我說沒法說我的處境是不是那樣造成的,我也願意接受自己的的過錯。但那就是我走下這條路的起點。」
「是發生什麼事呢?」
「有太多錯誤被搞到一起。一來,她不是正確的女孩。我們的關係是有進展,而我也察覺自己不喜歡女人。」
「喔。」莉絲忒說。
「那是有點晚了,但我一直以來都在做著我以為自己該做的事,跟女孩子約會就是那其中一件事。我讓妳不舒服嗎?讓妳覺得太無聊了?」
「不。不會那樣的。」
「嗯,我那時很年輕,是個愚蠢的二十歲男孩,我搬進去的時候,也沒把名字放到租契上,也沒有錢可以搬出去。她察覺到我們沒再約會,就威脅要把我踢出去,我也懇求她讓我留下來。我沒地方可去。想說假使我留下來處理那股怒氣的話,就能存夠多錢、找個地方住。她卻開始揍我。我從來都不是會回手的那種人。情況就愈變愈糟了。」
「我很抱歉。」
「就我所知,有家暴女性中心,但沒有男性的避難處。人們不知怎的,都沒想像到女人也能打男人。」
「你就離開了?」
「我很長的時間裡都一直在納悶著自己是否有做出正確的決定。」凱文說。「然後我們就到這了。」
道路到了盡頭,他們走到了一條流入烏茲河的細流。一座小型、古雅的橋越過水流,使圓石走道延展到對岸,長凳坐立在石製露台上,有年幼的樹木被種在緊鄰石圈的土壤中。
「這裡就是你還沒回去的家?」莉絲忒問。
「是最接近我的家的地方了。」凱文走出雨傘、走入雨水下方,也走近了那座橋:「他們修裝了這地方。我之前曾經睡在這底下。這裡也是我離開那女孩的公寓時所到的地方。」
「你從那時起就一直住在街上了?」
「有些時候會留在避難所——是在天氣太冷的時候,還有他們也願意接受杜克的時候。只要我一進去,我就得做出某些妥協。說回來,謝謝妳,謝謝妳過來。我知道妳錯過了火車。就算我身旁有杜克,我仍不知道自己夠不夠勇敢到,可以撐到這裡來。我停停頓頓的次數多到我都數不清了。我真的很感謝妳。」
她古怪地看了我一眼。「沒事的。你慢慢來。」
凱文點頭:「妳可以牽著杜克嗎?一分鐘就好。」
她接過他遞出的狗鍊,那條繩子被小心地綁在杜克肩膀的套具上。狗鍊幾乎沒必要存在。杜克從來都不會拉扯狗鍊。
凱文走近那座橋,手指劃過那構成石橋的圓滑石頭,而那被雨水沖刷的石像鬼的臉坐立在橋墩底部上。雨水流過石像臉面,也流下他的衣服,濕透了他的身體。這似乎也很應景。
考量到雨水浸濕了自己,這麽做就沒多少意義了,但他仍跪在水邊,來到河水跟大雨前後沖刷的岸邊,洗著他的手。他深呼吸一口氣,吸入他所熟悉的河水薄弱氣味。自然的味道。
記憶湧回,有如浪潮。
凱文將頭髮推開臉上,手舀起水,將水潑到臉上。
他站了起來,接著停頓、僵止了。
嘆息聲溜過他唇間,被大雨的噪音所淹沒。
在最靠近此處的露台跟樹木間,那個金色的男人正離地面只有幾寸,漂浮著,於昏暗的雨氣中散發著冷光。落雨也反射了那金光、閃爍著,在河中映照出毛骨悚然的倒影,那倒影的河水也流到了滑石與滑石之間。
凱文將雙手放到口袋裡、溫暖起自己,也瞥向莉絲忒跟杜克。杜克沒有移動一絲一毫,但他雙耳平貼頭部。莉絲忒雙手遮著嘴巴,雙眼瞪大。那把雨傘落到了地上,全然被遺忘了。
凱文細細觀察著那個男人。金色的男人外表不像任何年齡,也沒有絲毫轉變。他的頭髮依然那樣長,短蓄鬍子也與過去一模一樣。他每個部位都有著磨亮的金色,就連他雙眼也是金色。他沒有呼吸,凝視時也沒有眨眼。
雨水流下了那金色男人的身體,但他沒有被打濕。在雨水打下來時,他的頭髮幾乎沒有移動,他的假面服也吸收了濕潤,但也同樣迅速地變乾。雨水單純溜過他的皮膚跟頭髮,使他不被雨水碰觸。
一件延伸到他的二頭肌與腳趾的簡單白色緊身衣,也受到那股效力影響,使他那件假面服被保持乾淨。那件衣服被日光之下的所有東西弄髒了無數次,但那股金色光輝男人也推開了微粒——就像他身體排開了水流——緩緩而確實地清潔掉髒污。那件緊身衣現在,可能算是他的身體一部分了。
「哈囉老友。」凱文說。
唯一的應答是傾盆大雨。那個金色男人沒有說話。
「我也在納悶我會不會在這裡看到你。」凱文繼續說。「好一陣子了。我幾乎說服自己說,你是我的想像。那裡那隻老狗,他在我離開的時候根本還沒出生,而現在他都站不穩了。都十二年老了。」
那個金色男人僅是凝視。
凱文轉身離開那位超能英雄。他輕快地走著拿起莉絲忒的雨傘,撿起了之後也甩掉雨傘裝盛的雨水。他將雨傘交給了她。
「賽陽。」她低語著。
「不。」凱文說。「那從來都不是他的名字。」
「我不懂。」
「來更靠近一點。」
她猶豫了一下,但也走近,直到她離那個黃金男人只有一小段距離。他那雙毫無瞳孔的眼睛從未離開凱文。
「我說過我是全世界最強的人。我沒在扯謊。」凱文說。「瞧?」
金色男人沒有反應。
「你在控制他?」莉絲忒問。
「不。真的不算是控制。是的。但不是妳想的那樣。」
「我不懂。」
「之前的時間裡,這個金人把他的時間用來思考,飄到這裡、飄到那裡,觀察著,但從不做任何事。他一直在茫然中。跟他誕生時一樣裸著身。所有人對他是誰,都有不同想法。有些人認為他可能是個天使,其他人以為他是墮落天使,還有更多人在思考科學性的解釋。他們唯一都同意的事情就是,他看起來很悲傷。」
「他看起來是很悲傷。」莉絲忒也在凝視著,但那個金色男人只看著凱文。
「他不是那些東西。」凱文說。「我不信啊。他看起來不像有任何感情。他那個表情從來沒改變。可是不管那底下是什麼,是那個東西讓妳有那種感覺。他看起來很悲傷,是因為他是很悲傷。然而妳卻不會考慮『眼神』的部分了。」
「這不合理啊。」
「他可是能他媽的飛行啊!還會跟一隻能打碎大陸的蜥蜴,用金色的雷射光束戰鬥!他的事情根本不合任何理啊!」
金人將雙眼轉離那兩人,檢視著最近種植的樹木。他的雙眼正注視一片葉子。
「他在做什麼?」
「我正要說到這件事。那純粹是巧合,但他之前在夜半正中,停在這裡某個地方。那時碰巧是我依然對這種生活方式還是新手的時候,我仍對自己感到遺憾,我無法跟任何人對視。我就看到他,察覺到他就是那個我從新聞上聽過的金人。我當時意志非常消沈,就跑去用我雙手狂揍他的胸膛,對他吼著、罵著,用各式各樣的名字罵他。」
「為什麼?」
「因為他竟敢比我還更悲慘。或是因為人們把這些希望放在他身上,而他就只去一個碰巧沒有人能飛行的世界裡遊蕩,然後連他媽的一件事,都不幹。我不知道啊。我大都是在對自己吼。我說了不要這麼悲慘、不要這樣浪費自己,那種話,也許要他去幫忙做慈善廚房幫忙之類的,他就可能對自己感覺更好了吧。」
「慈善廚房?」
「我沒真的以為他會去做慈善廚房。我最後是有去慈善廚房,但那不是重點。我是叫他去做些事情、去幫助人。然後他就去幫了。從那時起,他就有行動。」
「就這樣?」
「妳看看他。那什麼感情都沒有。不管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不管是什麼事情讓他變成這樣子,都已經打壞了他這個人。打爛他的心智。那可能就是他這樣遊蕩的原因。他在尋找答案,試著搞清楚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金人繼續盯著那片葉子。
「他不會感覺被冒犯嗎?」莉絲忒問。「你這樣談論他,就像他不存在?」
「他理解的。他也有在聽我們說話。但我從來沒聽過他說話。在我說話時,也幾乎從來沒讓他看向我。他不會展現情感的,或許,他不懂情感是什麼。」
「那幾乎就像自閉症呢。」莉絲忒問。
「怎麼像自閉症?」凱文問。
「連結感太強。」莉絲忒說。「接收了太多刺激,所有東西都被淹過去。」
「強化聽力,可以同時聽見整座城市?」
「也許吧。或許他有感知到我們無法感知的東西。」她說。「世界上最強的人,而我現在看著他,就覺得他像個小孩子。」
「是啊,除非有事情轉變。」凱文說:「他唯一聽從的人就是我。之前在我一人待著時,他就會過來,都是在天氣很差,或是深夜時過來,而不論他怎麼來的,都不會有人會跟他到這裡。」
「我聽說,他們沒辦法用攝影機或衛星追蹤他。得要仰賴人眼跟全球的資訊系統才能追蹤他。」
「喔。也許就是那樣吧。」凱文說。「妳有待在這,我就很驚訝他會出現。我以為⋯⋯我幾乎以為他不會出現,因為我讓妳跟來了。這讓我感覺更好了一點。」
「為什麼呢?為什麼要避開他?」
凱文沒將雙眼移開那個金人身上。「他讓我很害怕啊。他是在所有人之中,選擇聽從我。就因為這樣,我就成了全世界最強的人。因為我可以叫全世界最強、最有能力的人去做某些事情。」
「然後你就逃跑了?」
「我花好一陣子才理解自己推動的事情。我開始聽說他的事。街上也有在傳,報紙、廣播也有報。金人拯救了小島災難。金人插手了迅速激化的戰爭,但直到那個該死的短片開始在新聞台播放以前,我都沒察覺到自己攪和的事。」
「我不懂。」
「他是個常客,對吧?他會順道拜訪這裡,就像在確認我有沒有其他要說的話。也許我會告訴他,把人從車禍裡救出來時要更溫柔一點,或是在那隻帶角的混帳下一次爬出地表時,那個金人卻飛過牠然後來拜訪我,我就告訴他,下一次他需要出手幫忙,去跟那隻怪物和類似的東西戰鬥。但有些時候我也沒任何話想說,也不是說他會遵守我的每道指令的所有細節,所以有些時候,他就在天殺的早上五點後,就待在這裡,而我也沒辦法甩掉他,我就只是繼續說話。」
「說話?」
「說起任何東西。像說起我入手的書。像時事。陌生人的好意。或是我會給他弄些衣服,讓他看起來更像樣一點,然後就聊起衣服的事。」
他沈默下來,看著那位金人。
「發生什麼事了?」
「他從來都沒回應我,在我張嘴隨便閒聊時,也幾乎不會注意到我。但他有在遵守著我給他的概略指令。幫助人,做更多這種事,做少一點那種事。但我在跟他談到我的童年,談到家的時候,他就會抓到了某些東西。他會轉過頭,跟我眼神接觸。那嚇壞了我。我一再重想了一次,但那時候,是早上該死的五點鐘,我也不怎麼完全記得自己說了什麼東西。那是說,我在三天前都想不到我說了什麼,我就碰巧在正確的時間跟地點,看了一家店裡的電視在播放那個,一直出現在新聞上的短片。是金人最初——也是最後一次——說了話。每個人似乎都以為他是說賽陽,然後他們就這樣決定了他的名字。他們搞錯了,但那個詞依然留了下來,那個辭彙出現在T恤上、在音樂裡頭,我住的這裡的人們也談到了那個詞彙。就因為我在某些胡言亂語時談到的一個東西,整個世界就轉變了。」
「這件事讓你很害怕?」
「那是敲響了我的警鐘。很蠢吧,不是嗎?這事情也太瑣碎了。」
「不。談到他的時候,不會事情很瑣碎的。」
金人將雙眼轉向河流,背對著他們。
「假使那個詞彙不是賽陽,你是談到什麼呢?」莉絲忒問。
「我只在之後才察覺。我是在談論家、宗教跟家人。談到我童年的記憶。我現在,也沒記得很清楚。但他有注意到的詞彙是錫安。」
「那是希伯來文,不是嗎?」
凱文點頭。「我不知道。不曉得那個語言,那是談到我的表親在我們還是十三歲時,跟闖禍有關的事。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在意這個詞彙。但他還是在意了,而就在同時,那個短片就開始播放,他們在談他做的事。還有他到現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強的人。這太嚇人了——所有力量都在我的指揮之下,聽我命令去留。就因為一個我這樣骯髒、什麼都幹不了的魯蛇,用一個詞彙就改變了世界。」
「你不是個魯蛇啊。你有叫他去幫助人。」
凱文面色陰森地點頭。
他的表情改變了。
「你也沒要改變那一點,不是嗎?」
他搖了頭。「金人!」
那個漂浮在附近的金人,正面面對他。
「我搞砸了,等這麼久才來跟你說話。但我現在在這裡,就有兩件我們得討論的事。」
沒有回應。只有毫無動靜的凝望。
「這很難辦,因為我在這裡,真的很希望我是想錯了。假使這樣能行的話,那就表示我的愚蠢跟懦弱不會讓人們有太多損失。也表示我也可以在更早先時就已經修正這件事。我上一次過來差不多是春天的事,我之後才有機會用最新潮的網際網路。我花了點時間才學會網路,但我也能讀你的事情。看到你在戰鬥的影片⋯⋯」
「凱文?」莉絲忒問。
「那些終結召喚者混帳。我告訴你說,你需要阻止他們,說你需要戰鬥、保護人們。而你也有戰鬥。」
他握緊雙手,向下盯著地面:「而老天幫助我啊,我也許沒說得夠精確。也許我沒察覺到你會怎麼詮釋我的字面意思。我們需要你殺掉那些東西。摧毀掉他們的最後一抹殘渣,將它們扔到太空裡。我不知道。但為了殺害而戰鬥,就別⋯⋯老天,我希望我搞錯了,也能想起自己全然搞錯的詞彙,然後你也不會聽我的建議,只為了戰鬥而戰鬥,或是為了阻止他們而戰鬥,而不是永久性地阻止他們。你理解嗎?別只阻止他們的行動。要永久阻止他們啊。」
那個金人漂浮在原處,讓他看起來依然像被時間凍結、站立於空中。
「我老天啊,金人,我祈禱你會理解我。我因為自己很害怕,我花了一年才有勇氣,之後我就⋯⋯我就拯救了無數的人,而同時,那些人所殺害的每一個人的鮮血,就都沾到我手上了。」
「凱文。」莉絲忒說,嗓音沈靜。她雙手放到他肩膀上。
他無視了她:「另一個重要話題?我沒有時間了。我年紀中邁,我的肝也完蛋。我從來都沒怎麼常喝酒,因為我得餵飽那隻狗。除了抽菸,我也從沒有嗑過任何藥。但不知怎的,我還是得了肝炎。有天晚上,幾個孩子決定要跟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打架,我反擊後,被送進一家醫院,輸了壞掉的血液或是其他有感染的血液。金人,我那樣撞見你,讓你停下來聽我說話?那是幾千萬分之一的巧合吧。而有這個疾病,恐怕也是另一個千萬分之一的巧合。遇到你是我人生中最棒,也是最可怕的的事——那也許就跟這個疾病一樣,是塞翁失馬。除開這位年輕女士的幫助,那也許就是唯一的理由,可以解釋我為何能有膽子回來這裡。」
雨水不像之前那樣激烈、沈重了。雨聲落水,在石頭與水流上有著明顯轉變。
凱文嘆氣。「我來這裡是要安排好我的後事,而你是在杜克之外最重要的東西。我想要你繼續做著你在做的事。去幫助人。試著跟好人們溝通更頻繁一點——我之前有叫你去溝通,你卻沒聽我的,但你真的應該溝通啊。而假使有問題的話,假使你需要有人可以傾聽、有人偶爾可以讓你拜訪的話,就來找這位年輕女士。莉絲忒。因為她是個好人。她是比我更好的人。她比我勇敢。假使她會停下來跟我這個狗娘養的流浪漢說話,還跟著流浪漢走到其他地方,肯定是比我勇敢了。」
「不要。」莉絲忒說:「我辦不到的。」
「我這樣做是很骯髒。」凱文說,轉頭看向她。「把這個重擔推給妳。但我不知怎地感覺,讓他聽從妳,會比去聽從那些穿著西裝的人,或捍衛者,或鮮紅護手【原文Red Gauntlet】,或任何其他人都還要好。妳就想想吧,搞清楚妳需要搞清楚的事,然後決定妳需要跟他說什麼話。」
「你認為他會聽我的話嗎?他會跟著我?」莉絲忒問,雙眼瞪大。
「我不知道,但我認為他可能會聽妳的。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選擇聽從我啊,但他還是有聽我的。我可能讓他想起他之前認識的某個人。或者他純粹是直接認定我們是朋友。運氣好的話,他也能把妳當成朋友。」凱文嘆息:「你倆懂了嗎?你們現在就是搭擋了。」
莉絲忒沒能開口說話。那個金人也沒有回應,根本沒瞥向莉絲忒。
金人在漫長、沈默的數秒內,漂浮在空中,便比肉眼能見地,要更迅速。只有一抹金色光跡留在他身後,並迅速褪去。
在短短數秒裡,賽陽就離開了。
「我們得要告訴其他人吧。」莉絲忒說。
「妳可以去試。他們會以看我的方式看著妳。就像妳發瘋了一樣。」
「但、但是⋯⋯」
「是啊。」凱文說。「不怎麼簡單,是吧?假若妳很幸運的話,他就會在其他人待在附近時出現,然後他們才會在妳談到這件事情時願意相信妳。」
他嘆了口氣。「來吧,杜克。」
莉絲忒在他抓走杜克的狗鍊時,並沒有抗拒他的手。凱文就要離去了。
「我不懂啊!」莉絲忒在他身後喊著。
凱文沒轉身或停下來,他也拉高嗓音來回應,壓過傾盆大雨。「這樣很划算吧,不是嗎?十磅就能成為全世界最強的人啊。」
#賽陽1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gPEOnvAk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