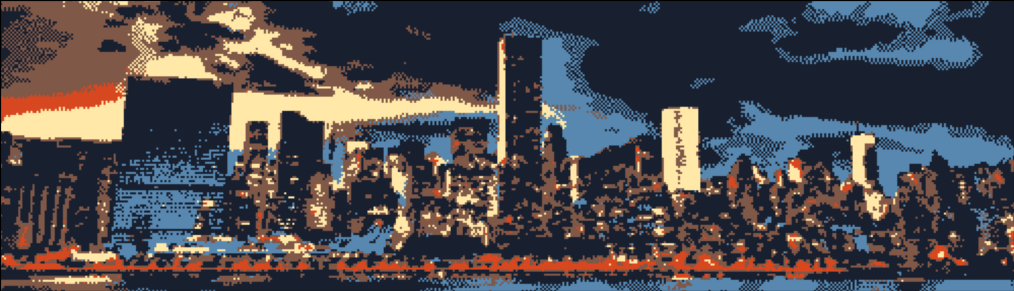 x
x
從屋頂跳到另一個屋頂,不像電視或電影裡那樣厲害或有效率。就算是狗在跳、是牠們在費力,牠們也不是最優雅的生物,狗的身體不適合被騎,而且我們也沒有任何馬鞍。這些大樓高度也劇烈地不同產生了問題,就像布萊恩的街坊鄰區有老舊的維多利亞風格建築在公寓和通天厝之間突出一樣。當猶大從六層樓大樓側邊跳下,將他的爪子嵌入旁邊大樓牆壁緩衝下落力道,直接跳過整條小巷的瀝青,著地力道真心讓我擔憂自己臀部會脫臼。
長話短說:我很感激能回到大地表面上。
「需要幫忙!」母狗在布魯圖斯趴了下來後喊了出聲。她讓媘蜜俯趴在她大腿和布魯圖斯的雙肩間,儘管看來母狗盡力抓住她,媘蜜仍快掉了下來。
我不情願地放開戰慄,他也滑下猶大的背脊,匆忙跑過去幫忙。我沈默地為裝甲板覆蓋了自己的胸口和肚子感到遺憾,因為我從佛斯伯格畫廊撤退、緊貼在他身上時成為了個堅固屏障。
不管我怎樣後悔,我並沒有健忘掉手上的事。我跳下猶大的背脊,正好在戰慄後面一步,趕緊跑過去幫忙媘蜜。我們發現把她側邊滑下來比把她弄回布魯圖斯背脊上,還要簡單。戰慄負責舉起重量,而我則專注在別讓她的頭和雙手落在地上或被壓在她身體下。我彎下腰幫忙把她慢慢放到地上時,我已經能感到大腿、背脊和肚子的肌肉開始僵硬。我很高興自己先前早晨運動,因為我明天不可能到任何其他地方了。
我瞥了眼我們周圍。車子呼嘯穿過兩邊的街道,可是路上沒有行人,而且目前看來也沒有人發現我們。我懷疑,大部分在鬧市區的人已經出去到,差不多羅德街周圍,慶祝宵禁的結束。大家都會表現出他們對ABB局勢終結的放鬆感,補償他們這六天晚上宵禁以來,被拘禁在自家的時間。
「有任何人看到假面追來嗎?」戰慄問。
「我沒看見任何人,可是我也沒認真看。這通常是媘蜜的工作。」攝政回答。
「她這樣給不了我們任何情報。」戰慄指出。
「等等。」我告訴他。我伸手進實用裝甲隔間裡,撈出零錢包。我移出自己塞進去,讓零錢不格格亂響的衛生紙,在錢包底部找到三個小白色包的其中一個。我撕開包裝,把它拿近媘蜜的鼻子。
「嗅鹽?」戰慄問。
我點了頭:「你在我們放倒上人和黑客文時,有問有沒有人帶。我在腦中筆記下來,要在下次時帶出來。」
「我賭我們一半都有記。」攝政回答:「詭異的是妳真照做了,呆瓜。」
「這有什麼詭異的?」我問,有一點防護心。
他轉移了注意力沒回答。媘蜜被擾動,轉頭把鼻子從嗅鹽扭開。我把嗅鹽又遞回到她鼻子下。
她醒了,咕噥道:「好啦,停下。」
「歡迎回來。」戰慄對她說。
「妳感覺怎麼樣?」我問。
「我感覺像有人把攪拌器塞進我的肚子裡,而且我手痛到爆炸,但我比外表看起來還要強壯。」她說。她不到一秒後,呻吟,呼出一口氣:「可是我需要有人幫忙我站起來。」
戰慄和我幫了她一把。她看起來很痛苦,移動有如冰川般緩慢。她明顯不想要我們倆碰觸她的右手,讓這整件事變得更加困難。
「我錯過了什麼?」她問,就像把她如同老女人似地移動的事上轉移開。
「踢哩滴啊,妳被甩了一巴掌然後被揍暈,是靠母狗和掠翅,還有我們才能溜出來。」攝政聳了聳肩。
媘蜜腳步凍結。因為戰慄和我仍把她扶成站姿,我被強迫轉變的手姿,確保她沒倒下。
「該死。」她成功將一個詞咒罵得比,和我爸一起工作的人的十字髒話還更惡毒,而且他們有些人還是水手。媘蜜轉頭:「那不是……」
「不是真的。」兵器大師說道,他回應她的言詞時,繞出了小巷子一端。
他看起來比疲倦還要糟糕。他臉下半部有著被毆打的痕跡,那並不多,但確實有一些。我有指示黃蜂要叮到不要纏住下腹部的程度,也就是說它們沒將毒液袋擠乾<然後在每次叮咬時把毒液注射進去。我只注射足夠的毒液到讓傷口有一點點痛,達到干擾效果。不過,在我筋疲力竭撤退後,我知道有幾隻會留在他身上,而且有幾隻在我離開範圍、不再能操縱那些黃蜂之後,會螫上他。然而,那傷痕不是糟糕的部分。然而,那抓住我眼睛的,是六條血絲流下他下半張臉。就算它們咬起來會痛,大黃蜂的咬噬不盡能刺穿皮膚,可是他身上曾有很多隻,而如果有幾隻咬上同個位置,或是如果它們夠到了眼皮或鼻孔的邊緣?也許會受傷吧。我注意到他右手中的戰戟。
當我看向剩下的逃跑路線時,無畏就在小巷的另一端。布拉克頓灣的新星。把他定為巧匠會很簡單,但他顯然不是巧匠。無畏的能力讓他--根據在他於電視上和雜誌訪談裡透露出的細節--他天用一點點能力浸染裝備。事情是,他每天包裹進去的能力都有永久效果。每天,他就比剛過的前一天更強一點點。更多才多藝一點點。眾皆期待,他最終甚至將超越雅麗珊卓、傳奇【原文Legend】和昹奪羅【原文Eidolon,昹音矮】--捍衛者的「三巨頭」--那些頂尖菁英們。這有點讓他在布拉克頓灣中變成一個大人物,一個家鄉英雄。
我沒在追這些消息,也不相信那些英雄崇拜。我總是認為假面很有趣,我會追不是緋聞的新聞,可是除了在我五歲左右時,我有一件雅麗珊卓T恤,我媽還幫我在網路上找到她的照片,我從沒為任何特定的英雄迷到昏頭。
無畏身體捆上了幾個標誌性裝備。他有一把電弧長槍,那是他單手端著的一把矛,看起來就像由白色閃電構成。他的盾牌被固定在他左手前臂的,是片晚餐餐盤大小的金屬圓盤,被一圈圈構成長槍的同樣能量環繞。他雙腳看起來像被裝進爆裂的白色能量。假使謠傳可以被相信,他也在努力強化他的裝甲,可是我不能從那假面裝看出任何那些能量的跡象。它有白色和金色,而他的金頭盔是像以希臘或斯巴達風覆蓋了他的鼻子,有為雙眼開的縫隙,也有一圈金屬蓋住他的鼻子,還有一條縫隙正在他臉的下半部。一個金屬裝飾在他頭頂上,就像個莫霍克族。
兵器大師專注在我身上時,你能看到他受傷的臉皺起的雙眉。
「我把你的戰戟丟到畫廊旁邊了。」我在他能說話前說。「無畏幫你拿來了?」
他沒有立刻說出回應。就好像要展示般,把他的戰戟直直進空中。當它達到上升過程的最頂端時,消失成一陣螢光藍線團,同時在他手裡重新實體化。我不是看過勝利小子用同樣的方式,把砲台帶進搶銀行的地點嗎?那是個借來的技術?
「我不會把這麼多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又不加上足夠的防衛措施。」兵器大師對我說。他的嗓音緊緊壓抑著憤怒。
沒蟲子。該死,我又沒蟲子了。當我攻擊兵器大師時把自己裝甲的蟲子全用光,而我又把它們和剩下的蟲群,在我撤退時留在畫廊裡。
「投降。」他吟誦道。
「你就想像吧。」媘蜜說。
「快點決定。」兵器大師咆哮。
「你們為什麼停在這邊。」媘蜜對我們喃喃低語:「我們,有,距離藏起車子的停車場一個半街區欸。」
「我想在我們脫衣服前確認沒有人追擊。」戰慄回答:「確認,也很好。」
「對啊。」攝政的嗓音濃濃含著諷刺:「就是因為這種事情所以,比起被他們發現我們鑰匙已經插進車子發動孔還要好太多啦。」
「大家。」我打斷它們,我雙眼不離開兵器大師地低語道:「答案。方案。」
「去停車場。」媘蜜對我們說。
「我們的情況不會改善。」戰慄反駁。
「去停車場。」她咬緊牙根絲絲聲說,兵器大師向前踏出一步。
小巷寬得足以讓兩隻狗肩並肩站,我看到母狗在戰慄把兵器大師和狗兒們之外所有事物覆蓋上黑暗前,指示那兩隻野獸站到我們和兵器大師之間。
那黑暗沒偉維持超過三秒鐘。戰慄有足夠時間將他的手臂抵住我鎖骨,把我推上牆壁,他接著把我們周圍的黑暗移除。空氣裡有燃燒的臭氧味。無畏用上了他的矛?
無畏周遭沒多少黑暗環繞的事,大家立刻便清楚理解。他高舉盾牌,盾牌形成一個泡泡形狀的力場,延展到他周圍半徑十呎,碰觸我們兩邊的牆。力場怎樣阻擋黑暗,我不怎麼確定,我懷疑那力場實際上吃掉了它所碰觸到的任何黑暗。它不斷發出嘶嘶、破裂聲響,淹沒我們周圍道路的交通雜音。
無畏向前踏步,力場也跟著縮減我們的距離。
距離無畏又一秒更近後,戰慄必須撤退,避免接觸到白色能量的破裂力場。又一步,讓我們與兵器大師更近。
「兵器大師恨透你了。」媘蜜對無畏說,把她的聲音拉高蓋過力場產生的爆裂聲:「他恨你是下個明星--那個會變得比他更強的傢伙。你不費吹灰之力就走上捍衛者裡面的大人物道路,而他才是那個必須熬夜、重改東西、編輯模擬資料、想出新點子、花費數小時又數小時在體育管理訓練的人。他每投入一秒鐘,他對你的仇恨就愈多。你為什麼認為自己是那一位被他派出去巡邏城市和看護監護者們的隊員,而不是由你參加那場派對呢?」
無畏搖了搖頭。他舉起拿著矛的手,輕輕用一隻手指敲了他的頭盔一側。
「耳機。」媘蜜嘆息:「兵器大師告訴他要帶耳機,所以無畏不能聽見他之外的任何人。這同時十分聰明,也鬱悶到讓人難以置信。」
無畏迅速地,前進兩步,我們所有人--除了母狗和安潔力卡之外--都處於必須趕緊撤退的位置。攝政太慢,他的手碰觸到那個泡泡。短暫一陣能量弧從力場竄上攝政拉回來的手上。
「幹!喔!」攝政倒抽了一口氣。「別在搞那屁小啦!」
攝政抬起另一隻手,無畏就絆了一跤。攝政接著將他的手拂過一旁,無畏便跌倒。當無畏用兩隻手在跌倒時撐住,那個力場被放了下來。
「走!」戰慄吼道,把黑暗除滅。母狗用力地吹了兩聲口哨,那兩隻正與兵器大師戰鬥的狗趕緊跟了上來。
無畏舉起他的矛阻擋我們。戰慄在我們撤退隊伍最前端,跳過不斷爆裂著的閃電光束,然後落地時將雙腳踩在無畏的頭盔上。那個英雄沒在我們跑過去與他擦身而過之前恢復。
我們從小巷跑了出來。兩隻狗沖倒我們前方,跑到駛來的車流中,好讓我們可以安全過街。我們移動時有幾輛車尖聲煞住。
無畏開火時,我們正好通過停車場的入口,他不下三次用電弧長槍打中布魯圖斯三次,接著將注意力轉向安潔力卡。那個武器能伸長到他所需要的長度,延伸的速度快到眼睛都追不上。白火花在它打進那些野獸時紛飛,但效果幾乎最多只有輕傷。電弧長槍介於某種固體和能量之間,綜合兩者的特色。那長槍靠電擊加成,它的打擊力已經可以足夠強了,我是猜把它用在那些狗兒們身上,大概不會與手持電擊棒電大象,有什麼區別。他們太大、太壯了。
得知自己對那些動物們沒有多少效果,無畏瞄準了我們。
攝政干擾了無畏的準頭,電弧長槍扯裂停車場上方的建築窗戶,玻璃碎片如雨落在我們身上而我們就如此穿過大門,進入停車場。
兵器大師走出巷子,發現我們。他意圖縮短距離,射出抓升鉤抓住懸於停車場門之上的「若車高高於此請勿進入」橫杠。抓鉤繞過橫杠那一秒,兵器大師便開始將自己捲過去,他的金屬靴滑過整片屋頂。
母狗奮力吹了兩聲口哨,指向那橫杠。猶大撲了過去,用他下顎咬住橫杠和抓鉤。吊著橫杠的鐵鍊在猶大一扯下斷裂開,兵器大師的滑行在猶大往後拉他們之間的鐵鍊時便被打斷。
兵器大師換姿勢跑了起來,在他的動向轉變時成功保住跑姿。他伸出握住桿子的手,我便看見猶大嘴中飛出一團血沫,那隻狗反作用以後腳站起。猶大放開那根橫杠和鉤子,後退幾步,仍低吼著。鉤子退回去時,我看到它已不處於抓升鉤的型態,而是通常的戰戟脊刃、矛頭,而且沾的血還不少。
兵器大師維持著他的動量,把鐵鍊捲回去,再次將刃球甩出手時他的武器又回到了連枷風格。他把猶大按倒,接著廣範地揮動連枷,讓另外兩隻狗保持距離不再靠近。無畏繼續走近,正好在兵器大師後方側邊停下來。
「我的地圖程式說有三條路能走出這個停車場。」兵器大師告知我們:「另外兩個出口的門被鎖住了,我也可以保證你們不會有時間,在我趕上你們之前撬開門鎖或打壞門。別再耍小手段,別再……」
他在話說到一半時停下來,把他頭甩向一側,然後面向其他人。「什……」
接著他消失了。
一塊黃色的水泥柱--那種用來阻止車子停在樓梯門口前,或是保護停車票卷機不被撞上的柱子--出現在他的位置。柱子重重落在地上,在一邊倒下。同一時間,我們聽見身後的沈重撞擊聲。
一個有龐大雙手的金屬的巨人,還有個水管在它背上,嘔吐出一陣陣灰黑色煙霧,那隻大手握住兵器大師。它不斷地,有條不紊地,把兵器大師撞進一輛車的後車廂。
軌彈天人,以他美式足球選手般的身材和穿著的尖角分明防彈衣,踏出無畏左邊正好在入口側車子的陰影。一位我認了出來,但還沒見過面的女孩,從無畏右邊出現。她化了小丑妝,戴了個弄臣多角帽,還有個青、橘色緊身衣假面裝,最外面則穿了件燕尾服。鈴鐺在她的帽尖、她的燕尾服、她的手套和靴子上刺耳響亮。她的假面裝、化妝和顏色設計,在她每次出現時都有所不同,但主題總是或多或少都一樣。
無畏移動要撤退,可是烈陽舞者攔截住他,從建築前方走出來就將她的小型太陽放在出入口的正中央,擋住他的退路。
我沒有足夠的蟲子來貢獻戰鬥,也沒有概念現在正發生什麼事,我就在旁邊,這樣待著,眼看眼前我之外的場景以驚人的速度發展。
兵器大師奮鬥掙脫出那個巨人的金屬手掌,可是發現自己對付的不只是那台機械,還有一隻《黑湖妖譚》的怪物--它全身充滿了殼甲,還有章魚觸手在手臂和臉的地方伸出。幾個短暫時刻裡他成功抵抗了它們,直到他對那個章魚生物揮出戰脊,結果一個車子保險桿卻出現在戰戟的位置。他在保險桿實體化時沒抓好,他摸索了下,弄掉了保險桿。他能從驚訝或缺乏一個武器中恢復前,發現自己被一隻機械手掌抓住。蒸氣動力巨人繼續他的條不紊,用兵器大師痛打現在已破破爛爛的車子,而那個章魚-螃蟹人有耐心地在旁邊站著等待。
戲團對無畏丟出滿手的飛刀,它們在他將自己包裹進力場泡泡時就被反彈掉。不過那泡泡一立起,我看到軌彈天人朝下伸手碰了台停在他旁邊的車子。他對那輛車用他的力量時,你無法看到車子移動。倒是,在一眨眼間,車子從原本位消失,猛然出現在一個幾乎環繞那個力場上半部的位置。它在力場卸下前開始滾到力場另一側,掉落在距離無畏不足一呎之處的地面上。
戲團沒有停止移動。當汽車擊中地表,她雙腳踏上車盤,她走上了那輛車越了過來,朝無畏猛衝。她將雙手往後伸,在某個我無法看見她的雙手時,就拿出一根雙手持的七彩色長柄大錘,當她把大錘朝無畏的方向揮動時,色彩拖曳流光。
戲團是其中一位,那種具備好幾種小能力的假面。我知道的那些人有好幾個小型操火能力、把物品憑空儲存起來的能力、也能同樣簡單取回那些物品,還有極大強化的手眼協調與平衡,來完成整組超能力。她是布拉克頓灣比較成功的單飛反派其中一位,身為強盜和竊賊,假使撞見一位英雄,她足夠迅速、靈敏到能獲勝或溜走。如果我記的正確,她曾被提議來接暗地黨的位置,然後也強烈拒絕了。
這也引起她和行旅人,在這裡要做什麼的問題。
無畏以電弧長槍格檔住戲團的長柄大錘,下一秒那柄大錘消失,就像未曾存在一樣。然而在同一時刻,她成功將一把點著了的火炬滑進手裡。她將火炬舉到嘴邊,朝無畏的方向吹出一大團火焰。
他從火流中蹣跚後退,舉起盾牌,再次以它張開成力場泡泡。盾牌舉起後不到一秒,軌彈天人又把另一台車子射上盾牌,車子反彈的力道足以撞上天花板,摔在地板上,飛到停車場的另一側。盾牌再次失靈、閃爍消失,無畏便蹣跚跑開。
戲團抓住機會縮減距離,火炬不見了,拿了大錘出來。緊接著是殘忍不講理的痛毆,當戲團每揮了兩次大錘,就讓它消失而不是往後方舉起,這讓她的攻勢更加無情。她迅速蹲下避開他的電弧長槍,接著她往他身旁踏步時小圈旋轉。當她旋轉自己的身體,那長柄大錘再次出現。她把手中的武器也帶上旋轉力,重重打上無畏裝甲胸口正中央。
無畏倒了下來,衝突兀然結束,沈默的只剩烈陽舞者的小型太陽,以及外面單獨一聲的汽車喇叭。
那兩個巨人--那個機器人和奇怪的海洋生物--靠近我們,魔閃師在他們身後慢慢跟著。我能看到機器男的臉,十分有高加索人的面頰,雙頰上還有著青春痘疤,他的長髮綁在腦後成了個油膩的馬尾,他臉的上半部被金屬面具和護目鏡遮住,我現在才能認出他。他就是車骸,是個滿像混混的反派,還沒為他自己闖出名號。我沒辦法說哪部分是那個機甲或是他真正的身體。就我所知道的,他算是某種燃煤動力改造人,或者是一個,不幸因自己的能力與紐特和格雷戈同樣被轉變身體的人。
當然,不能將那個奇怪生物排除,它只可能是行旅人的,創使了。
車骸把被擊敗、全身是血的兵器大師扔到地上,就在無畏旁邊。他花了一秒審視那把戰戟,接著把它在雙手中折斷,把金屬拳頭中剩下的東西碾握。他將弄爛的殘骸扔在失去意識的英雄們身上。
我掃視了這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行旅人和兩個反派從未--就我所知--組成隊伍。沒有人說話。
一個平滑、非常有自信的嗓音打破沈默。「我想,媘蜜,當妳說要和我在你們任務結束後見面,妳沒有提起會帶英雄們來。」
一個穿克維拉背心和巴拉克拉法帽的士兵,為蛇蜷,按著打開了的樓梯門。蛇蜷穿同樣那件有白蛇橫跨的黑緊身衣褲,他加入了我們,十分緩慢地走著,他雙手在身後交握,將眼前的情景以欣賞的眼神觀看。兩個士兵跟在他身後,手中拿著槍。
蛇蜷。我感覺自己的心跳加速。
媘蜜的表情相當疼痛。「對不起。」
蛇蜷環視了後,看起來做出決定:「不。我不認為有什麼要道歉的。」
他頓了下,我能想的全都是這就是了。我有我需要的東西了。
蛇蜷說話時,更像他對自己感到愉悅,而不是對我們任何人滿意:「我感覺這真戲劇化。計畫是要行旅人、戲團和車骸從影子中走出來,而我則讓人印象深刻地走進來。可惜沒辦法那樣實行,但我猜這確實有戰略利益。」
「我猜是吧。」媘蜜微笑。
「好吧,看來妳今晚很成功。很好。沒有更多人追蹤?」
「沒。」
「緊急應變組?其他英雄?」
「全都至少要花兩分鐘半,我想。」
「那麼我們就離開吧。暗地黨,行旅人,我已經準備好了車子,我希望你們來和我一起搭車。我相信我們有很多事情要討論。」
ns 15.158.61.51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