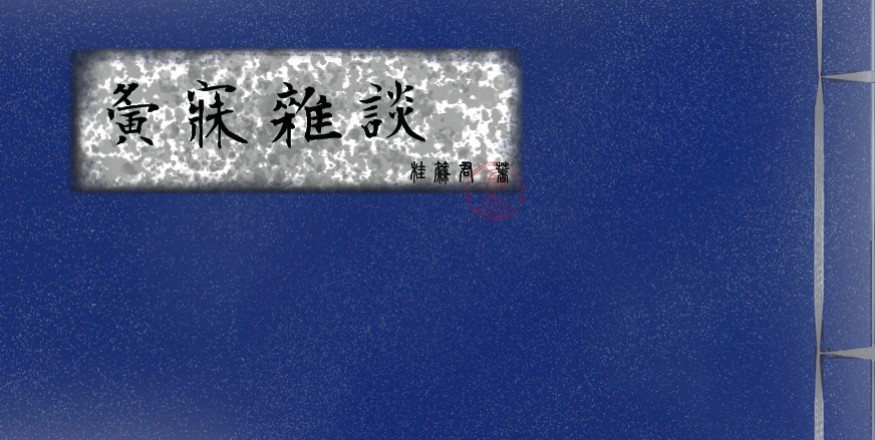趁著夜點的一些時間,衛京是邊吃邊把這水穀堂的事情給說了一遍。另衛京感到意外的是,宗非拺是二話不說地就答應了凝塵開了這些條件的交談會。
「這麼晚還外出,我還以為你會不答應呢!」
「有什麼好不答應的?」
「你不都很早就回來了?我還以為你不喜歡晚上外出呢。」衛京想了想幾個例子,除非有事,要不然宗非拺確實是沒有晚上外出過。這次他主動外出,雖然是自己跟凝塵的邀約,但也好歹難得了一次。
對於衛京的疑問,宗非拺給的理由卻很是平常「沒事何必要晚上外出呢?」
衛京沒想到的點是,北嶺的環境與馥鎮大不相同。馥鎮的夜晚,或非特定的幾個節,要不然多半是稍有涼意,不至於出不了門。北嶺可就不同了!午後日頃,那體感可謂直降不止,更別談入夜後還要外出什麼的,那待上一晚可是會死人的。這的確是沒有甚麼特別的事,誰會想外出?
當然這點宗非拺沒跟衛京解釋,衛京自個當下也沒意會出來。只當如同宗非拺所言,純粹就是沒想外出而已。
「你這沒問題,那我明日就跟凝塵談妥時間喔。」衛京撓了撓頭,想了一會又補充道:「大概就這一兩天的事吧。」
「這麼急嗎?」
「這怎能不急?」衛京嘴上這樣說著,內心想的卻是被扣在宗非拺的那本春書上。這別說急著趕宗非拺辦完他老爹的事,這衛京去西原的老爹應該都準備返程了!
對於衛京的急火,宗非拺只當他辦事求快求成,也沒管這般多。隔天就隔天吧!反正又不是天天晚上往外跑。
「我們要不要先準備什麼東西呀?」宗非拺反倒是比較擔心這個。
「準備甚麼?就是去跟人吃個茶談個話而已?」
不比衛京的單純。這時的宗非拺已經在心中開始想了各種問題與備話,就怕當天有個什麼意外。
而當宗非拺把這樣的想法跟衛京解釋後,衛京卻是覺得宗非拺想的太多。
「凝塵沒你想的這般心機好嗎?這聚談很單純的,就聊聊李師而已。況且就他這樣的態度看來,我倒覺得凝塵頗希望你把李師給聘回北嶺去。」
至於理由是甚麼?衛京自個也不知道,更別提要跟宗非拺解釋。不過從凝塵這麼幫忙的情況下來看,這舉動是不難猜出就是。
這時刻也過晚,拿著吃夜點的理由也好該歸宅。衛京也不管現在宗非拺如何想,桌上打點一番之後就打算回家。衛京這一路上只得領著不停做想的宗非拺往自家家院歸去。
尋日,到了約好的聚談的這天。由於約在水穀堂附近的茶館,所以住在北冬街的衛京與宗非拺早早就出了門,免得遲了邀約。
這衛京穿的到是比平常還要厚實,主要是近冬的夜晚還是略有涼意。不敢說有多低溫,但那風倒是可把沒關好的窗櫺給吹個咯咯響。
「你這樣也有些……過頭了吧?」衛京從出門時就想這樣跟宗非拺說。
相比衛京的穿著,住過北嶺的宗非拺雖然穿的就沒這般厚實。不過那穿著卻是比平常還要那麼正式不少!從那褥衣、外衣的層次搭配,到紳繩掛件紋飾來看,肯定是有特別細選調過。不得不說,宗非拺肯定是非常看重這場聚談。
「第一印象很重要的。」宗非拺對於衛京的話不以為意。
「第一?不是開堂那次就見過你了?」
「那都多久的事情了?」
「我說過凝塵記憶很好的!」
「連個自己姓氏都不記得的人?」宗非拺可沒忘記凝塵那些奇怪的語病。當然衛京也沒忘。
衛京也說不上甚麼,他總覺現在的凝塵與那時候的凝塵又有些那麼的不一樣「我覺得這問題等等也可以一並問他。」
關於這點,宗非拺反倒沒甚麼在意。「不管是不是見面的『第一次』,總歸也算是私下聚在一起的第一次,穿的好一些總歸是沒甚麼問題。」
「你說的是就是。」衛京也不想多辯。
兩人沒多久就到了預定的水穀堂附近茶館。茶館這時間原先是沒有對外營業,貌似是特定為了他們幾人而留了個位給他們聚談用。
宗非拺坐在位置上,看了看周圍環境後道:「看這安排,想來凝塵也不是甚麼都沒想過。」
這聚談的位置偏茶館内邊,就算這位置點了火光,從茶館外面看過來,也是見不著半點燈火,就好似沒人一樣。若不是特別進到裡面,或是他幾人談得太大聲,這外面理當也聽不太見裡面在說什麼。
這別說位置選的得當,就連這店從小管也是上了茶水小點後就走人,連句話也不多說,遠遠朝那灶房看去也見不著人,就好似消失一樣。
衛京見怪不怪,且當人家事前安排好,也自個隨意起來。
衛京幫宗非拺與自個沏了杯茶後道:「畢竟他也是要瞞著李師外出,就算離水穀堂近,多少還是要防備一下吧。」凝塵這點情況衛京也跟宗非拺解釋過。不過凝塵與李師的關係為何需要到凝塵特定隱瞞外出?衛京與宗非拺也不是有多了解。
兩人隨意談著等等要與凝塵討論的話題,邊等著凝塵從水穀堂偷偷出來。
然而兩人這一等倒是等了有些時間。這離原先約定好的時間約略過了半個時辰,若說這訂好的時間是凝塵打算偷偷外出的時間,那這半個時辰的「偷偷」未免也有些過頭了。
「難不成是失約了不成?」宗非拺默默道。
「那是不可能。這三人提前聚談還是他自個先提出,他這沒理由自個黜自個的約呀?」這樣自個搞自個的提議,還是對自個有利的提議,根本沒必要呀!況且衛京心想,就他對凝塵的感覺來說,他也不是這樣的人。
想了想後,衛京猜測道:「可能在水穀堂有個甚麼耽擱?」這是所有情況中最大的可能。
宗非拺朝衛京確認道:「凝塵是說會瞞著李師對吧?」
見衛京點了點頭,宗非拺約略推論出了個最大的可能「多半是被李師耽擱了吧?」
這說法的可能性衛京也頗為同意。
畢竟這夤夜之時是凝塵自個定的。原先的目的就是要瞞過李師外出,而超過這時間凝塵都未依約,想來是李師動了什麼作息,導致這夤夜之時,凝塵都還未有個法子可以瞞過李師外出。
衛京與宗非拺兩人現下也只能這般相信,自然也改不了甚麼,更不可能衝到水穀堂去找人。
兩人從一開始談話到現在等人,周圍彷彿突然安靜許多。除了茶館外的風聲之外,就連那貓間的荒叫貌似都可聽的一清二楚。
一直無底的等下去也不是辦法。然而就當宗非拺剛要開嘴提議該怎辦時,凝塵就從茶館外跑了進來!
凝塵這一進來,見到兩人早已在位置上等著,自個也知道早已遲到許久。進來之後連忙跟兩人道不是。
「對不起!對不起!讓兩位耽擱這麼久。」凝塵在桌邊邊道歉邊鞠著身子。這身子一彎,連連在地上低了幾滴汗水,顯然趕的匆忙。
兩人的確等的有些時間,但也未到需要發脾氣的地步。衛京率先開口,幾句無妨、無妨帶過。
宗非拺倒是觀察凌厲,這朝凝塵一眼望去,除了滿身大汗之外,這衣物也是有些凌亂。這水穀堂離這不過幾步路程,連過個街口都不到,真要說跑著過來也不該如此。換句話說,就算凝塵前幾刻才出門用走著過來都不該如此失態才是。
「該不會水穀堂那出了什麼事吧?」宗非拺淡淡說著。
宗非拺這樣一說,凝塵的神色有些變化,但是沒有很免顯得表現出來。聽聞宗非拺這樣說之後,凝塵沒有扯什麼嘴皮,很是乾脆的點了點頭,直接把水穀堂的事情說了出來。
「我原本是想等李師、恩,睡下這才出門。沒想到今日李師不知怎的,特有活力。勸了幾句都不肯睡,直到剛剛。」
衛京一聽,到覺得也不是甚麼大事,不過就是點小意外。反正現在人也出了門,想來應該就沒事了。幾句閒話就跟凝塵開始打起哈哈。
兩人在那說著嘴皮,宗非拺在一旁沒有多言什麼。宗非拺對於剛剛凝塵的那一絲變化剎有一瞬察覺,但是那一瞬過於快速,快地讓宗非拺不是很肯定。
或許凝塵剛剛說的話是事情,但是這事實之中肯定有什麼是他沒說清楚的才是。
宗非拺這還未開始多想甚麼,一旁的衛京到是開始把話帶了過來。
衛京拉著凝塵往自個這邊坐下,朝著對面的宗非拺開始道:「雖然你倆之前見過幾次,但還是跟你介紹一番。宗非拺,我遠房堂哥,就是要託聘李師的人。恩……凝塵?」
說到這裡,衛京卻是突然想起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凝塵。 基於上次凝塵自己的稱謂,現在衛京不確定凝塵究竟要叫杜凝塵?還是稱李凝塵?
衛京嘴上的籌足,凝塵也看了出來。他主動接下了衛京的話語,自個介紹了起來。
凝塵朝兩人躬了手禮道:「叫我『杜』凝塵吧,若是不習慣的話,直接叫我凝塵也行。」凝塵語畢,又對這事的疑慮補充道:「李師不過是我名義上的養父罷了。」
此話說完,凝塵就見宗非拺那應答的話語上有些生疏,似言不言,貌有蹊蹺。
凝塵朝宗非拺道:「宗非兄是吧?我同衛子一樣稱你恆叱尚可?」聽聞宗非拺一句無礙後,凝塵這才繼續道:「恆叱兄有話直言,無須匿著。」
恆叱眼盯著凝塵,就怕分神錯過凝塵臉上的意思變化:「不知凝塵兄為何自謂杜氏,許久前與衛弟閒聊卻自稱李氏,這是為何?」
這問題也是衛京與宗非拺一直覺得凝塵奇怪的地方。如同坊間那些傳問一樣,凝塵記憶不好,所以這才足不出戶,幾年來一直蹲足於水穀堂。
宗非拺提的這個問題看似普通,尋常人或許幾句交代就給帶過。然而這問題對於凝塵來說其實卻是直切所有問題的重點──他會週期性的失憶。
雖然這問題大可直接跟眼前的兩人直說就是,但是這又會扯出後續一連串的各種問題。這問題就好似那田間荒草一樣,壑土上看著一叢,拔了一把才知這根系連綿不絕,一串接著一串,從田頭連到田尾。
然而這失憶問題其實跟今天要來找兩人談話的目的也拖不了關係,所以這事情不說清也不行。凝塵對這問題也沒多想甚麼,就打算把事情的幾個始末給兩人說一說。
當然從頭說起來會沒頭沒尾,自然還是從他兩看到的面相開始說起。
凝塵喝了一口茶後,淡淡說道:「我其實會週期性的失去記憶。」
凝塵這一說,著實有些簡單又突然,原先以為會有一長串解釋的兩人,一時之間還以為自個沒聽完整。「什麼?」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會有週期性的失去記憶,或者該說是記憶回朔,有印象的部分會回歸到某個時候。因此我大概推算的出來,我失憶時的幾個段落。水穀堂剛開辦時,我應該有跟衛弟聊過對吧?」
「……沒錯。那時候因為沒登記到恆叱,我倆到門口找了一會,卻又沒等到恆叱回來。」這也是衛京對凝塵的第一次印象,當然是忘不了。
「這裡可能要跟衛弟道個歉了,事實上那次的聊天我大概、不,應該說我忘了。」
看著兩人不可置信的面孔,凝塵用剛剛宗非拺所說的姓氏自稱,再結合自己推敲出來的幾個點舉證了一番。
「若跟剛剛恆叱兄說的詞結合起來,我應該在那時是跟衛弟說我姓杜對吧?」這點凝塵甚至不用等到衛京回答確認,就已經知道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在那幾天後我就發生了週期性的失憶。而在失憶的這個期間,我對外的宣稱應該是姓李。」
除了這個失憶前後的自稱說詞之外,像是對衛京的態度、水穀堂上的行為等互動,凝塵都可以很精準地說出失憶前後的分別情況與對比,而這說詞無一錯誤,字字都與凝塵說的相當。
儘管凝塵說的實在,宗非拺還是有點懷疑。
「你這幾個說詞與情況,聽起來不像是失憶的樣子,就好像你還記得一樣。」宗非拺這說法只是沒明著說這失憶是你裝的罷了。
會這樣懷疑也沒有辦法,畢竟哪個失憶的人還會有如此?如此對自個過往行為有清晰的記憶?
雖然凝塵自個有在紀錄語書寫日記,而現在那些東西就放在水穀堂的黑竹書笥裡。但是凝塵暫時還不打算把這些東西說的這般多,難保一個解釋之後又有另一個質疑,總歸在不停地為上一個質疑作解釋。
凝塵把話就說到這,不打算對做懷疑的宗非拺有過多的回答。「失憶這點我沒有辦法跟你證明什麼,不管你是信還是不信。我只能這麼說,就是如此。」
一時之間氣氛搞的有些僵硬,宗非拺對於這個回答並沒有過多的追問,但要他全然的相信這個說詞?宗非拺的心中肯定還有些疙瘩。
這只不過是在相互介紹而已,真談起來那氣氛該有多壞?衛京見氛圍如此尷尬,連忙在桌下用腳踩了幾下宗非拺,還朝他擠眉弄眼,示意了一番。
見宗非拺貌似了解了自己的意思,衛京連忙在旁緩頰道:「那個我看大家也就認識到這,我們不是要來談李師的事情嗎?」衛京說完,朝宗非拺看了看,要他先接個口。
宗非拺一看,當然知道甚麼意思,這不連忙把話給帶上。
「前先日子叨擾了。後聽聞衛弟與您談起,這才知道與李師有些誤會。」
這事情衛京也是有跟凝塵說過,約略的來由衛京與凝塵也談過數次。只不過礙於宗非拺不再現場,那時候也沒有談的多深入。衛京對於凝塵提的幾個問題,是無法全然替宗非拺回答;凝塵對於衛京問的幾個疑問,是無法全然替李師應下。
既然現在兩人在場了,衛京自然是希望能把事情給好好說開。現在衛京能做的也只能到這,剩下的事情只希望兩人能在此辦妥,宗非拺就能安然的離開馥鎮。
衛京在一旁假裝半喝著茶水,看著兩人進度如何。
宗非拺的來意很是明顯,如同衛京之前跟凝塵說的,就是來聘李師。而先前在水穀堂的那場風波,只不過是場意外。
聘師這事情凝塵是清楚的。衛京記得自己當時不小心對凝塵說了出口,只不過凝塵當時礙於李師的各種問題,僅只於解開宗非拺與李師的誤會,更深入的聘師問題,就沒有再跟凝塵討論再多。
而現在果不其然的,凝塵第一個提出的問題也是問到宗非拺關於聘師的問題。
「聽聞衛弟說過,恆叱兄托父親來邀李師去北嶺。不知道宗非家父與李師是何種關係?又是為何要離開北嶺,遠至馥鎮聘李師回去?」這個問題衛京其實老早就跟凝塵說過。只不過現在凝塵貌似想要聽宗非拺親口說罷了。
而宗非拺的回答如同衛京當時所言,是託老爹卜掛而來。至於為何是馥鎮的李師?宗非拺當然也不清楚來由。
凝塵聽完之後,放開態度先表明立場道:「你們要聘李師,其實就我現在的立場來說是雙手贊成。但是這個大前提是,聘李師是讓他過好日子,而不是受苦的。畢竟沒有人希望另一伴、恩,我是說親人,換了另一個環境之後是過著壞日子。」
宗非拺略為想了想後答道:「家嚴為何要聘李師,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如同我前面所言,我甚至到了馥鎮才知道有衛家存在,更何況是李師?」宗非拺緩了緩語氣,嚴詞誠懇繼續道:「我無法要強迫你信不信卜卦聘師這件事。但是我能跟你保證,宗非家聘師絕無頑惡固劣之想!宗非家聘師,絕對一視同仁,這絕對無關他的身分、年齡……等其他而有所區別。」
宗非拺的話只能說到這,其他的東西如同凝塵一般,有些事情嘴上說說,真要證明什麼的?那也不過繞更多的圈子罷了。
宗非拺見凝塵沒回話,貌似還在考慮。又補了一句:「如果凝塵兄擔心,也可一同前往。相信家嚴是不會在意李師攜家眷前去。」
然而想不到這句話凝塵反倒是想都不想,搖了搖頭就拒絕了。
「李師若真要去北嶺,我是不會一同前往的。」凝塵言下之意非常明確,就是李師一人,且與自己無關。
至於原因?宗非拺當下也是問了一句,不過凝塵沒有回答。凝塵故意棄之不答,說起別的話來。
「李師去不去,我當然無法作主,畢竟要去的人是他,我只是擔心他走上歪路而已。不過聽聞恆叱兄這般說來,或許回去北領不是甚麼壞事。」
「李師以前住過北嶺?」
「聽他說過,不過應該不是山岳裡的那個北嶺,或許比較偏南方一點。」
凝塵一說完,宗非拺偏起頭來開始想著,北嶺南邊自個家族裡是有哪個比較熟識的,或許有人認識李師的老鄉也說不定。
不等宗非拺想好,凝塵這邊倒是早已做好打算。
「我這邊先跟你講幾個李師的忌諱好了。免得你邀李師的時遇到什麼困難,這樣你們交談下去也比較好談。」
這問題的確也是今日來聚談的重點,宗非拺自然是開始聚精會神的聽起來。
這李師的忌諱,凝塵說起來其實也就這麼幾個點。就算不特別書寫,光聽起次記起來也不難。
而這幾個點無非繞著李師過往的身分打轉。例如,稱謂李師時不要用舊名、不要跟李師談論起對打之類的競爭行為,居如此類的東西也都大同小異。
李師過往的事情,宗非拺也聽聞衛京轉述過。因為家鄉發生這種血光之災,會有這些忌諱,也是不難理解。
而這幾個忌諱講著講著,那話題竟是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凝塵的各種抱怨,抱怨起李師生活上種種的壞習慣。
「聽起來反倒是你在照顧他?」衛京這一路聽下來,突然的插嘴說到。
「可以這麼說,李師其實比你想的還要年輕。」
不知怎來由的,宗非拺突然問起一句毫不相關的話來:「凝塵兄不知多大了?看上去跟衛弟差不多?」
這個問題凝塵也是笑了笑道:「比你們想的還要大就是。」這回答聽起來跟沒回答差不多,不過真要說錯也不知道錯在哪。
說到這些,凝塵也自覺把話題差地遠了,立馬把話題也倒了回來做個結。
「我看時日選在水穀堂這期過堂之後吧?」
「這麼快的嗎?」衛京有些詫異到。這不過了半載而已?
「李師這水穀堂也不是甚麼大庠,教教皮毛而已,這當然比不上那些大家,沒必要扣著眾人在水穀堂這般久,這些時日教的也差不多了。」
其實凝塵說的也是有道理,不說學數計的,就連學字的衛京都學得差不多了,那其他不是來學字的早就學的七八分有了。這還不過堂?那還要拖到何時。
凝塵說完繼續道:「我會跟李師談好,趁著過堂後比較空閒的時間在外吃吃,你們先在那等著就是。」
宗非拺就這凝塵的話又琢著地點、時日什麼的更加補充詳細,這裁定了個時日下來。
凝塵見事情說得差不多,這拍了拍衣襬外絝就打算離去。
「那實情就這般說定,時日不早,兩位回去還請多加注意。」
幾人又是一陣寒暄道別,凝塵這才匆匆忙忙地離開了茶館,而宗非拺、衛京兩人這才後著出去。
一路上雖然暗著可以,不過秋尋時節的天輪看上去貌似比往常還要大,透著那麼個月光,大街上也不是這麼的昏暗。
這回去的一路上,不知怎的宗非拺卻是半句話都沒說,貌似在想些甚麼事情,就連到了衛家大門都忘了進去,差點就過門直直走去北門去了。
衛京控著音量,聲音小小的氣音道:「恆叱,你要去哪呀?到家了。」衛京這一喊道,宗非拺這才轉過身子看了過來。
「你在想什麼呀?這麼專注。」
宗非拺想了想後這才跟衛京道:「我在想剛剛凝塵說的話。」
「李師的事情嗎?這不、進展挺好的?就差你當天能不能說服李師了不是?」
「那是一個問題,不過我剛一路上想的不是這個。」
「凝塵的話?他說了甚麼嗎?」衛京這樣聽來,卻是凝塵說了什麼早已忘的許多。或許是因為專注在聞李師的種種顧忌,這才沒有記憶到凝塵還說了些甚麼。
宗非拺見衛京沒甚麼記憶,倒也不好討論,擺了擺手就道:「沒什麼,我們先進去吧。」
衛京見宗非拺沒答這也沒在意什麼,領著人就往院內走去。
宗非拺這回到房間內,不只沒有停止思考。坐到案桌旁的矮凳上,又開始繼續想起剛剛凝塵說的話。
「比你們想的還要大就是……」宗非拺總覺得這句話貌似有個奇怪的點沒參透,好像哪裡有些詭怪?但宗非拺又說不上什麼。
ns3.137.186.20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