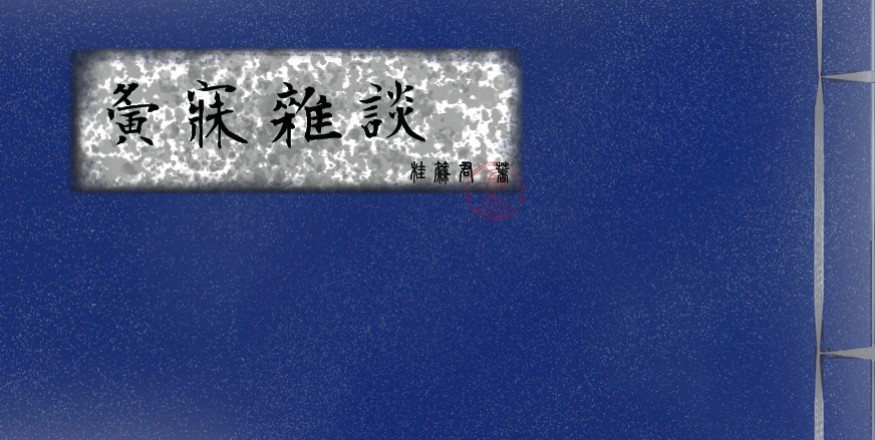7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i9Orzb0td
裴束修這樣子,耿菽哪會相信什麼沒事這種說法。然而耿菽蹲下身子朝坐在椅上的束修左看右望得卻也看不出甚麼外在端倪。
最後猶豫片刻,束修怕耿菽最後動起手檢查起來,只好自個先說來。
「那個醫太以為我是你從別處帶來的男契,帶來這要那個……」
這後話不提耿菽自然知曉,顯然是被人誤會來這吃外食,再加上剛剛退了頭務跟後面的服務,的確要讓人不想歪都難。
如果只是提這個,怎可能讓束修這樣害羞,顯然那醫太還提了什麼。耿菽續問之下,束修這才緩緩道來。
這醫太好心跟束修提了幾句,主要是要他明道身子剛恢復不宜行房,更是使不得穀道,勸束修別跟耿菽一二,直接拒絕就是。醫太也是好心,怕束修拒絕不了,還隨口說了一二個南風院對新客慣用的手法,要束修隨意幫耿菽弄弄就完事,不要再叨擾自個身子,壞了恢復。
束修雖不是孩童,好歹還是個處,頂多看過幾個密戲春圖,打個手活過,乃還有什麼實戰經驗。這一聽醫太手法說來,實打實的畫面一想來,難免羞澀臉紅,這才有了現況。
這情況耿菽也是無言以對,只到自個無過,他人有意。
耿菽拍了拍束修肩膀,讓他回過神道:「這事你別想太多,明天醫太來了我跟她解釋就好,別想太多。」拉著束修回桌上打算繼續吃晚膳。
鬧過這麼一齣,兩人也沒什麼胃口食之無味,桌上飯菜又是隨意吃了幾回就草草結束,也沒完食。
須臾,耿菽托人前來收拾桌上飯菜,自己也順道打算跟著出房去取個兩人盥水。
回過頭要束修自個注意,要他先幫忙整一下行李,房門上拴不是他別應門,也別自個好奇外出。
束修不疑點頭應是,耿菽也就出去取水去了。
這事束修不知,在樓欄房內,一盆盥水哪還需要客人去自取?那這南風院的服務也太不上道!而耿菽會這樣說,也是藉口離開房間,想要自個在南風院內蒐集一些訊息罷。
在南風院房內雖不比什麼要塞壁壘安全,但你只要有錢花的起,不怕進不了門開不了防,但要是尋常人可是連外門都進不了,更別題就算進來了,這裡間數眾多,不知道人在哪、房名是哪間?要找特定人物可謂難上加難。別說兵衛難尋,芳樂本身就是景家在管,除非景家不要商譽了,要不然自己人也是無法擅闖。
你道耿菽要尋什麼訊息?這自然是景家實質當家,景煜的消息!
且暫不提耿菽尋著方式、過程如何,這景煜消息也不是尋常找找就有,自個藉口外出也不好拖太久引束修懷疑。一時找尋未果,耿菽只好提了桶盥水與巾布歸去,且算明日再尋。
一回房間卻見束修不知怎地在趴在桌上睡著了。這事其實也不打緊。原來是因為束修忙個一早上了,現下突然無事等著耿菽歸來時,一瞬間放鬆下來竟是開始犯起困意,不知不覺得在桌上盹起睡來了。
耿菽拍了拍束修,卻又不敢太大力。輕聲在旁道:「裴仲,稍微清個身子上榻在睡吧。等等又著涼了受風寒是好?」
無奈束修貌似累得很,睜眼看了看後,見來人是耿菽竟是安心地揮了揮手又打算睡去。不料耿菽也是不死心,趁束修未熟睡又是一震晃肩,同時半真半假的作勢恐嚇道:「你再這樣,我可要幫你給抱上榻囉!」
這話一說,束修也是醒了一絲,不過卻是拖著身子懶得起來。雙眼閉著,嘴上伊伊嗚嗚假睡著,心中想著大不了就是被梗菽給背上榻,這又有何不可?
束修還想著耿菽是以前好使喚耿菽,自己只要懶得應,自然耿菽會收拾善後。殊不知,耿菽的確是以前的耿菽,會幫他善後做打算,不過現在的耿菽可是比以前要大膽多了!雖然束修沒有明確的跟耿菽表示心意,但是耿菽看的出來,束修名面上肯定是不反對,甚是有好感。而早就跟束修表明過自己的心意的耿菽,也就仗著此意敢放手跟束修示愛。
而耿菽也不愧是以前在束修身邊侍過一段時日,束修甚麼心性與常慣老早就一清二楚。束修那懶著起身的少爺脾氣,也就只有在外、在耿菽面前敢使,束修這種樣貌裝得老早就被耿菽給看出。
既然束修敢這樣使,耿菽也打算順著他意玩起來,就看誰先忍不住自個破梗。
耿菽怎麼想束修自然不知,就是趴在桌上等著束修來背他。而果不其然,是盼到了耿菽過來把他給背到榻上。
背是背到了榻上,不過卻是沒盼到什麼被子蓋上來,耿菽也就幫他把外衣給拖了,就這樣放在榻上不管。這不經讓束修覺得奇怪,這點小事理當不會讓梗菽疏忽才是,怎就這樣放著自己不管了?束修強忍著想張開眼睛確認的慾望,想說等著片刻確認是否有後手,這一等卻是沒等多久,不讓束修多想甚麼,一陣擰水聲響傳來,偶後束修就察覺自個上身褻衣突然就被耿菽給拖了個空,耿菽意料之外的舉動與脫去衣物夜晚帶來的涼意,讓束修露餡地低鳴出了幾聲。
然而耿菽貌似沒發覺,認為束修自己是夢囈一樣,耿菽在榻旁邊聲音不大不小地道:「幫你擦個身子而已,你繼續睡便是。」
那聲音彷彿哄小孩一樣,讓束修誤以為耿菽沒發現他假睡,也就任著他給耿菽擦身去了。
耿菽這一擦,起初束修沒覺得有什麼不妥,甚至覺得這水溫適當,剛好不會讓他因為脫衣而覺得冷,壓過自個肩頸的力道舒適、揮過自個背脊的手感適當、撫過自個胸口的手法順心。這些極好的感覺,讓假睡的束修都有些不自覺得開始真睡起來。放鬆的身體與恍惚的心神,竟是讓束修沒察覺耿菽在自個胸口吃了許多豆腐而不知!
若說擦個身子乾淨也罷,不過耿菽這胸口著實是擦得比其他地方還要多了一倍不止。耿菽原先想著,擦的這般明顯,不醒的人也該醒了吧?卻不知自己擦的手法竟是讓束修真的快睡去。
耿菽擦著擦著不見束修有想起來的跡象,眼見這胸口兩端都給擦的立起見紅,耿菽只好做的再過些,這擦完的巾布往水盆一丟,手是往紳帶、腰邊絝口而去。
耿菽一手解完紳帶結,束修還沒麼實體感覺,而就待耿菽一指往絝口內插去,和著絝外幾指就打算拉扯的同時,束修卻是立馬驚覺!
束修一時之間什麼舒適順心感消失得無影無蹤,醫太說得幾個畫面卻是不自覺地浮上腦海快速晃過。
趴的榻板震了一聲!束修一個挺腹施力,上身彈了起來,兩手就抓的外絝不讓耿菽脫去。同時還一臉通紅的朝一旁耿菽喊道:「你做什麼!」
束修只見耿菽一臉正經無殊,朝他笑了笑道:「現在醒啦?」
原先還想著耿菽怎樣這樣得,現在看到耿菽這樣,想通前因後果後,束修這才明白耿菽早就知道他裝睡,鬧著他玩。
「你早就知道了?」束修一臉不解,自覺沒有半點破綻。
耿菽拍拍他的頭道:「日清冥都跟你住過多少次通旅了?我會分不清?你倒好,習慣都沒變過。」
束修被耿菽這樣說白也沒反饋幾句,就是被他看透得有些害臊。
束修故作鎮定不談自個假睡,就談耿菽手腳不乾淨,心中晃過幾個醫太說的畫面就朝耿菽謮道:「那你脫我外絝做什麼?」
耿菽一臉無辜清白反道:「擦身子呀!沒理由擦一半就睡吧?多髒呀。」
耿菽的確是沒打算做什麼,畢竟他早就知道束修是醒著,自然不敢多動手腳。但只要耿菽自個作勢脫束修衣物,怕人家看的束修肯定會醒來!前頭脫上身褻衣看他還忍著,現在脫外絝這不就忍不住了?換個角度看,這個擦身子說法就束修方面來看確實沒半點藉口樣,正常不過。至於在這之前的擦胸口與撫摸,耿菽見束修現在沒說什麼,自然耿菽不會犯傻自己去提。
儘管這說法正經,束修還是有些不信。
「擦身子,那你布呢?」
「總要清個換水吧?」耿菽指了指一旁盥盆說道。
束修也沒好想法逼問,只好跟耿菽要過巾布,跟耿菽說打算自個擦。耿菽也沒拒絕,見束修醒了就好,遞過巾布就往旁邊坐著。
這擦下身自然是要脫下絝,束修儘管在怕人看,也還是得脫。不過他可不像耿菽一樣打算全部一脫了事,而是只脫了外絝,打算擦個腿腳就了事,他可沒打算脫光讓耿菽看個光。
束修擦身子,耿菽也沒打算一直盯著,怕自個盯著只會讓他越擦越慢。耿菽回過身開始收了收一旁幾個脫下的衣物。
耿菽剛收拾沒多久,身後就傳來束修問話:「……剛剛真是打算擦身子而已?」
「不然呢?」耿菽沒想太多,只是有些笑意回到。
耿菽有些笑鬧的話語,不知怎地讓束修怒意中又有些失望,擦著身子卻是開始賭氣著不回話。
耿菽見狀,也知道束修有些生氣,自然不打算繼續鬧他,也就安靜過著。
片刻,不等耿菽摺疊好衣物,背後突然就是一陣輕撞,就聽到背後束修喊道:「不管你了,我要先睡了。」
耿菽回過身,只見腳下丟著一條巾布,想必是剛剛束修朝他背後砸過來的。抬頭見著束修背對著他,身上只穿著褻衣褥絝,被子也沒蓋。
耿菽隔空喊道:「蓋個被子吧?」
耿菽見束修貌似還在賭氣,只好自個走了過去幫他把被子蓋上。
7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87PPIfPG8U
7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wSLp16BoPh
7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0IUL6kuUqK
暫不論耿裴兩人榻前如何,南風院一角的屋內氣氛卻是不太平和。
此房並非對外的房間,根本就是給景家或是南風院的人內部所用。而現在這房間正是給景家大老景煜臨時來芳樂當辦事所用。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景煜眼瞎的關係,這房裡面擺設簡單,一桌一椅,除此之外就無其他,就連桌上也只有文寶與幾本案冊,不如其他房間繁華亮麗,彷若是個剛建好的空房一樣樸實。
有人不太相信景煜是真的眼瞎,因為就算景煜眼睛如此,他還是可以如同一般人一樣批案改冊、行動自如,若不是他眼皮緊閉,還當真有人認為那眼瞎是假、那眼皮能穿透才是真的。
景煜桌前的案冊早已批註好,現在的他正靠在椅上休歇。景煜外在閒著,心中卻在盤算景家商務的各況,無論是景家名面上的帳務還是暗底下的交易,無一不是他時時刻刻掛心。景家能做實黃國四大富賈,景煜這實質的大老又怎會有一刻閒著?而現在他最煩心的就是現在南風院的事情,這也是他跑來這住紮一陣子的原因。
景煜休歇沒多久,就感應到門外有人緩緩靠近,片刻不等那人敲門應聲,就喊道:「進來吧。」
不等那人進來說些什麼,景煜靠在椅上的姿勢沒變,聲音卻是冷冷低了許多道:「我猜人沒抓著是吧?」
這進來之人不是別人,正是剛剛外出沒抓著人的琝陞。琝陞沒應答,僅然鞠了上身朝景煜敬到。
「連個小賊同夥都抓不著,我景家城主一個樣,連你也同個樣。」
「琝陞不才。」
琝陞人不傻,他不會現在說個什麼道理出來,就算他有理了,在景煜面前也不過是藉口,寧願忍個嘴舌一時罵,大不了省了皮肉痛。況且他看的出來,景煜現在心情貌似不錯,也無真得甚麼氣樣。
也不愧是在景煜身邊待過時日的琝陞,景煜現在心情的確不錯,對於琝陞現在沒做到的事情也沒啥意見繼續追究。
「反正他們頭頭跑了,你追到小賊估計也招不出什麼。」
「小人多事,在此多言問到,那這後事如何安排?」
景煜直起身子,面無表情的定在桌前。景煜臉上無明顯特徵變化,眼臉閉著也著實讓人猜不著是什麼意思,不過熟知的人都知道這是景煜在思考事情的樣貌,而不是甚麼發呆無神的樣子。這情況琝陞自然是不敢叨擾,只等景煜發言。
片刻,景煜緩緩令道:「我透查過這一年的帳冊了,好在少的只是票錠,沒缺甚麼大東西。但城主這過免不得,少了我景家一城收入的一時票錠,竟斗膽竄改帳冊,這少的票錠得他自個來收拾。」
這事現在整段看來也不過如此,可大可小、可繁可簡。
來由是此,也就是有個賊人不知怎地,很巧妙的持續從芳樂城主這偷了許多票錠,這被偷的城主竟然還過了一整年沒注意到,也算絕了!而城主注意到時,卻也不敢把這事上報,打算自個私了,把需上繳的帳冊寫個天災人禍,收入短少就算完事。殊不知,恰好景煜剛好在上個節日巡查至芳樂,又恰好賊人又再一次犯案,這短少一事,沒多久就被爆了出來……
而景煜那幾句話,就是景煜自個把這事情事情也完後了,至於少的票錠缺失給造事者自行填補。這安排就琝陞來看算輕的了,估計也就因為城主是景家人,景煜也不想做的太絕,要不通常這等缺失,就誠信為主的景家來說,不少個幾塊肉都不為過。
琝陞看得如此,景煜想的卻不一般。
景煜不怪城主多少的問題在於,這偷錢小賊就景煜來看不太尋常。
首先就有能耐偷景家錢又能安然而退的人就很不一般,要嘛見世多廣不為權貴、要嘛人傻不知情,而就只偷城主一家票錠來看,顯然是前者,且有意為之。
二來這賊人很是聰明,偷也只偷票錠,不偷其他神寶異物,且是打定了這個錢財定是追不著自個,而就景煜查來,芳樂周邊也確實沒什麼大量金流,這偷竊票錠必然被這賊人流向遠方,一時半刻是查遍不著。
三來也是景煜這幾候才得知,這賊人貌似不是人種,似是人外異族。然而芳樂商港流物龐大,雖少有異族人外入城,但似人族類不特意張揚,或是改個外貌遮掩入城也並非難事,這幾日封港探查城內竟也查不出個所以然,顯然這賊在芳樂有點門道,且熟知芳樂大小各處。
這事情景煜想來短時內也不是易解,想來這賊人如此有能也不會只盜一時。景煜也只好留個後手,等往日再來芳樂收網就是。
而這琝陞也是景煜調派放這的後手之一,且是口頭道道,不多加責之。
「沒事就這樣吧。我已信城主歸來,你來在這且歹看著辦。我再待個幾日就要回綠玉堂。」
「遵意……」
景煜眼睛見不著,但他聽得出琝陞並未打算離開,且語氣貌似有其他事情要知會。
景煜不耐道:「還有什麼事情?」
「不久片刻,有人在南風院這有些唐突,雖這人不顯揚低調,但就小人來看……貌似在打聽大人去向,且似乎知道大人就在芳樂。」
「哦!還有這事。」
想打聽景家的人很多,但特別指名要找景煜的人很少,要嘛不夠資格找他、要嘛根本不知道景家當家是誰。這樣會特意找他的人,想來別有目的。
琝陞見景煜有興趣也就沒隱瞞,把來人名字給報了出去。
不過景煜一聽之下,卻是根本不認識也沒印象。
「云丘號,耿菽?沒聽過。丘字號的船隻,東丘人嗎?」
「這幾年剛做起來的採貨人,就這資料上來看,是東丘人。」
景煜想了想依然是不知道,東丘的幾個大老闆或是頭幾位商家,印象中沒一個是姓耿的年輕人。而云丘號,這船隻貌似也不是送什麼大物件過,景煜也是沒什麼印象有接觸過。
「他人現在還在南風院?」景煜想了一下後問到。
「是,聽聞院內醫太說過,貌似要待個幾日。」
「這跟醫太又有何關係?」
「耿總身旁陪了個旗總,身體欠樣。小的自主託了醫太前去。」琝陞把在路上遇到耿裴兩人的事情給說了一遍,順道也把旗總這人的印象也輪了一遍。
景煜想了想後,突然確定了什麼一樣,朝琝陞問:「這身旁旗總是否姓裴?」
琝陞雖不知道景煜是如何得知,但還是回話應是。
景煜又是一陣靜止,手指卻是不同以往,開始不耐煩得拍打著桌面。這一敲卻是敲了數刻不止。
原先琝陞以為景煜要開始一連串的吩咐。然而當景煜開口時,卻只道了一句「這事情我自個處理,沒事就下去吧。」
琝陞不敢怠慢,既然景煜如此,那他也沒道理繼續待著。鞠個身後,琝陞就靜靜離開了。
琝陞知道,當景煜會有如此吩咐的態度,那自然是有什麼事情出現,而這類事情通常都是大事。有時候是內容很隱私,不方面告知下人處理;有時候是票錠很大方,不方便散著分。
而這情況顯然是後者,不過景煜想的很多,有些事情不單單錢的問題,要不然也不會叫他退下。
等琝陞完全離開後,景煜從桌前的幾個冊內拿出一本稍早前才批好的本子,這本子是芳樂景家的各個店鋪票錠流向統整本。裡面有註載各項事務,除了各店鋪買賣了什麼,當然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細項。
其中幾頁是景家其中一個票莊的內容。這票莊的金流龐大,難免林林總總寫了一堆細項,其中一項景煜特別有印象,雖然這內容起初看似有些荒唐,不過剛剛琝陞提到那個旗總的事情,不免讓他在意起了這條細項主題──「委,北嶺裴家裴束修消息」
委託找人不奇怪,然而這則委託無論是委託人還是解託人都很是奇怪。
解託人是不具名的張氏,怪就怪在於,他雖然提供了裴家裴束修消息來源與去向,卻拿不出證據道明消息的正確與否,也因為如此這票莊並沒有把委託的全額都付給他,僅依委託人要求給了個消息金錠。然而這所謂的消息金錠卻是給的甚少,甚至連委託全額兩成都不到。
而說到這,那委託人就更怪了!一開始看到這則委託,景煜以為會是北嶺那個裴武大老爺,畢竟前陣子裴少跑出來的事情黃國無人不知。然而這冊上寫的委託人卻是一個代稱,既不透漏姓名、也不透漏來意。會用這種方式不留名字的人,顯然是不想暴露身分,就裴老來看,他都肯用武商裴印廣發找人,委託找人卻不留真名?這委託人顯然不是裴家老爺,定是有其他人再找裴家少爺,且就內容來看,這人要嘛認識裴少、要嘛與裴少關係不淺。
景煜用這個代稱又找到了冊子上另一個他不留名的委託,這則委託並沒有成立,而是寫在冊上給上級批註,而又恰好給景煜改註到。
這則委託不一般,不是正常的交易項目,也因為如此才會暫時未成立交由上級批造。
這則委託,早些時刻景煜是註寫了否定。不過他現在看了一下後,覺得很有意思。至於要不要改成立案?他打算會一會那個耿菽再做打算。
只見景煜在那條「委,贈張氏供解消息者,裴君烏酒。」給註寫了一字,緩。
7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HPf6f43Ze
7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C3VaRuWxyZ
7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5CxUasVn8d
暫且不談這委託人是誰,這供消息者說的張氏自然是云丘號的張凌山。張凌山下了船後,自然是跑去找供消息賣買的景家店鋪提供裴束修的消息。然而他固有消息,但口說無憑,也無證據說云丘號的旗總就是裴束修。鋪堂的負責人也見為難,這消息給得不清不楚,著實難辦。尤其這委託人開的條件表面上雖是要裴少消息,是私底下給的細項卻是一條接著一條,而這張氏這無證據的說法,卻剛好不搭這幾條的細則。委託人要確確實實的確認這人是裴少才可。
無奈負責人只好請示上層託人去找人確認,這不剛好琝陞大人在外面抓賊人,藉這理由堵人、順道在外收查,且不一石二鳥?這才有了琝陞堵人進旅店、又刻意引入南風院待著這事情。事情雖然看似事事如意,人找著了、也看到了,但難就難在芳樂根本沒人見過裴束修長什麼樣子?
好不容易找來了一張前段時間廣傳的「尋人 武商裴印」,但依然問題多多。一來不可能當著人的面對照比對,只好憑著印象去對照傳單、二來這傳單也不知道復刻了多少次、傳了多少回?有些地方早已不像當初的原畫,而有所偏差。琝陞與見過裴旗總的幾個下屬,看了這傳單,楞是覺得好想哪裡有點像、又好像哪裡不太對,一時間也不敢妄自下獨斷。
最後無奈之下,這店鋪的負責人只好把這事記下,卻也不敢把委託全額都供給提供者,僅私自貼補不虧本的價格給張凌山。怎料這事情都還沒個完,也不知道委託人哪來的消息,又委託了另一筆「贈烏酒」事情。這所謂得「贈酒」可不一般,委託人若不帶酒卻要贈酒給某人,這是一種只有特定幾人才知道得景家暗號,「贈酒」的暗號意思可是殺人委託!「烏酒」可是不求過程只求無全屍的意思。
這彷彿人不再現場卻全然知道現況如何的奇怪委託人,也才有了後續立定不了的情況,最後呈上給了景煜批註。
另方面,張凌山那邊倒是老大不滿意了。
要不是有消息說到了芳樂會給大筆錢財,他平常才不會上耿菽這種規定頗多的正經貨船。當時張凌山在東丘好不容易找了一夥人陪著上船作掩護,怎知道這找人掩護上船的錢都先給了,到了芳樂卻是沒拿到預定多的錢財,這不連發出去的錢都賺不回來?
張凌山當下就在店鋪吵了許久!然而無論他如何去吵,卻是拿景家店舖不理睬的態度一點辦法都沒有。人家不理你就是不理你,全然是按理在辦,張氏拿不出證據說明來源消息的正確性,人家還肯給你點錢就不錯了,哪還有什麼腳站得住?
張凌山吵到店舖關門了這才怒沖沖的回到自己在芳樂的小據點。
這小據點只得一兩層的小房,一樓租給人開店鋪,二樓就是平時張氏來往芳樂時下榻住宿的地方。
現在二樓這房除了剛回來的張凌山之外,還有他那名義上的小叔張亦宿與阮堯。
這幾人混在一起到不怎般意外。意外的是,居然還有個外人在!這外人頗為古怪,人在室內還戴著斗帽遮著頭,一身素裝沒啥特色,但那褻衣衣領不知怎的老高,高的那人都把它拿來遮住自己口鼻。這衣裝不說別的古怪,拿去外邊給人看就是一副遮頭遮臉的可疑樣貌。
ns3.144.70.25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