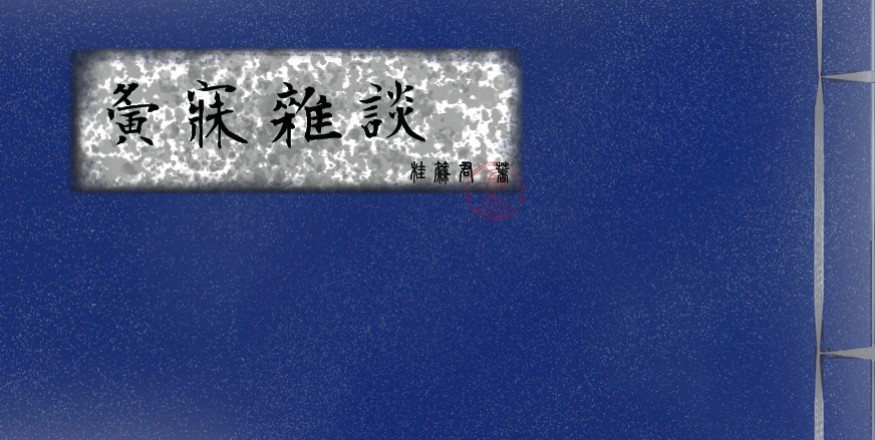8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bldvqhKNE
張凌山一路吵到了近日落,吵到店鋪都要關了,這還沒吵個結果,就被人趕了出來。現在一回到自己下榻的小房,上樓開了房門,一肚子氣又升了上來。
房內待著阮堯與張亦宿兩人。原先這個小叔是待在這鋪等他領錢回來,怎知現在回來就看到他與堯子在房內交歡在一起。張亦宿不知道是不在意還是沒聽到,就算張凌山開門走了進來也沒有想要停下身下的衝勁,頂的是阮堯腹下濕漉片片。
阮堯這幾日被他們在船上玩到身子差,照理說是應該留在云丘號上待命才是,怎知被亦宿用什麼手段給搞下了船。
張凌山看阮堯身下那勢頭與叫喚,顯然是與亦宿歡快了許久。
兩人在這搞歡也就算了,這頂多讓凌山不快。真正讓張凌山氣上心頭的是在一旁坐著的蒙面人。
這人蒙著嘴臉、戴著斗帽,雖然讓張凌山不認得這個人,但是這個座派很是讓張凌山熟悉。
自個在東丘接這倘錢財時,也是有這麼個藏頭藏臉的人。這個人肯定不是在東丘的那人,但是要說沒關係,凌山肯定是不信。
張凌山先不管一旁還在忙碌進出的小叔,他用大過阮堯浪喊聲響的聲音,明知故問得朝那蒙面人吼道:「你是什麼人?不會是排隊等著上堯子的人吧?」
那人站起了身子,起身朝張凌山報了個名號。果不其然,與張凌山想得相當,是跟東丘同一掛的人。
一確定那人來歷,張凌山開口就罵了聲髒,又道:「你們說話不算話阿!說好事後給的錢,我根本拿不到。照你們說的那樣做,我剛剛才從景家店舖出來,實際拿到的錢加你們給得頭款,根本就不足你當初說的一半!」
蒙面人貌似不意外,聽到張凌山這樣說,他只是從懷裡丟出了一個包。張凌山拿起打開一看,裡面錠數不少,算了算愣是比當初說好的錢還多了不止一倍。
張凌山唾了一口,心裡有些不是滋味,他特別討厭這種人。
張凌山討厭的不是那蒙面人的態度,而是討厭那種抓拿人心狠準的行為。
這人肯定很清楚自己不會為了多拿那點錢就高興。
「你又想做什麼?」
那人聲音乾啞的道:「回程再幫我辦點事吧。」
這人也很清楚只要對自己拿足夠多錢,那多半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蒙面人沒繼續多說什麼,僅是看了看旁邊還在瘋狂運動的兩人一眼,顯然是不想走漏太多風聲。
張凌山看著還在上下磨墨的兩人也很是不客氣,抬起一角腳就往亦宿肩膀上踹。
「你他媽的還要玩多久!」
這一踹非但沒有把兩人踹分開,反倒是讓張亦宿原先壓伏的身子重心往後,屁股一跌身子一立,坐了起來!
張亦宿突然被人一踹,重心不穩的往後跌坐了起來,這下頂多讓他驚訝剎那,卻是沒嚇著多少,然而身下阮堯可就差得多了。
張亦宿這座起身子卻是沒把孽根給抽出,反倒是處著阮堯的臀腿,自個雙膝一曲、腿腳一撐,讓還癱躺在地面的阮堯給一起頂了起來!
阮堯被頂起了身子,猝不及防的全身重量壓坐在張亦宿的身上,阮堯下腹部突然一陣腫痛,自身穀道內的那個外物被頂到更深處,彷彿是脹大了數倍一般,原先長時間下來已經習慣的肉壁,頓時又是一波新意,讓阮堯穀道受不了的痠麻收緊且不自覺得輕鳴數聲。剎那阮堯一個不穩,又是往下坐了數毫,碰不到的肉環節點頓時被戳了個刺,隨著那頓刺擊,阮堯感覺到飽滿溫熱的液體在自己穀道肉節內竄流,自己也忍不住脬腎之癮,淡黃又燥騷的液體從自身陽根噴濺而出,弄得自身與張亦宿的腹腿之間都是陣陣濕腥。
張凌山見狀,也不管兩人玩得多開,喊了一句:「爽完沒?老子要跟人談事情,爽完就給我滾出去!」
阮堯貌似回過神,率先起了反應,想站起身子離開。怎知自己雙腳剛立定,臀肉下意識的一出力,穀道又是一陣收縮,還頂在內的燙棒自然又是回饋的貼了上去。這讓阮堯又是一陣痠麻,腿腳忽然無力又是跌坐下來。
想要退的,反倒是包的紮實,該退出去的沒退半分;不想出的,卻又是頂的脹熱,不該出來的出了許多。
張凌山不管兩人如何,一腳更是用力地踹下去,嫌棄自家小叔還在褻玩。
也不知道這腳是踹對了點還是痛處,張亦宿這才回過神來。他聽是聽到了,可是不管張凌山要跟誰談事情,反正有人在旁邊看著他也不怕。張亦宿當下孽根還是不拔,一個蹲起,雙手往阮堯臀肉一抓,頂著阮堯往自己身上一靠。蓄力站起後,靠著自己雙腿間的堅挺,戳提著阮堯身子就往外走。
張亦宿對著靠在自己耳邊的阮堯悄聲說道:「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張亦宿邊說邊頂著阮堯往外走,邊走還邊時不時故意抖個腰腿,讓阮堯身子忽沉忽伸的穀道緊了又緊,自個孽根是進進又出出。
兩人出去關了房門,然而還是可以透過緊閉的門扉聽到外面傳來的細微聲響。張亦宿的狂言、阮堯的浪語、兩人的肉體拍撞聲響……
張凌山皺了皺眉,朝那蒙面人道:「我看兩人也沒心思偷聽甚麼的,你有什麼要求就直說吧。」張凌山說完,又在手上惦了惦那袋錢道:「多少錢做多少事,辦不來的我也沒辦法。」
蒙面人聽了聽外面兩人的動靜,面色沒多大變化坐下來就說道:「景家那邊也是我們誤算,少的那筆錢就算我們補貼你的,但接下來的事情,還是得你去景家接。」
「錢就這個數?」張凌山確認道。他可是要估好做這筆生意究竟划不划算,如果要求的太過分,那他寧可把這筆多的錢丟回去。
「除錢袋那筆錢之外,你能做得多好,看景家對任務的完成度判斷會給你多少是多少。」
張凌山聽完衡量了一下後,轉頭又問:「你們委託景家什麼任務?」
「一個送酒的任務。」
張凌山也不是孩童,放卷走私都敢做過了,贈酒任務也不是沒聽過什麼意思。
不過這活張凌山可不想接。
張凌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也知道這樣做會讓其他人有怎樣的後果,然而那不關他的事情。他放卷讓人還不出錢,散盡家財、流離失所,但那與他何干?他走私讓人沉迷淪陷,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但那與他何干?
張凌山覺得他這麼做是為自己謀求活路生存,其他人要從他這拿取什麼,就該付出怎麼樣的事物,至於他們拿取的事物要如何使用,那是他們的事情,他沒有必要負責。
但若是要他自己去做下手,殺人滅口什麼的,大可不必。
「你以為我不知道送酒是什麼?你很清楚我張氏從不接這種贓活,這我可辦不來。」
「我的確打聽過你們張氏不做這種活,但你經手的其他物業貌似也乾淨不了多少」蒙面人語焉不詳,意有所指。
然而張凌山也不理搭他,想看看他還有什麼說法。
兩人靜默的可以,門外持續不停的喘喊在兩人間顯得特別突兀。
過沒多久,張凌山見蒙面人沒說話,開始盤算錢袋,打算把多的錢掏出來還蒙面人。這時蒙面人才動了動身子,又拿出一布袋推到張凌山前面。
不等張凌山拒絕,蒙面人道:「賣刀人不使刀,買刀人使刀弒。賣刀人明知刀會傷人卻又為何賣刀?」
張凌山摸了摸那布袋,裡面除了金錠之外,還有個小方盒。張凌山在蒙面人面前把盒子打開,布絨內裡的中間裝著一粒不小的藥丸。
蒙面人沒多說什麼,只繼續道:「你手底下的買刀人不少吧?若這刀非刀樣,買刀人又如何知道他會傷人?」
張凌山唾了一口,心裡有些不是滋味,他特別討厭這種人。
討厭那種對人心掌握分毫不差,又善於利用這點的人。
重點是自己明知如此,卻還拒絕不了。
蒙面人看張凌山默默收起袋子,知曉事情已成一半,起身走之前還朝張凌山道:「事成後那盒子可別弄丟了,到東丘後,拿到盒子找我們還能再換一袋。」
張凌山只覺得這人真是錢多到沒話說,也不知道打哪來的,定要那裴小輩性命。
那蒙面人站起身走向門口,卻又聽聞門外那春艷聲響。蒙面人嘴邊切了一聲,竟有些鄙視的轉過身朝窗櫺走去,看來是打算從窗口離開。
蒙面人一腳站在窗台上,回過身朝張凌山道:「看你合作人的份上,跟你說個一聲吧。」
蒙面人用下巴朝門外走廊那點了點道:「那人吃了通麻丹對吧。我勸你們,那東西還是少碰為妙。」
張凌山眉頭一挑頗為意外。通麻丹這玩意照理說很少人知道的,頂多在幾個人之間流通而已,怎麼這蒙面人很了解一樣。
張凌山說道:「賣刀人不使刀,就算使起刀來,也不過是小試一番。」張凌山言下之意是自有分寸。
蒙面人可不覺得,對於這通麻丹的了解他可是比張凌山還多。
「通麻丹說穿了,也不過是禁藥罷了。」
「用量適宜,禁藥又何妨。」
「你根本不了解這東西,哪天你自會知曉。我勸言於此,好自為之。」蒙面人語畢,翻身就往窗外跳去。
張凌山走去窗邊,窗外昏暗也見不著什麼人影,更別提甚麼蒙面人了。張凌山對於蒙面人說的禁藥問題也不當一回事,反正這通麻丹自己也是當春藥用,無論外用內服也沒遇過什麼大事。這藥也在其他人之間流通,更沒聽過其他人有發生過什麼事。
「怎麼,人走了嗎?」張亦宿默默一人開了門從外面走了進來。
張凌山沒回頭依然看著窗外,手上拿著蒙面人給的那小盒子想著各種問題。
「你聽多久了?」
「我也沒多忙,可從頭聽到尾呢。」張亦宿從旁邊拿了個布開始擦身子,又問道:「那藥有問題嗎?」
「我哪知道?這藥流通很久了,也沒見有人抱怨過。」
「我這問題,你看算不算呀?」張亦宿笑笑地問道。
張凌山回頭一看,只見張亦宿裸著身子站著那邊,而下半身的陽物仍是那頂朝天的樣貌,看那時不時隨著張亦宿呼吸而顫動的樣貌,顯然沒有半分疲軟樣態。
當然這不是藥的關係,張亦宿只是開玩笑罷了,這點張凌山也知道。
「你還沒玩夠嗎?」
「人家都昏過去了,我還要玩什麼?」張亦宿隨意找了個空座了下來,竟是開始自己勞煩起來。
張凌山也不管他,兩人都見過對方玩過什麼,這點東西也不過爾爾。
張凌山嘆了口氣,拿了那個小方箱想了許久。一直到張亦宿自個下身都忙退疲軟了,愣是沒有一個結果。
張亦宿開始穿起衣絝邊問道:「送酒這活你有什麼打算?」
「錢都收了,還有什麼打算?」
「那個裴小子值這麼多錢?」
張亦宿這話的意思是,這筆錢真的夠他們鋌而走險幹這件事?甚麼活都有風險,錢越多的活顯然越危險,要不然誰會平白無故託人下手。
「當然值得可不少,我估計蒙面的這些傢伙也是個狠人。」
張亦宿沒想這麼多,一開始在東丘接活的也不是他,自然就不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我聽船上的人說,這裴仲是耿菽日清冥的舊識,來之前是在北嶺做隱衛對吧。」
「所以呢?隱衛很值錢?」張亦宿只覺得這職雖然錢多,但總是死的莫名又早,就算之前張凌山跟他說這人有多值錢,張亦宿絲毫不覺得有哪裡好。
「我說如果裴仲這裴姓沒改過,那這隱衛肯定是來頭不小。」
「耿菽不是說他是那個裴少爺的隱衛?來頭當然不小。」
「能這般了解一個隱衛的走向、又能各處走跑的人手、還有眼線可以看照著我們的人,我估計蒙面人那群分子也是裴家的人。」
張亦宿對於張凌山的分析沒什麼心思,他只在乎這錢賺得安不安全,他可不想要跟著人賺錢,賺到命都沒了。
「就算蒙面人是裴家人派來的好了!我也沒興趣知道,所以這活你究竟要怎麼做?我可不想要下這手喔!」
「自然是不會叫你這浪狗去做這個細膩活。」張凌山在剛剛想了許多,自然是考慮到了張亦宿這點。
不過一說張亦宿這點,張凌山突然有了一個想法。
「亦宿,我說你剛剛在外面聽了全部對吧?」
「這又怎麼了嗎?」
「堯子那傢伙有聽到嗎?」
「……他忙著享受應該是沒聽到吧。」張亦宿好像有些猜到張凌山要做甚麼。
「加上你剛剛那次,算上分利,他應該還欠我們不少吧?」
不等張亦宿算好多少,張凌山早就考慮好什麼了。
「我這人很好心的,幫我什麼忙幫得好的話,欠利什麼得一筆勾消也不是不行。」張凌山邊轉動著手上的小方盒邊不懷好意地說著。
8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QFDADFOdy
8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GDxbYNRtZ
8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zyRJfUDQP
束修躺在榻上,身上剛被耿菽蓋上被單。他嘴上雖然說了要先睡,然而剛剛耿菽最後那摸身子的玩笑,再加上醫太那些言論,現在腦中滿是各種慾想,哪還有任何睡意?
蓋在身上的被毯沒讓束修覺得溫暖,反而是讓他覺得身子更熱了。
束修總覺得剛退燒沒多久的身子彷彿又開始燒了起來,不過身上蓋著被子的自己卻是不敢多動半分,就怕耿菽發現自己根本沒睡,身下還有精神得很。
沒多久,耿菽貌似擦完了澡,束修只感覺水盆的水聲在一陣稀哩聲響之後,身後的人就沒什麼太大的聲響。
突然束修感覺身下榻板一陣下沉,想必是耿菽也上榻來準備睡覺了。除了榻板的震動之外,束修還感覺自己整個背後貼上一陣觸感。不知道是不是耿菽剛擦完身子的關係,背後那觸感柔軟又有些冰涼,讓束修燥熱的身子緩緩退了一把火。
這沁涼的感覺讓束修不自覺的安下心來,緩緩地起了睡意睡去。
然而這晚睡眠卻是沒有讓束修一覺到天亮,不過夤夜過半,束修卻是被自己給熱得滿身大汗醒來!
束修緩慢坐起身來,就怕身後的耿菽也會一定被他弄醒。怎知束修慢慢坐起身子來的時候,回過身透過窗邊簾外的月光悄悄窺看,這才發現他背後得哪是甚麼耿菽背貼著背,而是用被單捲起來的一長條「界線」。隔著這條界線,耿菽在他另一邊睡得正熟,身上卻是甚麼都沒蓋。
原來束修剛剛睡著前,貼在他背後的根本不是甚麼耿菽的背脊,而是這條捲起來當邊界的被單,一切不過是他想太多。
束修靜靜的把自己身上的被單給拉到一旁,在悄悄地跨過耿菽的身子下了榻。冒了一身汗的束修哪還有什麼心情繼續躺著睡覺,自然是打算把身上的汗水處理了先。
束修在房內繞了一圈,然而屋內太暗,僅有月光與房外的廊燈,束修摸黑了一陣子還是找不著他想要擦身體的布巾。反而因為自己在半封閉的屋內繞來繞去,身子沒乾多少卻是又留了一些汗。
最後束修放棄了繼續在屋內無意義的尋找,反倒是想到另一個辦法。既然這裡有窗,芳樂又靠海,那坐在屏擋那邊的美人靠上,等風吹乾身子不就得了?
雖然是窗邊的美人靠,但不知道是不是南風院怕危險,那窗邊美人靠的高度卻是不低、弧度也沒多斜,若尋常人坐在邊上時,也只有胸口才超出杆邊。雖然杆邊很高,但是這不影響束修趴著打算吹風的意願。
束修身上穿著褻衣褥褲,在怎麼高的杆邊,好歹有個欄能透風,總該不會有多麻煩。
束修靠在邊上,為了不讓月光透進太多照亮屋內,束修自個把身子鑽出簾席之外,雙臂靠著杆上,等著晚風吹乾自己的身子。
一探出身子的束修,最先享受到的不是甚麼晚風徐徐,而是窗外之窗的吟聲夜語。
且說南風院營的是樓欄,晚上鮮少有人如同耿裴兩人一樣單純來住宿的,外食不在話下,內用自然是忙著幹活,免得了錢。
這不說束修住的間房這窗多高多低,恰是中間不上不下。這些聲響並不大聲,透得出簾子也透不到人家窗內。但束修這身子一鑽出簾外,多半是聽的三兩跑不掉。
上層見不著的,隨著夜光傳來陣陣嗚鳴、下頭眼見著的,透著簾影演著慨昂武打。
不只近處如此,遠遠的束修貌似還聽到了各種不同的聲響。束修身子沒吹乾多少,倒是各房的聲響聽了不少,等束修反應過來把身子探回屋內,自個下身早已要脹不頂的在那蠢動。
且不說這些淫聲浪話,束修這間房的對外窗是層樓之中,雨水甚麼的根本吹不進來多少,更別提什麼晚風了。
然而這樣呆站在有些封閉的屋內等著身子乾,肯定是要花上許久時間,再加上這靠窗處的各種聲響,讓束修害羞地有些不太敢接近。束修最後左思右想之下,悄悄的在屋內找了盞沒點火的空油燈往房外廊道走去。
ns3.144.127.18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