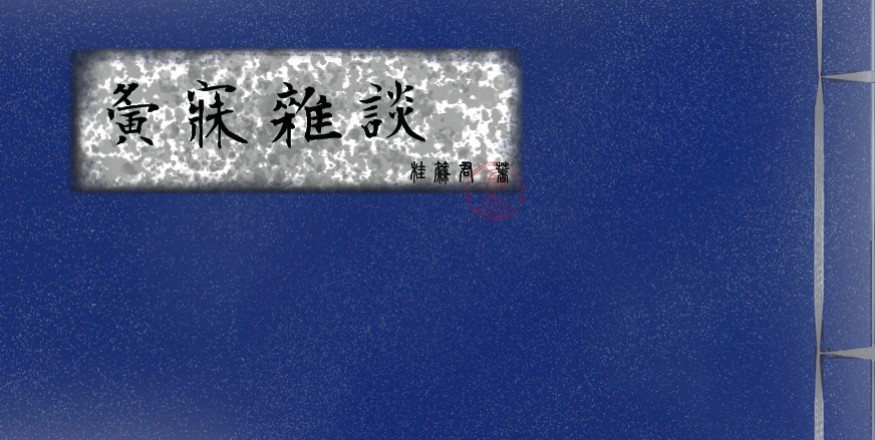跟著隊領的腳步往港區的轉角走去,在那的是一間間蓋在邊坡上的小木屋。
束修後悔了。這地方要說的上是清廁的話,也太簡陋了!仔細看的話,這屋頂還是由乾燥樹葉的枯枝所堆疊而成。不像常見的草屋一樣,乾枯頂通風不易潮濕、木芳強烈也不易藏蟲,但也代表著它很開放。
束修不用進去就知道它的確很開放。若是站在邊坡的上方,肯定可以隱隱約約的透過枯支間窺看裡面,事實上,束修的確看到有幾個峋嶼的小朋友在那邊坡上歡鬧玩耍,無論小孩是有心還是無意地在窺看,這都令正準備要上廁所地束修非常尷尬。
「裴總,我就在外面等你,小心地滑!坑不深,但這摔著出來也不太好看。」
頂著下屬關愛的目光,束修只好步入清廁,關上隔間門。對了!這門還不帶鎖的!自個進來還要拿個小石擋著,避免被下位要上的人誤闖。
束修看了看被石頭擋著的門口、又看了看上方那還透著絲絲陽光的枯枝頂,再轉頭看著那個坑洞,洞口下的確如同隊領說的一樣不深,但這也代表著坑低回彈大,好在束修不是真的要上廁所,要不這環境他還寧可不上。
束修找了塊還算乾淨的地方坐了下來。航行雖然不算輕鬆,但有跟著耿菽,整趟旅程也算順利,從離開北嶺到東丘,在一路到峋嶼。雖然還沒到目的地的南洲芳越,但這旅途的總目地要到何時何處?束修卻沒想這麼多。他一開始只想離開北嶺、離開裴家、離開那生煩的大院。但離開後要做什麼?之後要何去何從?還會回去嗎?他真的沒考慮這麼多。或許一切的一切只是他自己的一種逃避罷了!逃避各種他不想接受,卻非得接受的未來,不是對裴家沒感情,而是對裴家的種種過往與傳統壓的喘不過氣。一開始的逃避或許是因為好玩,現在的逃避卻真的是為了自己?
唉……束修嘆了口氣,總覺得現在想這麼多,好像也改變不了甚麼,逃都逃了,人也不在北嶺裴院。
沒過許久,也不知是一時放鬆座太久的關係,亦或是在清廁待久了的緣故,本來只是編逃跑的藉口,現在隨著有些發脹的下肚,還真有些尿意。束修整了整裝,開始在坑板前蹲座了起來。
一靜下來、沒繼續細想心事的束修這才察覺,除了在上坡邊旁的孩童玩鬧聲之外,這嘻笑聲中還藏著一股奇怪的聲音,幽幽咽咽、矯矯細細,有著人聲、有著水聲,彷彿刻意壓低聲響的在這附近哭泣一般。
「……嗚嗚……」「吚吚……」
由於地點特殊,神怪異誌聽多的束修難免多想了甚麼,從小至大雖沒親眼見過,但真自己碰到難免還是會驚滯個一下。待平靜下來後,束修開始去聽那藏在玩鬧聲後的細響,專心到連原有的尿意都洩完了都沒發現,就這樣維持著空蹲座的下半身在那。
幽咽的聲音沒有改變,在束修專注的傾聽下,甚至覺得更為清晰!
在一次孩童大喊玩開又突然寂靜的那剎,束修終於聽清楚這聲響是在說些甚麼。
「好、痛,我不要了……」「東西給了!現在才不要?」「你騙我、根本沒有舒服過。」「你的小花柱好像不是這麼說的……」
瞬間的驚悚變成尷尬,這下不是甚麼神怪異誌,而是艷文歡詞了!別說甚麼事情、什麼活了!在做甚麼事?想都不用想,自然不在話下。別說是街頭說書,這根本是現場體驗,堪比那些樓欄青臺的荒淫選舞,雖不是男歡女愛、是雙龍並柱,但現場聲響詞句不差於文本戲曲,現在就只差那畫面罷了!
束修心中震驚歸震驚但仍然停不下偷聽的行為,且越聽越是清晰,越去想像那交歡畫面就越是專注!就連原先那上坡的孩童嬉鬧聲響,也無法蓋過那些刻意遮蔽的聲響!
「不、不要、嗚……」「你可以哭大聲點,讓外面孩童都聽到!」「吚嗚……」
隨著男子半威脅的口氣下,原先的啜泣與對話逐漸變小變少,但水聲卻是依然存在。
像是布匹沾點池水拍過、又像是口唇從果莓表面舔抿一般。這時束修才後知後覺的了解,這水聲根本不是甚麼清廁裡的大小落坑聲,這根本是兩個體塊在面接面的碰撞分離罷了!不知隔牆有耳的兩個塊體,依然有節奏的帶起漉漉聲想,聲小卻也確實的傳入束修的耳中,撲碌碌得傳來放闢邪侈的響擊,帶起了束修星星慾火往腹下奔去,讓束修不自覺地燎起玉體、挺而豎直且自不查。
如同海浪拍擊沿岸一般,濕潤的水聲不止地拍撞,夾雜在其中的還有一絲絲哽咽與獸鳴的低語。
束修邊聽邊意想著種種畫面,扶著牆柱的一手,竟也下意識的離開牆體,轉往自己雙腿間摸去!隨著荒淫的潮水聲開始順著莖節滑動起來。
沒過多久,隔間的沉穩浪潮卻似鯨蛟鯤獸突現一般,浪起水破、風吹岩碎,潮起快而速亂、氣落慢而單一,浪潮原先的穩健早已消逝得不見蹤影,只剩亂水在岩間亂打不止,求快求力的四處打擊,隱忍的氣息也只剩忍讓,堅定的岩體任由潮水拍打,任由自己的岩間的絲絲泉水,隨著拍擊滴滴外漏,隨著力道聲聲碎淚。
隨著海象的異變,束修也加快了雙腿間的航程。隨著巨浪波波的拍打,抓緊了力道,次次的往那制高點前進。
誰知忽然間外一聲聲響,打斷了束修想前往的終點,也讓那交合藏隱的浪岩帶來最後一次的潮襲與噴發。
「抱歉!裴總,你好了嗎?我覺得搞不好耿總會想要衝過來催我們了!」
清廁旁的浪岩最後隨著一聲帶有力度的低吼獸息之後,海面就像風暴過去一般,僅剩平健沉穩的呼吸聲與止不住的喘息在束修耳中蔓延。
束修在心中暗罵一句髒話!自個瞎忙了一陣,感覺就快到了就被硬生生打斷,這感覺很是難受。轉頭隨口對著門外回了幾句,又低頭望了望自己,原本隨著興奮而聚集在熱柱的紅液,現在已漸漸退去,手中原先的奮發以開始轉態軟化。
只剩自己歡愉時偷偷提前吐出的一絲灰白,以及手中帶點柔魚味的半黏液還記錄著曾經航程的快捷與高猛浪潮。
束修也不是很了解,這樣弄了又不弄出來是否真的會傷身,不過在怎麼樣也不能讓人久候下去,束修隨手外衣長袴穿穿、紳帶系了系,就打算往外走。不料,這立柱快意沒出、半硬不退,就算褻褲、外絝穿上,這鵬發還是把衣絝頂個凸起,若紳帶往腰間一系,那蹊間更是明顯。
等了許久的隊領,好不容易盼到裴旗總出來,但這姿態……
「裴總,你……這是怎麼了?」
「沒事沒事!就是肚子還有點疼,不礙事,走走就好。」
束修一走出清廁,整個身子自然前屈,雙手交於腹前,外衣袖自然垂下的擋住了半身。隊領一看,乍看認為束修抱腹欠樣,殊不知只是個人興奮未退罷了。
束修也不管隊領怎看,誤會更好。一出來後找個手檯,掬了把水往臉上潑了潑,好讓自己可以更快的冷靜下來。一旁隊領急著催促裴總快點,提醒他倆早耽擱不少時間。
束修才不理這麼多,他只忙著讓自己冷卻並讓下身早些消退下來。旁人催促他?他在裴院早就習慣了!你怎麼催都沒用,除非裴老爺掄著拳頭走過來才有用。
啪刷一聲,清廁一旁的門扉打開,走出一褐膚青年,身形不高有些纖瘦,面孔深邃、形好端正,若稍作整潔一下,會是一個不錯看的青年。
青年一手揉搓著大腿股,一手上臂抹擰著鼻腔,雖然臉上並沒有特別的神情,但雙眼的紅腫與面頰的細微淚痕,在束修眼中卻是異常清晰,看青年的動作貌似有意遮掩,束修也就沒理會他,隊領忙著在一旁催著騎總,看了一眼發現是當地人,也就沒多加關注。倒是青年自己一出來看到兩個外地人在這,卻是驚的同手同腳,面頰變紅,也不管身子哪裡疼,衣物還有些凌亂不整,就快步地往一旁跑去。
束修甩了甩臉上的水珠,撇了一眼往身後的清廁看去,心中暗慨著。
這人也真是心機,先不論他在此處所做之事,但他肯定知道此處上坡有孩通嬉鬧之事,再來隊領在外一喊也一定知曉此處並非只有單獨他兩所在。這人若說不是刻意在旁有人的時候為之,束修絕不相信。
爾後,這人現在還不出來,想必是為了避開他與隊領兩人的目光,與青年前後分出,避嫌避癖。
束修雖好八卦軼事、但絕非好事之人,對於他人的行事作為並不想管太多。既然人家想避開外人而不出來,束修也不想在外耗著等著他出來。待身子退了些後,束修就陪著隊領往港務區走去,當然是在隊領用左探右擋的陪同下,以異常緩慢的方式前去。
只待清廁的周邊聲響又回如常安穩,躲在清廁內的那人這才出來。
束修只在隔間內聽到聲音,卻沒見到人,若這時束修在場,肯定會知曉這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該晚站在張凌山身後幫忙攙扶阮堯,且與凌山有著相似血緣的張亦宿。
亦宿不像凌山一樣愛張揚,總是陪著凌山一旁處理著各種大小事。但知情人士可不會小看這個時常站在凌山身後的男子,亦宿為人處事低調隱蔽,但真脫離凌山自己幹事時,無不慘忍無情、無事不濺血濺肉。
外人不知,雖他常與凌山一起同進出一樣的窯子,且多半與凌山幹同檔事,眾人皆以為他張倆愛好男色,但不知的是這色卻各有千秋,凌山喜好挑軟的吃,不喜挑戰蠻幹,對方能自己跳下來為佳。但亦宿可不同了!就像現在,他一下船,只要還沒上工幹活,他定會找些雛好好犒賞自己,特別是那些不知人事的那種,要教、要哄,更甚是……要騙!
不過峋嶼本島要找男雛可不好找,本島多是女性,只逮找些棄窟的人來玩玩。本島棄窟的人多半無親無靠,要份、要地位都沒有,這種人隨便用些外地物就可打發人家,就算東窗事發鬧出問題,多半不是被人打得不敢外揚、另半就是自個也沒地方訴苦。
峋嶼本地人看不起,認為這些人作賤自己總向著島外人吃島內飯,峋嶼外地人也看不起,認為這些人沒峋嶼人風,既無岩島鬥心,也無本島育心,只當這些人是峋嶼貧民、只當這些人會乞騙討拐。
亦宿才不管這些道評關語。下船時,隨手拿了個浸過煉油、有些香氣的拋光圓木球,就把個棄窟子給騙來這玩。
現在的亦宿一臉若有所思地站在廁旁,心中想著凌山跟他說過的話,許多冒出的問題讓他百思不得其解。
數日前,那時凌山與亦宿才剛上床禢沒多久,躺得很開放的凌山悄悄在他耳邊說著這句話。「那個裴仲可不能放過他,盯他盯緊些。」
現在看著束修與隊領慢步離開,亦宿怎麼看都看不出凌山看上這個裴旗總哪一點?
說外貌嗎?長得也不差,身子剛好介於壯碩與纖細之間,使的了力、受的了累,凌山或許看得上眼。說個性嗎?這點還看不出來,不過從跟他與耿總熟捻的情況來看,兩人個性或許有相似之處,但這絕不合凌山的喜好,若非工作需求,依照凌山個性來看是絕不想搭耿菽的船。
暫且不知自己大哥在想什麼,是想要個新玩具?還是想要個新合夥人?又或是下一個
商業目標?亦宿也只能做好自己的事,聽從大哥的吩咐,對這個新旗總多加關注。
8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a36RN8ApJb
8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164jyre0UX
8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fx5pLJdxE
轉到再也看不到的束修的位置,耿菽也只好專注於眼前的事項,雖然擔心再多也沒用,只能期望,這附近沒有什麼東西能引起束修太大的好奇心。
走出港口的停泊區,周邊多數為補給及維修的作業區,還有一些少量的店舖與商家,而在這尾端,有個特別注目的二層建物,這個建物就是港區的綜合管理處,也是多數航手們口中稱的港務區。
它不像這裡多數的建築是純木造再上漆油搭建組成,而是用石堆、石崁、泥塗的純土式建築,不管是手法還是風格都明顯與周邊不同。佔地雖不大,但周邊的房子彷彿有所牴觸般,隔著的道路與空間比其他地方還大上兩倍,再加上這裡多數是外人其聚,就讓這地方,更像是突然隔閡出的一個異空間一般。
港務區無招牌、無指向,唯有門外大量的走動人潮,及門口的守衛宣告著它的存在。
繞過走動處理各項事務的人潮,耿菽走往一旁沒什麼人的小區域,這個區域冷清清的彷彿是個雜物處一般。櫃檯前沒有任何人排隊,櫃台後只有一個快睡著的辦事人員,耿菽到櫃前的時候,他甚至沒有發現櫃檯前有人來。在他後方還有塊板子與可供喝茶的小空間,小空間的茶几旁坐著一個人。
耿菽沒有理會櫃台半瞇著眼的人員,視線繞過檯前與看板,直接轉往茶几那邊。
耿菽一眼就知,這個人就是要找他傳口頭信籤的人。
這個人不像櫃台睡覺的那人一樣,這個人面孔神采奕奕、坐姿端正方直,身上衣物不同於峋嶼人一樣,是多層次的分內外的穿搭,座凳上還放了把帶鞘短刀,明顯是個外地人,明眼人細看身上配件與面孔的話,還可區分的出來這人就是皇國區域的人。
越過櫃台,耿菽直接往茶几前一站,連凳都還來不及坐,那人就率先開口道
「主人知曉耿水師到來,還請耿水師老地方見。」看來對方也知曉自己,人還沒開口就知道他是耿菽。
「……」耿菽沒急著應話。看這人提話的情況,貌似也不是急事,就像是話家常邀人去玩一樣。但是上頭主人卻又急著派口籤前來傳訊?耿菽想了想後反問「我在等個人,緩些一起前往如何?」
「卑無權定奪,耿水師自理即可。」那人雙手作揖答道。動作迅速、不拖泥帶水,看來是個受訓練過的人。看著作揖的雙手表面,雖乾淨修整過,但仍藏不了那粗厚的繭塊,往下看了看配掛在腰際的短刀,這人顯然不是普通的下人。
「武衛如何稱呼?」
「武衛不敢擔之、先生吩咐我功三即可。」
「手心恭?」
「卑無名,字工力功、三橫三。」
下人取個功字?還帶數字?看來這主人又不知道有什麼奇怪思想了。
「好吧!功衛士,我跟朋友約好在外等他回來,我們先前往外面再一同前往如何?」
「耿水師方便即可。」
耿菽心想,看來真不是甚麼急事。耿菽自認對這功衛的主人來說,雖還不到熟捻的程度,不過基本上該做何事、該行何路還算知曉,但有時這主人在想什麼他還真不清楚,也不太了解。
耿菽與功衛兩人走出港務區沒多遠,耿菽隨意的在一蕉葉下的石頭上座著,功衛則站在後方看著。隨著時間緩慢的過去,日中始降,耿菽還是等不到束修前來,與功衛之間好似也沒什麼話題,總是搭嘎不上幾句就中斷。
「䇂工娘最近安好?」
「謝耿師關照,主人安好。態度依舊、興趣依然。」
「功衛、當家落過食沒?要不共食一會再回?」
「耿師無須擔心,要不我們帶點東西回去,想必主人不會不快。」
耿菽忙到現在,自個倒是沒吃。束修就算了,這麼久還沒來,肯定在路上買了甚麼。至於要不要帶點食去府上?耿菽想了想來由,覺得還是免了,免得又被耽擱時辰。
隨口聊個幾句,還是被功三斷了回來,且話不離回府兩字,就算是沒長眼的大概也聽出來意了。好在耿菽沒再候多久,終於看到束修與那名隊領走了過來。
隊領在束修旁邊像隻蜜蜂般繞來繞去,束修也就被擋的只能往前行。然實無論是再有興趣的東西,也被隊領遮擋個大半。路上也就掏了點幣,買了個沒見過的野食跟貝環,走走繞繞的終於來到港務區,兩人還沒入界內老遠的耿菽就找了上來,後面還跟著一人。
看了眼束修手上與嘴裡還在咀嚼的食物,以及旁邊一臉歉意的隊領,耿菽也不好說些難聽罵人的話,況且旁邊還站著個外人。「我說裴少爺,你路上吃跑了嗎?要不我們可以上路了?」
又是這起手勢!束修連忙把食物吞了吞,嚥了口口水後連忙回道「恩!肚子剛剛鬧翻騰,脫的有些空補了些回肚裡去。這不還有事要忙對吧?走走走!」
邊說束修還往耿菽旁靠,示意自己不會再亂跑。
順道遞了遞手上袋子裡的小點給他。不過耿菽拒絕了:「沒空吃了!趕著日墮前入洋流。」
束修沒理會這麼多,只是點了點頭。他不像耿菽一般對著時辰精準細算,對束修來說,現在也不過剛過日中沒多久,要說到日墮,那可還有三個時辰左右,這不還有大把時間?
「裴仲,等等我們去跟人見個面,這人是䇂工家的功衛士。」
「功衛,這位是我們云丘新來的引水,目前暫佔旗總一職。」
兩人互相點個頭,交揖一番。在跟隊領交代完各項事情並支開後,三人就開始往䇂工家的方向走。
一路上,功衛走在前方,速度快而不及,也不怕後面客人跟不上,連回個頭確認一下都沒有過。耿菽跟束修兩人則跟在後方跟著。
耿菽來過數次,對於路徑不會不熟,對於周邊也就沒什麼新意。束修就不瞭解了,對於路途上經過的事物都很是興趣,無奈還要跟著前面那人,故也沒法多做停留,只好凡是遇到甚麼就往身旁問。
這趟路很是快速,從港務區一路走來,穿過商街,穿至一般住家,甚是越走越偏,快往棄窟走去。
「耿菽,這䇂工家是在哪呀?我們這都走離住區了吧?」
「沒多遠,就在坡頂上。」
「喔……」
「怎麼了?」看著束修若有所思的樣子,關心的問了一下。
「不是甚麼大事,就是有些意外而已。」
「意外?」
束修往左邊看去,路道一旁皆是藤樹茂草,在隔著綠意過去就是棄窟,隱隱約約就可以看到幾個人,或蹲或坐的在那生活,還有些炊煙在那飄散。在往右一看隔著幾個小坡就是峋嶼一般住家,幾個架高木屋成群成列的建在那,不時也傳來幾個嬉鬧聲。
他們在走的小徑就像是一個分隔帶般,切開了這兩個區域,同個地方不同的風情。
「耿菽,現在這樣的場景讓我想起還在北嶺時的景色。北嶺戰事紛爭不少,時常會有些刻苦的人群住在一起,當時裴老爺也是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但這峋嶼看似不像是會發生這種事的地方。」
剛到峋嶼的時候,束修認為這地方就像是個小村莊、小聚落,人們理當會敦親愛鄰什麼的,畢竟這裡也就這麼大,還不相互合作的話,想必日子會過得很艱難。然而從廁所那走來,在一路經過商圈直到現在束修才確定,事情並非如他所想的那樣。
「難道是因為皇國與峋嶼之前的開港戰爭有關?」
「雖非主因,但也不全然是。」耿菽沒有多做評論,對於峋嶼的現況,從一開始的開港戰爭,到後續的保守派與新流派紛亂,在到至今的皇國管理,有太多的複雜情況,他不敢多做設想與評斷。倒是想多的束修,沒來由地跟耿菽抱了個歉。
「怎麼了?」
「那個……只是突然想起,你的爹娘都……對不起,讓你想起一些不好的回憶。」
「現在來說都不是甚麼事了,都已經過去。」耿菽隨口回了幾句,也沒後續。
隨行一路無語,靜然然的三人走往䇂工家院。
就在三人走到可以目視䇂工家院的門口時,在前方的功衛突然開口道
「恕小人多言,峋嶼雖地小人少,人心齊聚且團結,但也只是在同個地利文化下才有的結果。」
「甚麼意思?地利文化?」束修不懂。不都在同的地方同個族群嗎?還會有分彼此的情況?
「開港前,峋嶼本是多爭之地,要不也非有外岩山之處了!」
想想也是,一個本島八個外岩守外,頗有要塞高塔之相。
功衛又言「峋嶼已有眾多族群爭之,皇國只是起了個始、領個頭。誰導誰遵?乃是時巧地和,非刻意為之。然人心異己,開港後分化更甚,非我則他,群起合之,雖在同地,然分劃界。」
「在我看來峋嶼與皇國並無二樣,皆是巧合,巧於佔了地、合了群於多。」耿菽在一旁補充意見。保守派雖會責難都是皇國開港侵略才造成現在這局面,但在耿菽眼中,現在這局面,峋嶼族人一派獨大,雖說不是刻意,但也因為巧於在此處、巧於在此時,在皇國管理之下,峋嶼人不也排外他族,自己佔了個峋嶼各處。皇國之於峋嶼、峋嶼之於外族,兩者也何嘗不是如此相像?
「耿師此話可不能在峋嶼人面前說呀!峋嶼人多是自負己族,排他皆非。」
「功衛是峋嶼人?」束修在一旁問道。
看功衛這樣提醒,貌似是有經歷過什麼一樣。不過比束修還了解的耿菽卻搶在功衛前答道「䇂工家院的近侍都是皇國人,想必功衛亦同。」
功衛不答,僅微微頷首,也不知對耿菽之言有何感想。走至家院門前功衛揖手朝兩人請之「兩位請,䇂工娘已在內候之多時,下人就止步於此。」
䇂工家院門庭不大,一門二牆面、三飛銜簷四臥獸撐柱,多方看來都像是皇國的東、南方式建築,除了材質之外,處處都與峋嶼本地差異甚多。往門邊左右遠處望去,皆綠面白華,人植卻不失自然,自然卻不多雜意。
雙扉開敞,卻毫無裝飾,簡單的厚實木門、尋常的峋嶼黑漆。
門內一人,如同功衛一般,雙手作揖,等領著耿裴兩人入內。
ns 15.158.61.16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