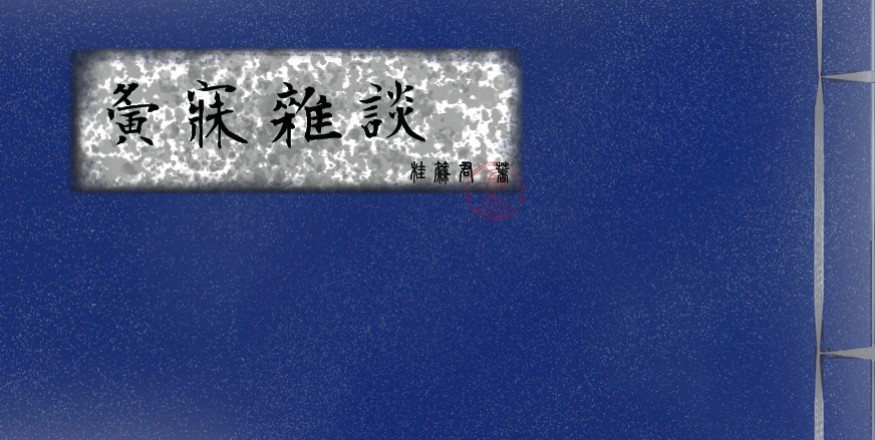這一大早的送行,不為其他,就是人少。況且北嶺路途遙遠,早點出發,也早點能到下個停靠旅宿。
如今北門的繁忙更甚其他出入鎮門,東門以及周邊區域封鎖的情況下,南北門的出入更是繁多。現在時刻不過旦時剛過要日始,衛京等一群尋衛就領著宗非拺來到北門送行,那是連個早膳都還未來的及吃。
「恆叱,東西可都帶著?」
衛京這在宗非拺左右轉著走,那是看來看去也不確定東西到底帶全了沒。這出了衛院問一次,現在北門又問一次,那怕真上路了,衛京搞不好又要多問一次。
「衛弟,這都確認過了。」宗非拺那是提了提包袱,就怕衛京還想打開包袱檢查一番。
北門現場幾個熟人除了衛、宗非兩少之外,一旁還站著鄺總與李師兩人。
一旁鄺良延也是看不下去,仗著身高比衛京高,隔著後頭就朝宗非拺道:「衛總未能送行,且差敝人送宗非少爺北行,望宗非少爺見諒。」鄺良延說完雙手抱拳,一旁幾名巡衛同禮。
宗非拺那是同禮躬道:「無妨。衛伯伯剛西原歸來,又行了一場軍。此刻不歇,何時能息?善事且休,馥鎮待復。」
鄺良延頷首,領著巡衛往北門外走去,留下衛京與宗非拺、李師三人。
衛京不知宗非拺是如何勸說李師一同去北嶺,現在也不敢開口問過。衛京只知那晚與宗非拺在門口升著營火陪著李師,醒來沒幾天後,宗非拺就與李師談妥了細節。
而在宗非拺與李師談妥的這幾天,衛京那也是沒閒著。儘管衛父歸來先忙著東區的整頓,衛京在家依然是不好閒著過。撇除沒了早上的課堂,回歸原樣的衛京除了自己早課之外,其餘時刻是陪同整個營的巡衛到處協助。一會是南們缺人手,一會是北門缺領頭,那是接著各總的另在馥鎮跑個沒完!晚歸之後更甚是開始學著營內的文書卷業。
這三天兩頭的幾候而過,宗非拺那頭是談了幾句不過半辰,沒個深入就給忙裡找去。這找了李師談妥,沒個幾天就要歸去,那是驚的衛京連個禮會都來不及妥。
衛京從外衣內襯掏出了一包囊,穩妥地交付在宗非拺手上「恆叱,你走的太臨時,我這裡都來不及給你找著,這點小東西給你帶著。」
那物也沒多重,宗非拺接過後那是直接收入衣中,沒打算現在開來看。
「我到了北嶺再寫信給你,等家嚴事情辦妥,馥鎮歸軌後,我尋個節再來你這待個幾日玩。」
「那是當然!你那房那物都給你收著,就等你再來。」衛京很是興奮的說著。好歹是開始接手家裡事業,這點還同個孩童一樣欣喜。
「那就說定了!」
「說定了!」
兩人指哥交扣,四指護掌言誓著。此時,宗非拺一個手臂力拖,把衛京往自己這給拉了拉,自個也順勢靠前,臉嘴貼在衛京耳邊悄聲道:「我房那還不要整個太快,我留了個禮在我房內,你等回著見就是。」
宗非拺說完,那是托起行囊準備離開,領著李師同北門外走去。
宗非拺這走了幾步,那是想到甚麼,回過頭又跟衛京道:「那點東西自己用著就行,可別看著荒廢道業。」
衛京沒見著宗非拺留的禮,那是不知其意,只得點著頭先同意。宗非拺見狀,這才跟著李師往北門外走去。
見著難得的同齡武伴走了,說衛京不捨那是不可能。然而馥鎮那點後事可多著,那也不等著衛京去幫,還有衛父那營事妥著學,衛京是一點離心還未散去,就得回衛家備妥午後的事情。
北門不過離衛家一個面,衛京那是沒跑幾步就回到了家中。家嚴不在,家慈也妥著婦女們去鎮上幫忙,家裡竟是沒幾個大。衛京退了小僕的午膳,那是自個房都沒回,就到了書齋那找恆叱口中說的離別禮物。然而當他到書齋一看,那是哪都見不著那禮物。問了問在家的幾人,卻是沒半個僕說有整過這房。
「難不成是藏起來了?」衛京的這番猜測自覺是頗有道理。問題就在於要從何找起?
衛京約略看了書齋一圈,那外表是沒有變化多少,甚至那有幾個櫃給恆叱自個給歸了位,恢復成原先書齋該有的布置。
衛京見找不著,所幸就坐在書齋看著內部內思考起來。
既然離別時恆叱這才私下咬耳告知,顯然這東西還有點隱私,又或者比較不合適拿著明面走來走去。再來恆叱還刻意叫人不要整理屋子,這東西或許很容易被其他人忽視而被收走?
衛京坐在椅上,神色繞了書齋一圈,那是沒看見甚麼容易被收走的小玩意。
那時間竟在衛京尋找之下過了半辰之久,衛京只好回營上忙去,這恆叱的禮物且歹放著後日在尋。衛京擔著恆叱那話,怕人亂了房把東西收走,這走之前還吩咐小僕們這房千萬不可進入整理,進之前還得知會他。小僕們當衛少睹物思人,也不覺得怪奇,少了間房收拾還輕鬆,那是循著衛少之言,妥著就是。
而等到衛京找到恆叱留下的禮物時,那是早已過了一候之久的時日。
那時衛京正在營內妥著文卷,試算整理著過往幾年的營內項目。這文卷不比書冊,內容枯燥不說,用字遣詞更比一般書卷還要偏澀。衛京這整著遇到不懂的文辭還要找人問著,這不懂問著還可,有時甚是那文冊自個錯詞,搞的衛京還要重新謄寫一遍。
而就在一次衛京整著異地考察的貨物盤整時,尋著又有錯字重新謄寫之後,卻是突然靈光一閃,不知怎地想起了恆叱臨走前說的那句話。
「可別看著荒廢道業。」衛京有股直覺,隱約知道了恆叱留給自己的東西是甚麼。
那日衛京提早出了武營,一回到家中那是盥洗換裝都還來不及整,就往書齋那走去。這次衛京不是漫無目的找,而是把搜尋地縮小在書櫃之上。
書櫃都是恆叱整理過且歸位的樣貌,那樣子不太系上可以藏禮物的樣子。不過若禮物本身就是書冊的話,那這樣好像也不怎麼奇怪了。
衛京站起身來往書櫃那走去,迅速掃了書冊一遍,果不其然那表面那是看不出來異常。不過當衛京把視角從書冊表面轉移到上頭,也就是書側時,那差別可是一目瞭然!就的書側自然因為年久日照而泛黃,而越新的書那側邊自然不會黃捲到哪去。這不過剎那,衛京那一尋書側就找到了幾本穿插在書中的幾本新書。
這幾本新書有些的確是沒幾載的書,那是衛京有印象讀過的幾本,自然是無疑可說。不過其中有一本光書名就讓衛京訝異不已。
這本不為其他,正是「尋地搜靈誌」!
這本地誌是恆叱偶然之間買下,說是地誌,實則春書。與恆叱在房內一同讀著此書的情景,衛京那是還未忘記多少,且後之事更是想忘也忘不了。
在那之後這書卻是給恆叱給藏了起來,衛京私下想找卻也找不太著,更甚後頭又發生太多事情,衛京這都給忘了此書的存在。
照理來說,這書屬於恆叱,理當恆叱會給帶走才是。現在卻還躺在自家書齋裡,這樣想來不是忘了帶走,就是刻意留在這裡。
衛京原先打算快速翻個幾頁來看,殊不知這剛一翻書卷,那是從中調出了一張字條。
「自用勿傳,廢長用短。」
這字條的詞義語氣,更讓衛京確信這本書就是恆叱留下來的禮物。不過本來是藏起來不讓自己看的東西,怎麼如今這又拿了出來?且這東西衛京也知道是恆叱字個買來的,二手物品拿來當禮物,是不是有些不妥當?
抱著懷疑的心情打開了這書,這時衛京才知道,這書留下來被稱為禮物的原因是甚麼。
這本書的內容依舊,仍是那些各地樓欄與床笫之事的描寫。然而書內的內容之間,卻是多了許多字詞。而這些多出來的字詞,就是恆叱自個的批註。
對於書目內容的敘述,恆叱是批寫了該敘述的真實性與正當性。有時寫的是告誡勿用、有時寫的是小嘗即可,在在是為整本地誌的各種內容,都給下了適當的解說與評論。
這本書宗非拺本來就沒打算帶著回北嶺,然而留下來若被衛弟給尋著,那就宗非拺對衛京的了解,那肯定會出事。然而自己怎般勸,人遠在北嶺那也無可奈何。直接銷毀此書,卻是有些可惜浪費買財。既然衛京喜歡,宗非拺索性就把這給留了下來,目的不為其他,就是為了衛京自個翻來看的時候,不會誤入歧途,更不會為了某些東西而過於傷身自殘,這才有了這本經過宗非拺批住過的書冊禮物。
至於這書對於衛京的擇偶影響與後續發展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時日回到鄺良延與一眾尋衛送了宗非拺與李師來到馥鎮屬地之外,幾人停在界石標地前戶道別離。
「拺子在此謝過各位,勞請各人在馥鎮煩忙之際送行,還帶我向衛家候安。」宗非拺那是抱拳鞠禮,李師在旁同示。
眾尋衛回禮後那是頷首離去,卻是徒留鄺良延一人在原地未走。
「鄺總?」宗非拺那是出聲提醒,誤以鄺良延走神。哪知鄺良延未走卻是有事想私下問之。
鄺良延抬頭,突然朝宗非拺問:「拺子還記的西門問你北嶺之事?」
宗非拺記憶尚存,然而鄺良延問的可不止一事。有的是衛京的事、有的是自己。
「不知鄺總所言是何事?」
「『裴水棗葉』可記得?」
宗非拺點了點頭。他依稀記得那是鄺總在問一些關於北嶺的事情。
「幫我帶封信到北嶺。」鄺良延語畢,從懷中拿出一封信件。
宗非拺尚未答應,不過雙手還是承接下來。信件很是尋常,就是有些厚度,貌似除了信紙之外還放了甚麼,不過宗非拺沒有過問太多。
轉了個面,中央寫了服橭兩字。
「這是收件人嗎?」宗非拺問道。一旁李師瞧著卻是比鄺總率先開口道:「那是姓氏,北嶺統合前的其中一個部族名。」
聽聞李師之言,鄺良延那是態度一轉,眼神充滿神采道:「李師可識得部族之人?」
「我也只是聽人說過,並不認識。」
看著鄺良延那神采盡失,想來也是有意無望。
「既然李師聽聞過,那我回去問爹爹,應該會有消息。」這話也算承接了幾信,宗非拺把信件往懷中收妥。又問道:「不過僅有姓氏,那這信該當給誰?」
既然李師說是部族姓氏,顯然不止一人才是。
這問題鄺良延沒有馬上回答,而是猶豫了片刻之後,這才有些打啞謎一樣的答上來:「你就問姓服橭的,哪個人舍弟跟著男人跑到南邊打仗的就是了。」
雖然意義不明,不過宗非拺這還是照著鄺良延的話重複了一遍,確認沒錯。
這時鄺良延還補了幾句可能找尋的人選,例如那人約略多大,是男是女什麼的都給敘述了一遍。
聽聞那敘述,都是形容之詞,想來這收信人,鄺總可能連人都沒見過。
而在一陣重複確認之後,鄺良延這才打算轉身離開。這離開之前還囑咐道:「若找不到收件人,就隨便找個有棗葉的地方給埋了吧。」
「鄺總,我在北嶺可沒見過棗葉呀?」這南方之樹,怎可在北冷之地生存?
鄺良延沒有理會宗非拺的問題,僅是背對著他朝他建議道:「家嚴知道的。」
他父親會知道?所以是在他出生以前的事情嗎?
看著不明所以的委託,宗非拺道也沒在意多少,反正那也是回北嶺之後的事情了。
提著簡單的行李,宗非拺與李師踏上了返回北嶺的路途。
這路途不短卻是相對平坦,走起來不會辛苦多少,真的辛苦那是走到北嶺之後。
原先以為李師為人寡言,在失去愛人之後想必更甚,一路上肯定是靜默不語。殊不知,這路途話題卻是李師先開了個頭。
「剛剛那個巡衛為何問起北嶺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這個問題宗非拺自己倒也想問。想來這也沒什麼好藏,李師短時間也不會回馥鎮。宗非拺就把在西門,鄺總跟自己談起北嶺之事的怪樣給說了一遍。
李師聽聞之後,卻是回了一句「還行,也不怪到哪去。」
「可我問他到過北嶺嗎?他卻說沒去過。現在這封信也是如此,貌似要給一個從未謀面的人。」
「因為他真的沒去過。」
「卻說得煞有一回事?」
「那巡衛的感覺我懂。那是聽聞某人一再敘述自己家鄉故事會有的感覺,雖沒去過該處,卻是在那人耳濡目染之下彷彿親如其境一般。」
宗非拺想來,李師也有跟鄺總一樣的友人吧?或許哪天自個也會跟衛京說上這麼幾個北嶺風光。
「話說回來,北嶺有棗葉嗎?我不曾在北嶺見過呀?」
李師瞧了瞧宗非拺問:「你有記憶以來,北嶺的當家是誰?」
宗非拺想都不用想道:「瞎了一眼的那位。」
宗非拺說的那位貌似李師全然不解,見他想了許久這才開口回話。
「應該不是現在的家主。你這年齡……可能錯過,或是恰好沒聽聞過。北嶺之前的女主人喜食棗果,故當時的大當家有在方圓之內栽了幾叢棗樹。」
方圓之內是裴家家院的另一個敘述,屬於師子們的宗非家當然也進出過裴院,但不可能裴院每個地方都跑過,自然是沒見過這栽種棗樹的地方。
「鄺總認識裴家的人?」
「不好說,那棗葉挺大的,大到出了裴院,這院外偶而還可以減幾個落地的。或許我們到北嶺可以先從裴院附近找起。」
李師的分析宗非拺點頭稱是。好在有個剛好熟識的人指路,要不然鄺總這信要給誰還真難找起。這話說回來,聽聞李師住過北嶺南部一段時間,所以才會這般理解這種事情?
「李師原本住過北嶺?」宗非拺試探的問了一問。李師也沒什麼特別的反應,僅是點了點頭稱道,還回頭問了句「怎麼了?」
「那李師還要回故居嗎?」
這問題李師到是搖了搖頭:「不了。只有我一個人住,這走了也沒人打理,不是荒了就是佔了,隨它吧。我聽你說過,裴家會給師子住宿處不是?」
宗非拺看了看李師,相比自己的行囊,李師的行囊更是簡便,不像是要搬家離異之人,彷彿隨時說走就走一樣。
「一度程度上的處所肯定是有。這麼說來李師行李很少呢。」
順著這話,李師手抓著包袱整了整道:「就是些衣物與書冊罷了。」
說到書冊,宗非冊想起水穀堂那一些書卷,那是隨意的提道:「水穀堂的書不一起帶上嗎?」
「那些都是學子自個到處自購而來,本來就不是我的財產,臨走前倒也託給他人處理了,我身上的都是我自個的書。」
「校書或導本之類的嗎?」
宗非拺這問題問的順口,卻是讓李師有些尷尬。只見李師笑了笑有些遲疑的道:「……你多心了。我本來就不是名門出生,說是師子也不過一介鄉鎮庠序,身上那書也不過都是些日記與筆記罷了。」
說到這,李師還反問宗非拺道:「我聽聞是家嚴囑咐,邀我去北嶺當師子,然而到現在我真不明白我有什麼能教的。」
「這……」
這還真不好開口。的確是自己拖家嚴的令來邀李師去北嶺,也不能說是家嚴一個占卜就下的決定吧?
現在想來,那日找到李師的夜晚,自個跟衛弟在門口營火待了一晚,這不慎睡著醒來,李師就自個過來洽談去北嶺之事,要說自己不驚訝?那是不可能。一開始李師那還堅決拒絕,那理由當時也不難理解,就是礙著凝塵罷了。
如今態度反轉,突然又要跟著自己去,這怎麼想都跟已逝的凝塵有關。既然人邀的來,宗非拺當下也是快速應對沒想這般多。
現在看來,疑心上頭,甚是不解,李師何想?
真要開口問起,這一定會談到凝塵。這想到李師那晚悲傷欲絕,宗非拺那是不好開口談人痛心之處。
然許這氣氛靜默的太久,李師是察覺什麼,宗非拺不問,李師卻是自個答起話來。
「其實你不邀我去北嶺,或許不是裴家,我也總有一天要回北嶺一趟。」李師說這話的時候手在胸口緊握著什麼。說到這停頓了一會又繼續說道:「那時北嶺一片混亂,我因故失去了相愛之人,這才逃離般地離開北嶺。」
北嶺的戰亂是宗非拺出生前不久的事情了,情況如何也不是多了解。換句話說,李師這不因為戰亂死了兩個愛人?宗非拺這話問不太出口,只得靜默地等著李師繼續說下去。
「很慶信我再來到馥鎮前遇到了凝塵,要不然我或許會在馥鎮渾渾噩噩的度過下半生吧。」
「凝塵也是北嶺人……我是說,來自北嶺?」
李師搖了搖頭:「我也不清楚。老實說,我到現在才發現自己竟不多了解他。」李師頓了一下,這又補充道:「我是說另外一個原本的他。凝塵應該有跟你們說吧?」
「蟲精的事嗎?我知道,他有提過。」
「凝塵的人身是我從小帶到大,他的樣子就像我過去的愛人一樣。我了解他,如同了解我的愛人一樣,而他待我就像愛人待我一般。如今撇去這層『相似』身分,認識真正的他,我才認知到對於原本的他,我根本沒了解多少。」
宗非拺想了想李師的想法,心中猜測道,或許李師害怕愛的人,不是人的身分?然而這想法很快就被裡師的話給否決了。
「不過當我認知到他根本不是我原先愛的那個人,想要去了解他並跟他溝通後,卻失去了他。」
「他不曾在你面前暴露過嗎?」
「我隱約有察覺過。」
「他與我們對談間,貌似沒打算藏過。」
「他在大家面前一直都很坦率。在我面前我也是一知半解,又或許那早是坦率而我只是不想揭穿他。」說到這,宗非拺見李師停了下來。李師正了正衣領,低頭看了看胸前,這又抬頭繼續說到「在某個特定的人面前,總是會有某一些臉面不想讓他見到,不管這是好的那一面還是壞的那一面。我自覺他坦率的那面並沒有全然的對我展示過,這是我的遺憾也是我現在想了解的。」
李師貌似很多部分略過不談。不過就宗非拺一開始猜測的情感來看,李師對於凝塵的感情肯定是愛人般的感情,只不過這愛情在李師想要撇開舊情人的借代,並真正面對非人的凝塵時就結束了。
「我想回北嶺或許只是種儀式。」
「儀式?」
李師對宗非拺的問題沒有正面回答,反倒像是自言自語般地說著:「凝塵在聽聞你的聘師邀約後,也極力勸我回北嶺,或許那時候凝塵早就知道我該為了舊戀情而回北嶺。」
宗非拺對於李師的想法無法回答太多。畢竟那也只是李師對於凝塵勸他去北嶺的猜測。實際上凝塵當時勸說的想法是什麼?宗非拺也無法理解。
在水穀堂旁的茶館,凝塵說的那句「李師若真要去北嶺,我是不會一同前往的」此時在宗非拺此刻的心中默默響起。李師踏上去北嶺的路途,不知是凝塵一開始就了解李師而答,還是他知道自己終究不會在李師身邊?
不等宗非拺想明白凝塵說那句話時的心境,李師又是突然答到:「忘掉或許是種方法,但我自認為我不可能真的忘卻所有,與其這樣找藉口逃避他的死,不如借另一種方式來面對。從失去的地方重新開始或許不是一種辦法。」
李師依然沒有說完全,或許重新來過這種行為就是一種儀式吧?宗非拺不經這麼認為。
對於愛人死亡與前往北嶺的話題,李師並沒有在透露更多,反倒是開始問起了在北嶺師處的各種問題,看似對於前往北嶺師職甚是積極。
不過就宗非拺看來,更像是對於前個話題避而不答。
宗非拺不自覺的望向李師,揹著少量包袱的李師,或許是因為肩傷的關係,儘管李師的包袱既少又輕,李師一路上仍然是不停的調整著自己的背袋。
這樣的行為一直到下一個休憩處時宗非拺這才注意到,李師那行為並不是要調整包袱的平衡,而是要調整包袱帶不要壓到頸骨上的配飾。
男性戴頸飾在黃國很少見,這讓宗非拺那是多看了幾眼。
李師脖子上的頸飾很是單調,就像是用黑檀木鑿刻出來的一樣,充滿木紋的黑色圈環。
那抹圈環很快地消失在宗非拺的眼中,迅速地又被李師給藏於胸懷。
ns3.149.246.106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