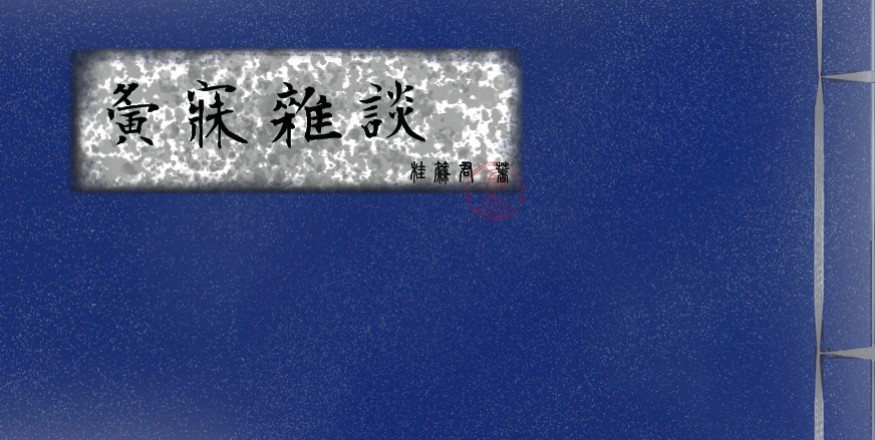宗非拺一早醒來,卻是覺得整個衛院有些紛亂。平常日旦頂多只有一些細微的聲響與自然晨鳴,這次醒來的衛院卻是隱約有各種人為的走動聲響,就連前幾日都早早到來的峻子今日也比平常晚到。
依然無法改口慣,叫宗非拺師子的聶峻這般跟宗非解釋:「宗非師,沒辦法呀!一早衛夫人到處打點,嫌院子哪不夠乾淨、哪不好看的,眾僕從都被差來遣去,甚是少了好多人手。」
峻子邊說邊遞上巾布,放著盆桶就在一旁候了下來。這行為若是衛京那邊肯定是沒法這樣幹,好在這衛家姪子喜歡自個來,峻子想來也是落得輕鬆,這不躲在這裡等空閒?就算站著陪人聊天也比在外走來走去搬東西好。
「衛夫人這麼早就起來了?」
「是呀!平常可沒這麼早起呢。別說衛少起來早課,搞不好早膳時才會出房門。」峻子邊比手畫腳地邊說道,彷彿這事情有多誇大!回過頭卻又道「這話說回來,今日也沒看到衛少起來早課。」
「你不知道今日有甚麼事情?」
「有甚麼事情我們僕從還管得著?這般情景我只見過兩次,一來是大整房,二來就是有貴客到。這次肯定是有貴客來,就是不知何人來訪。」
峻子看宗非拺一言不發,很是平靜的梳洗著面容。峻仔這下也猜到,宗非拺肯定知道些什麼。
「難道……宗非師知道是何人?」
「約略知曉。」
「可否告知峻子一二?」
宗非拺搖了搖頭道:「只知來訪者是何事,卻不知來的是何人。」不等峻子續問,宗非拺又道「且是衛夫人道我知情,卻不許我言之。」
這下峻子也不好多問,免得被衛夫人知情多事。宗非拺見峻子沒多問,也就不再答話,專心盥洗面容去。
宗非拺頭沒蓄髮留長的文化習慣,盥洗就不多花時間,面容身子整了整後,就把用品放一旁給峻子收拾去了。
峻子見宗非拺只是盥洗卻是沒更衣,詫異問道:「宗非師不著衣?」
「沒這般早出門,暫不換。晚點我出門再來拿濯衣吧。」宗非拺說完就往床榻旁的案桌一座。那桌疊滿了許多書卷,甚是昨晚歸房後,沒來得及看的書卷。
峻子見宗非拺沒要著衣,自然也就沒事要忙,這就開始收收盥品準備走人。
不過峻子收東西之時,卻發現宗非拺好似有些不對勁。
峻子刻意緩了緩自己的收拾速度,悄悄地往宗非拺那看去,只見他在案桌前翻來覆去,一下拿起這本冊子、一下又翻了翻旁邊的紙卷,貌似在找著什麼東西。
剎那,宗非拺貌似想起了甚麼,轉過頭來朝峻子問道:「衛京現在在哪?」
「峻子只知衛少一早就被衛夫人叫去,現在打哪兒也不知曉。」
宗非拺嘆了一口氣,無奈道:「你見著衛京回房時,差我道一聲,我的書冊忘在他那。」
「峻子知道了。」
只見峻子收收東西後就往房外走去,過沒多久宗非拺這才想到,自己卻是忘了告知峻子自己等等出門後會晚歸,甚是也找不著他告知。
宗非拺到了房門口,卻是沒見著峻子,其他僕從也在那忙著東奔西跑,宗非拺也不好打擾,這事且逮作罷。
良久,宗非拺這才換裝更衣出門,從房口到院外,僕從到是少了許多,卻是不知又被衛夫人遣去哪忙了?宗非拺也不顧這般多,隨便跟個僕從告知自己出門後,也就一路往水穀堂而去。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W7a3Lza3OL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rlt8BkN86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QWl7gLifBl
水穀堂數隔幾日後開課,門外卻也是沒多般人群,靜的可以。不過待宗非拺靠近後,隔著外牆一聽,牆內卻是熱鬧可以,這聲響不外乎是各孩童的話語。
一早上的時段多半是低年齡的孩童,不為其他,只因一般父母托孩子上庠續,一來習字學數,二來委子顧人,這般近午時來接孩童,恰合不過。
宗非拺一來水穀堂見到的便是這般情景。一群學童從庠序走出,正好是幼童那時段的學子下課,氣氛歡快,各學子在哪打打鬧鬧好不快樂。
而門一旁站著的正是幾日前,他們幾個近束髮的幾人在討論「水穀,三怪不成」的一怪,凝塵。
不知是水穀堂本身貧素,還是因為他本人愛好,凝塵仍然是他那一慣的樸素打扮,素衣素紳,無紋無飾。
他一人如同剛開庠序時相同,正拿著冊子一一清點著離開的孩童,不時還有幾個長歲一點的少子要進去待課,凝塵還得翻著冊子找人。
這學人進進出出,點人錄字的也是一陣折騰。宗非拺見狀也就不好打擾,且待人少些時刻在打算叨擾。
須臾,過了半辰數刻,這出堂學子才漸少似無,宗非拺這才上前招呼。
宗非拺不同於其他學子,報了個名就進入庠序,而是等在門口與凝塵招呼,這行為獨樹一格,讓凝塵不自覺地記了一筆。
凝塵慣性的問了一句「貴子何稱?」
這話問的除了是庠序紀錄需要,另方面也是凝塵自個想知道。因為凝塵很少見過這般有禮貌的學子。
「名宗非,單一字,拺。」
凝塵翻了翻學冊,想當然的是找不到這個名字,更別提宗非這少見的名,該當很好找才是。
整個學冊不過才五頁,凝塵可說是剎那間就翻完了。回過頭,凝塵一臉抱歉地朝宗非拺問道:「同儕,你是否來錯庠序?我這沒你的名字。」
宗非拺這才跟凝塵說上衛京昨晚交託的事項。
宗非拺見凝塵聽完之後,又是回過頭翻了一次學冊,不過貌似沒有找到「恆叱」這兩字,抬起頭來的凝塵滿臉尷尬。
凝塵闔上學冊,突然像是想通甚麼事一樣,忽然朝宗非拺問道:「你說這事是多久之前發生的?」
雖然不知道凝塵為何要問這事,不過宗非拺還是如實回答了一番。
「數日之前,不過一候。庠序剛開招子之時。」
「你說與我交談的人叫什麼名字?」
「衛京。」
凝塵點了點頭,朝宗非拺說道:「你稍等我一下,我去詢問一下事情。」凝塵說完就往庠序內走,也不管宗非拺是否還在等。
這凝塵一走,宗非拺自然是不敢離開,免得又像上次那般剛好錯過。
然而凝塵這一走就是走了快半個時辰,許多學子或慢或快的都抵達庠序。宗非拺這一人獨自在外看著學子陸陸續續的進入,好似有些詭怪與尷尬。
也不知道凝塵詢問事要問何事?也不知道要問誰?這跟衛京所說的情況有些出入。
原先宗非拺以為只要報了衛京所說的事項之後,自然就可以進入庠序,最多也就補筆個學子姓名與預學之事罷了!怎知事情現在變得有些奇怪。
好在這等待沒真等滿半個時辰,正當來上課的學子漸漸變少之時,凝塵這才從裡面走出來,後面還跟著一人,這人不是別人,想必定是李師!
也就是宗非拺受父所託,想要聘回去北嶺的人。不過此事自然是不急,現在連門都進不著邊呢!還談說什麼聘不聘。
宗非拺放下心中的意念,故作不知的朝凝塵看去,等著他給個說法。
也不知凝塵與李師說了些甚麼,只見凝塵見宗非拺看來,卻是沒給個說法,只是轉頭朝李師看了看並道「就是他了。」
李持水繞過凝塵擋在他身前,朝宗非拺看了看,言道「你跟塵子說的事情我知道了,但是我怎知你說的是真是假?那事情是你過了報時還想入學編的謊言,還是真的幾日前來說過?我預何查?」
這事情不說別的,又沒人證物證,就看當事兩人的心證,其他人多說無益。既然衛京不在場,自然只能找凝塵對談。
然而當宗非拺轉個身子想詢問凝塵時,李師卻也移了移身子擋在凝塵前面。
「有甚麼問題你直說,別找著凝塵問。」
「李師子,這事只有杜、衛兩人知情,若不問杜兄,這事怕現下是無人可答。」
「我怎知是不是你剛剛強逼凝塵說的?」
李持水這話說得勉強,宗非拺一聽也聽得出來。這態度很是明顯,就是說甚麼李師也不給他進,要怎麼強說詞都有,就不怕你不接受而已。
宗非拺也無可奈何,他可以肯定他說什麼,李師肯定也會有別的說法把他堵在門外。至於不讓他進的原因,宗非拺目前是想不到。
而凝塵給人的態度也很是奇怪,貌似真的忘了此事一樣。對於李師擋在他前面的行為,凝塵雖然覺得抱歉,不時有想要站出來說話,然而卻被李師用手給擋著不讓他到前面來。
兩人在門口拖的時間貌似有些久,不時有幾個學子從裡面探出頭來觀看。宗非拺見狀也不好繼續耽誤其他人,只好跟李師留了一句「我代衛氏長子京告知,家院要事,假課一日。明日我在與衛兄前來叨擾。」
語畢,宗非拺確認李師聞之頷首,也沒意願等李師回應,獨自一人信步行遠。
李師見宗非拺走遠,放下心來、嘆了一口氣,轉過身子走入廳堂。
凝塵見狀自然事察覺到什麼,一個手勁就拉住李師子的袖擺。
「李持水!你是不是知道甚麼?」
李持水一臉茫然的回過頭看著凝塵回道:「你說什麼?」
「他剛剛說的事情,你根本就是知道的對吧?」
「那又怎麼樣?」看著凝塵堅定的眼神,李持水自知早就被看穿,那他也沒打算繼續圓謊,很乾脆地就認了。
「你!你怎麼可以趁我……我那時有做甚麼讓你不高興的地方嗎?」
看著突然一臉驚恐的凝塵,李持水語氣放軟的安慰道:「沒有呀?我們這兩天不是過得挺高興的?」甚至出手拍了拍凝塵的肩膀。
不過這舉動卻讓凝塵更為警覺,他拍開李持水的手後道:「你是故意提兩天前的事?兩天前又怎麼了?」
「沒怎麼呀?你別這麼緊張。」
凝塵兩手在自個全身上下拍了個遍,卻是沒有發現什麼異樣。然而凝塵看著一旁師子無謂的眼神,他立馬就知道他肯定是找不著了!要嘛證據被湮滅、要嘛身上找不著。
看著李持水的態度,凝塵道:「我的錄冊呢?」
「在你房間裡。先說好,我可沒碰過你的任何書卷。」
凝塵對於李持水的話沒有聽進任何一字。他飛快的轉過步伐,往水穀堂一旁的住屋走去,顯然是要回房間找他口中說的錄冊去。
「今天的課你不聽嗎?」
遠遠的,凝塵沒說半句話。碰碰碰的幾個踏階步伐與啪啦一聲的關門聲,道盡了凝塵今日肯定不會再輕易出房門。
李師見狀,聳了聳肩無謂。最後獨自走入廳堂準備開始講課。
其他學子則是第一天來上課,自然是不敢多言什麼。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5eqa9qesu0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qsNS2mfZ6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2kfpnY42I
回過頭來談,宗非拺走是走遠了,卻不知打哪去。跟衛嬸說好了要晚歸,現在可好了!一整個上不了庠序,剩下的時間不知道要怎麼度過。早知如此,出門前應該帶幾本卷測出門的,現在衛院內應該正忙的慌亂,宗非拺自然是不好回去打岔添亂。
走著走著,不知怎地宗非拺忽然在心中冒出幾段話語。
「凝塵這人記性差,常教的事情,往往久時不提個一次就給忘了。」這話自是與衛京在茶攤聽那茶嬸說的話語。
現在想來,凝塵這行為正好應對了茶嬸說的話。不過若真是如此,那衛京所言豈是謊話?貌似也不是這樣,因為衛京沒有理由跟他說這個謊。且衛京說的兩人師徒關係確實真有個那麼一二,從李師子坦著護言的態度來看,衛京說的李師子特寵這凝塵,也不是什麼瞎說。
宗非拺心想,自個父親真是給他找了個大麻煩。特地要從外地聘個師子回去,卻又不說明個來由,原先以為這事情難只難在地遠,怎知事情貌似沒這般簡單。
李師子看來態度強硬,講好聽點是守規矩,難聽些就是不知變通。宗非拺也不知道這師子有什麼特別的,父親硬是要聘這人回北嶺。像他這種鄉學、地庠的師子,北嶺不敢說很多,但是比他好的定是不少。
宗非拺這般想來想去,一方想著要怎麼跟師子打好關係、一方又想著他父親究竟想做甚麼。想著想著卻是不自覺的跟著衛京上次的路徑來到了北冬街街尾的那個市場。
比起上次黃昏時與衛京前來的份亂,現在市場的人數可謂稀稀落落,有些商賈甚至在台前打起盹了。
上次與衛京黃昏來時,許多攤販早已關了不少。現在來看,卻是多了許多不曾見過的攤販。
宗非拺這般待待、那邊晃晃,甚是打發了不少時間。
然而整個市場也就是街尾的這一區而已。真要說大?也不至於讓你逛個一整天,尤其是在重複性高、且幾乎都是吃用居多的地方市集,宗非拺用不到一個時辰半的時間就把整個街尾市場給晃蕩完。最後停留在衛京帶他訂製短著的那家布衣店觀望。
原先宗非拺只是想看看,那時跟吳老闆訂製的短著不知做得如何?雖說吳老闆也去過北嶺,但是對於褥衣褻絝甚麼的應該也沒見過多少。不怕用料差,就怕作錯型。
不過宗非拺一進店家,卻是見到一位姑娘在顧店,旁邊還帶著一個孩子,也不知道是老闆妻兒還是哪來的僱員。
那姑娘見到宗非拺進門打了一聲招呼,也沒問甚麼需求,回過頭就繼續在那哄孩子。
姑娘那行為宗非拺也不在意,反正他也只是進來看看,還真沒打算買什麼,店員不理睬他,他到落的輕鬆。
前天晚上與衛京來時,忙著與老闆扯話題卻是沒心留意店內。今天這早來看,走進了店內,這才有意留心整個店家內部。
店家外觀看似不大,繞過櫃台走進後整個空間卻又是增了不少。裡面的空間不管是牆面還是天頂,都塞滿了各式東西!店中間雖然空蕩蕩的沒東西,但四周牆邊卻是做滿了隔櫃,滿滿的塞了許多布匹,而各個櫃頂上又釘串了幾個線繩,線繩在店家內留下了一串串的軌跡,線跡上掛滿了各式衣裝。
布匹與材料,宗非拺也不懂多少,繞了一圈後就回過頭來看那些掉在線上的衣物。
吳老闆不愧是以前當過走商的人,這裡的衣物並不拘泥於當地需求。從常見的馥鎮生活衣物與西原傳統服飾,在到不常見的北嶺禦寒外罩及東丘繁華絲辦,無一不是什麼尋常可見的衣物。就是不知道這是老闆自個弄得還是另有職人托工。
或許是看宗非拺在店內留著久,櫃台那姑娘件現在沒什麼客人,這才回過頭來搭睬宗非拺。
「不知這位少將需要什麼?現在天冷,我們還有許多保暖長著可供你挑。」
聽著那姑娘的招呼,宗非拺對於語後的那番推薦甚是不易外,但是句前的那番話語,宗非拺甚是不解。
「……少將?」
那姑娘看了看宗非拺後,一臉疑問的反問:「你不是巡守嗎?」
「恩、不是。」
聽到宗非拺這般回答,那姑娘有些尷尬地回道:「不好意思,我看你長相以為你是西原人。我聽吳老說這裡多數的客人都是巡衛,這才誤會。」
「沒關係的,這也不是第一次了。」宗非拺輕鬆地帶過這場誤認。或許是外觀問題,他的確是很不像北嶺人,這樣的短髮褐肌在馥鎮反倒是更像是西園人。
回過頭來,宗非拺撇開外觀印象反問道:「你說的吳老是那個有些跛腿的老伯嗎?」
「先生你認識呀!他是我大舅,我來幫他顧下店而已。」
那姑娘說到這時,兩人口中說的跛腳老伯剛好回來,此時正緩慢地背著一竹簍走進店內。
「舅舅!有人客找你。」
大伯聽聞後一臉疑問,想說平日沒什麼客人,怎現在忽然來了一個招待不來的?
待大伯拐進店裡,看到宗非拺後這才恍然大悟並開始招呼到。
宗非拺與吳老闆一陣寒暄之後,各自在櫃台邊緣坐定,話題不雜,自然是那訂做短著之事。而原先幫故顧店家的那姑娘見吳老回來,簡單的打個招呼後,自個抱著小孩離開了店裡。
吳老闆見姑娘走遠了後,這才話題一轉反問起了宗非拺。
吳老闆走到櫃邊,拿了一壺預泡好的茶水,邊給宗非拺添杯邊問:「我那外甥女,沒做甚麼亂事吧?」
宗非拺搖了搖頭道:「那姑娘就是帶孩童呀?怎麼了?」
吳老闆一句「我這外甥女呀可怪了!」做開頭,緩緩地跟宗非拺抱怨了起來。
吳老闆抱怨,妹婿不疼女兒,自個妹婿不敢說是甚麼有錢人,但是肯定是不用自個幹活的閒人,邊下養三四個家事自是沒問題,但又偏偏讓她女兒去做事。
「這妹婿問題,跟姑娘怪有何相關?」
吳老闆一拍掌驚道:「這怪就怪在這裡!我跟你說,我這外甥女居然也不反對!家裡勞務也就算了,平常那街坊甚麼務活、集會的也沒落下,人家不說,還以為我外甥女是哪來的僕妾。」
吳老闆添了一口茶水又道:「也不是不讓她做事,但是我妹婿好歹教她一些業活呀!家裡那些內務給僕妾做不就得了?」
「那她剛剛帶的孩童……」
「那肯定是她在幫街坊鄰居帶的!」
其實老闆這問題宗非拺很能理解。自個本家的少爺也是天天往外跑,家裡的本務不做,盡是跑去外面做些外務,自個聽他宗非老爹不知道抱怨了多少次。老闆的外甥女套個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吧?
或許因為馥鎮這地方是以商業貨貿為主,所以比起在北嶺常見的男女分務,馥鎮反倒是男女們都會些商學與業活。好比隔壁路口的獵戶大姑,與其讓她在家做家務,不如跟她老伴出來一起做活還賺得比較多。這樣的例子在市場可說是見多不怪,宗非拺剛在街口看著也是覺得新奇一陣,這女販與男販都有的樣貌,在北嶺可是見都見不著。
吳老闆或許也不是土生土長的馥鎮人,總覺得自個地位不同,怎樣的身分有怎樣的事要做,而不是這樣主副不分。
「這不我腳傷不方便,我才託我外甥女幫我顧個店,好讓她學著些甚麼。怎知她顧店還幫人帶著孩子,這樣子真是難堪。」
見吳老闆搖頭無奈,宗非拺也不知道該怎麼跟吳老闆說他的想法。
沒多久吳老闆也覺得自己抱怨太多,回過頭不再談自己家務事,轉身從裡面拿了件衣物出來。
「照你的說法我紉補了三套出來,你看適合不適合?合適的話,我剩的料還可以再紉個兩套。」
吳老闆拿出來的衣物正是照著宗非拺的說法所做的短著。這短著既無袖子、也無胛面,若布料在少一些,說是兜布搞不好都有人信。
吳老闆手藝好,宗非拺比劃也不差,這作出來的幾品與宗非拺所想的差異不大,拿來穿可謂合適。不過這衣物在老闆眼中可是詭怪,正如同他一開始所擔心的,這衣物除了好活動之外,無一保暖與蔽體的作用,再加上宗非拺當時還不用暖綿羔毛,而是用虫絲木麻,這通風透氣雖好,但宗非拺居然說要拿來當褥衣睡覺用?除非你在屋裡生個爐,要不這樣穿就算搭個布毯也必要凍個不行。
「我說恆少,你真要這樣穿?不是我話多,北嶺公衛真是這樣穿?」
宗非拺點了點頭道:「內著卻是如此。吳老闆不是有去過北嶺當走商?沒見過?」
吳老闆搖了搖頭,直言自己沒探究這麼多,別說北嶺常見款式,若不是宗非拺提點,吳老闆也只會做馥鎮這附近常見的款。
其實也不怪吳老闆無知,實則宗非拺不懂。北嶺從走商那批來的東西,後續加工成什麼樣,走商自是不知。
見宗非拺這般了解北嶺內配,吳老闆不經問道:「恆少與衛家同樣是武家?」
「差不多,只是與北嶺走著近罷,怎了?」
吳老闆走到店內的一處隨意坐下,摸了摸自己的膝蓋後,緩緩說道:「就當是我人老多話吧。若是像衛家一樣當個一處小鎮守衛,那是自好不過,若是要像那北嶺武家一樣?聽我一言,還是別近著好。」
吳老闆自是不知宗非家的情況,僅當宗非拺是衛家遠親,這話說的是讓宗非拺著實有些尷尬。
不等少年接話,吳老闆又是續言道:「這戰亂之事,自是在蠢不過。」
雖然早有料到,但是宗非拺還是緩緩地問道:「你這腳傷該不會?」
「自是如此,那時馥鎮還好說,只是貧了些。我當走商之時,正巧要路過北嶺南方,怎知戰事剛起,各處自是動亂一陣,那是一個瘋亂!也不知道著什麼道?碰到一群人就是喊打喊殺,逢人就砍!我這膝腿就是給人一個切到。」吳老闆邊說邊柔著自己的膝蓋。
那事情宗非拺自是不知,聽聞過自家長輩談過,卻是沒半點畫面,不知其亂有多亂?殘有多殘?
吳老闆見宗非拺聽候沒什麼感言,自是以為宗非拺年少不聽勸,執意做職,那自個談這個就沒什麼好言。
「你在馥鎮要住一段時間,自然會見到各種人事物。吳老在這勸你不要自曝是北嶺人一事,這裡有不少是像吳老一樣因為那場戰事被亂了半生,吳某老了看得開,在年輕一些的人未必就會如此好言。你在大點,多了些場面,自然會有感觸。」
宗非拺諾道,承了吳老勸練。
「剩下的料,我就幫恆少都給用掉,恆少有空過幾日再來取吧。」
吳老闆不知道是說多了有些感觸,還是因為時近燈燃,應完幫宗非拺的訂單後,就打算閉店關門,讓宗非拺也不好多言留談。
最後宗非拺也只好順著北冬街打算走回衛院。期間宗非拺還怕時間不夠晚,沒達到衛嬸的晚歸要求,還在隔了衛院一個街口的地方吃起了晚膳。
這店是衛京上次帶他來吃的那家,雖說那時衛京點了一堆朿食,但那蔬菜確實不錯食,宗非拺這會還想再嘗嘗。說也恰好,這門口剛好站著一人在那躊躇不前,一臉要進不進的堵在門旁,這人宗非拺走進一看不是什麼閒雜人等,正是衛家小僕,聶峻!
ns13.59.167.6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