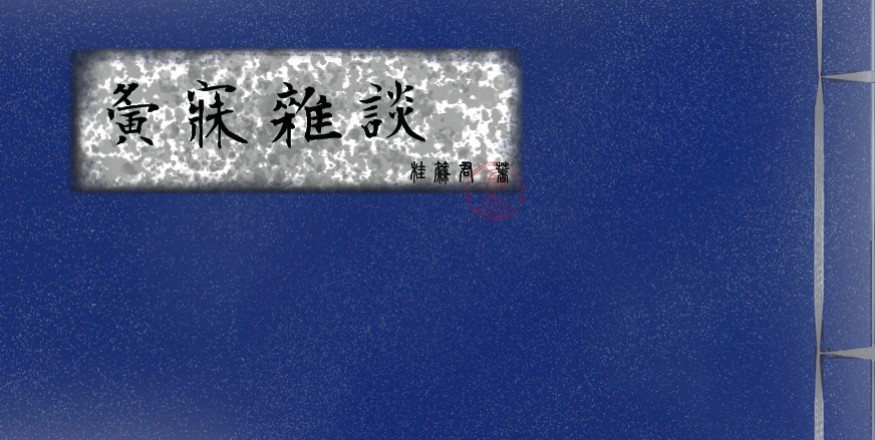耿菽說出去當然也不會帶束修真的走出南風院。當然口頭上還是會說要帶束修出去,不過會先在南風院裡看看逛逛,等拖了些時間後,就可以用近晚夜深的理由回絕出去的要求了。
不過現在也沒多晚,一個半男娼院自然也沒多少可逛的,顯然單純況店內是逛不久的。這點耿菽也是做足準備,事先就打聽好了南風院中「格」的時間。
格,這是在南風院中的眾多「表演」之一。在一略高的平台上演這各種短劇或是尋常故事,而在台下則是用一條條木頭,橫豎搭建成一格格的小空間給顧客落座觀看,也因為這樣的方格樣式造就它的名稱由來。然而說是表演短劇故事,在南風院自然不是一般的故事,多半是一些陽癖內容,更甚是一些搔首弄姿的走劇。
耿菽當然是不會讓束修看這些東西。
他會選這個時段去格賞戲,自然是做足了準備。格也不是全時段都有,現在這場就是非常單純的走劇。走劇多半沒甚麼內容與連貫性,多半是單人到兩人左右,表演的內容就是看個人,有些有藝在身、有些則是南風院會安排。且因為時段關係,現在上來表演的人也不是甚麼頭牌,多數是一些新人。
耿菽帶著束修在南風院逛著,在不經意地經過格外,說著要不要看著表演,最後領著束修帶到一個格子內就坐。這位置不是正坐主位,但也不到偏間露位,且是恰當。
這時間的格,消費通常一般。畢竟多半是沒什麼艷戲,就只當作是給新人露個面、曝曝光,來的人也沒多少。
耿菽與束修坐在同一個格內,周邊的位置都沒甚麼人,隨意晃過去可說是一手可數。
耿菽還怕表演不夠精彩,束修想早早走人,拖不了時間。耿菽入場刻意多付了點票錢,入座後一旁還多來了一些水果、甜點,這是原本格就有的服務,這樣讓束修邊看邊吃著解饞,就算無聊多半還可以拖上一段時間。
不過這食物這東西,卻是耿菽有些多慮,這時段格的表演對於觀眾來說雖然是無聊,但是對於束修這個北嶺人來說都是新鮮沒看過的東西,更別說束修這大半時間還待在船上,就算台上只是單純地跳段舞都算有趣!有時候台上的人還會唱個小段,聲音不敢說上乘,但那轉調與難度卻是做得到位,唱功也算獨特。
束修看得專注,耿菽卻是沒甚麼心思在看台上,反倒是專注著座位旁得束修。
比起台上的那些走唱,看著束修一會而笑、一會震驚的表情,反而更讓耿菽覺得悅目。而這走劇一看也是看了幾刻半辰,原先的表演也過了一輪,台上表演告了一段落,只見台旁幾名正裝人員,各拿著不同的樂器,有絲有管地在台前合奏起了音樂。那音樂是首很尋常的輕快小曲,沒多少轉折與難度,也沒多長的曲段,片刻就結束了。這音樂在黃國及周邊很是常見,就是在北嶺的束修也是聽過。
「這是表演?」束修常一旁耿菽問道。束修覺得奇怪,這段落說是表演也太無聊了吧吧?表演完也沒啥收尾,曲奏一落,幾人頭也不會的走下台。
「這是走劇的某個段落結束的意思。」耿菽又示意束修朝剛剛那幾個走下台的人看去。「那幾個正裝的是南風院的人,這工其實沒多少錢,就是上台吹個段,結束下來而已,就別太要求他們有甚麼服務精神了。」
「所以還會有下一段?」
「恩,不過要等一下,人通常也不會完全是剛剛那些人。」
「是喔、我覺得有個人舞的還不錯,那腰力搞不好可以改去耍劍花。」
「總要給其他人一些表現機會嘛。」
耿菽沒說的是這些被替換的人,通常就是被台下某個人給選走了,自然是不會待在台上繼續表演,而是跟著那客人轉去房間了。
這方法選人算是在南風院最簡單的消費了,而來格的門票就算是入場費,還能免費的觀看選人,雖然之後還要再付一筆開房與陪人費,這價錢比直接開房還要貴上一筆。不過這樣反而比直接付房錢抽到差籤來的好。
而這時間的格也會開始做簡單的服務,幾名人員拿著掃具在木柵格走動,除了掃除之外,也有人會收格內客人給的小費與小牌子,出入口也是大開,方便人們進出。
這小牌子就是用來指名用的,給了工作人員之後,沒與人有衝突的話,就可以開開心心的去開房了。
當然小牌子這東西早就在束修來之前,就被耿菽給吩咐收掉了,束修來了自然是見不著。而這個空閒時間束修也沒閒著,忙著跟耿菽分享剛剛幾人的表演,全然沒注意到這表演的目的是什麼。
束修跟耿菽講的歡快,卻是看到什麼突然頓了一下,聲音變的小聲。耿菽覺得訝異,順著束修視線找去,這才發現背對著自己的地方、也就是他兩座位隔壁的格子座下了一名客人。
看了那客人,耿菽這才知道為什麼剛剛束修會被嚇到。
這客人裝扮很是怪異。全身上下就那頭上戴了個竹編全罩笠帽特別搶眼,從頭到肩全是蓋著見不著,而來了室內也不脫下來,就這樣戴著坐在位上,一手還轉著一根翠玉色的筆棍。雖然沒特別說來了這裡一定要脫下帽巾之類,但是像他這樣的人耿裴倆人還是第一次見著。
南風院的工作人員一開始見著這客人進來,也是有幾人驚訝片刻,不過會許是訓練有素,剎那之間表情一轉就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
除了頭裝之外,笠帽人的行為也讓束修與耿菽覺得奇怪。
明明現在空的格子這麼多,他倆的位置也不是首選位,這人怎麼還偏偏要坐在他倆旁邊?
想的再多也不是自己的事情。耿菽回過頭就不再理會那人,朝束修問:「要繼續看下一段嗎?」
束修想了一下後說到「再看一下好了,如果還是那些表演的話,那再離開吧。」
雖然表演還算新鮮,不過表演如果還是剛剛那些表演的話,第二次就沒有什麼新鮮感了,束修也就沒什麼心思想看下去。
束修這樣說,耿菽自然是在樂意不過,畢竟主要的目的就是拖時間不要讓束修出去院外。
然而當耿菽正要說話時,一旁卻是有個聲音朝束修這邊插問過來。
「小兄弟、剛剛的表演不精彩、很無聊嗎?」
這聲音不是別人,就是坐在他倆旁邊的笠帽人所言。從聲音聽來雖然輕柔,但其中語氣有些嚴肅、命令的語氣,可能是有些地位的人士。再加上那隨意出言的態度,不難想像是位哪的上位男士。
雖然坐姿頗有些纖細謹慎,但南風院沒說只能男客進入,但是百位來客中,能有一位女性都不太可能了。耿菽怎麼亂猜都不太會去猜女性就是。
束修不比耿菽謹慎,雖然覺得這人穿著奇怪,但是基於人家發話詢問,也就禮貌性的回答他一番。
束修動了動身子,頭遶過耿菽身子朝笠帽男那邊道:「也不是不精采,就是同種表演看兩次,不都會覺得有些……恩,該怎麼說呢?也不是無聊,就是沒什麼想再繼續的意圖。」
對於束修的回答,笠帽男動也沒動,傳來的說話聲音卻是有些大聲,彷彿怕旁人聽不到一般。「我能理解這種感受。短時間重複的事物總是讓人覺得無趣。明明不是必要性的東西,為何還要重複兩次以上呢?」笠帽男說完這句還頗有感觸的輕笑幾聲,自此就安靜不再動作,彷彿靜止的雕像一般,這突然的靜止安靜,讓人以為剛剛的對話彷彿都不存在一樣。
正當耿菽與束修以為笠帽男沒甚麼事的時候,笠帽男動也不動,不!或者該說在笠帽內的頭有動,但是從外觀上來看卻是沒動作一樣。
「那真是可惜了!下一場的表演我知道會精采很多!」
那聲音默默響起,大的讓周圍的人都聽得見,但是耿菽與束修知道那是在跟他們說。
不過就算知道如此兩人也都沒有回話,就當是奇怪客人的自言自語罷了。
或是是見過許多客人的緣故,笠帽男的態度也沒讓南風院的人員難辦,更惡劣與汙穢的都見過了,這樣只是說話大聲的人,頂多讓他們刻意關注幾眼後,就不再理會。
笠帽男說完這話後,也沒再理會耿裴兩人,回歸到他那彷彿雕像一樣的不動境界。
實際過場的時間沒過多久,台上突然出現一名少男,他隨著細微聲樂奏響,緩緩地走到中間。
不知道笠帽男是熟客,比較了解南風院的出場安排,還是他真有甚麼過人判斷。從這名少男穿著與手持的道具來看,不用有什麼過人眼力的人都知道這場表演會很特殊。
這少男與前場表演的人大不相同,相比前面幾名穿著來說,這少男的穿著甚為暴露,上身一件無袖短褻衣,大片的手臂與腹部袒露在外,下身一件短禈,只遮擋了那男性的象徵。兩手拿的也不是甚麼舞技常見的緞帶與劍棍,而是一條金屬鎖鍊,鎖鏈長度不長,那少男兩手一舉一拉,台下眾人勘差一比,不過臂胸之距。
台下響起的樂聲不再是那種慢調子的絲竹聲響,而是鼓瓦之擊。穩定的敲擊節奏與漸快音樂,串起了彷彿戰歌一般的旋律。獨特點不只有這戰歌般的音樂,台上鎖鏈少男的表演更甚獨道。
只見鎖鏈少男用兩指扣抓著鎖鏈的一端,隨著那音樂節奏,將手上鎖鏈甩往自己身上!那鎖鏈彷彿是活物一般,隨著音樂或是繞過肩頸、或是繞過腿蹊,竟是沒有發出一絲金屬聲響。
笠帽男在旁沒有動作,但是彷彿看著束修他們兩人一樣問道:「小兄弟如何、這人比剛剛好多了是吧?」笠帽男的聲音在那音樂之下沒有被蓋過,穩穩的傳到了耿菽與束修兩人這邊。
「是不錯,比起剛剛的幾個人獨特許多……」
耿菽有些警惕這個突然出現的人,不理會還有甚麼感想的束修,就把他給往旁邊拉的遠了些,又冷冷地道「不過是換個道具罷了,尋常人練練勘此。」
對於耿菽的冷言冷語,笠帽男沒有任何動作,頭上依然戴著笠帽也不知道他什麼表情,是喜是怒不得而知。
笠帽男手上筆棍往自個手掌一敲,語氣竟是有些訝異「喔!這人、這般功夫卻是不知其技高如何?」語畢,手上筆棍往台上一指又道「仔細瞧瞧那些鎖鏈狀態。」
然而,一時間要人觀察甚麼,耿裴兩人硬是看不出個所以然,不過聽聞那笠帽男這樣說,台上那人耍的似乎真有什麼門道。
笠帽男貌似知道兩人看不出門路,不等耿裴兩人逕自在那解釋。
「鏈鎖環環相扣,緊而不鬆。肉身時時相貼,和而不咬。」
聽笠帽男這樣說來,這才覺得似乎有所道理。那鎖鏈看似指是在少男身上隨意環繞走動,但是卻是沒有一絲鬆和的情況,各個都是處於繃緊扣合的狀態,也因為如此,鎖鏈快速的在身裸身上走動,卻是沒有咬到一處肉塊或細毛,技術堪稱精湛。
雖然經由笠帽男的提點,耿菽也看出台上的人是有何能,但是對於旁邊的笠帽男也看出了一絲相識感,內心已有七八成知道這人是誰。
耿菽一方面不讓束修與笠帽男對話,更是挪了挪身子,擋住了束修與笠帽男之間,打定了主意要個冷處理。
耿裴兩人不理,笠帽男卻是沒有識相停嘴,仍然繼續著他的分析。那聲音是不大不小的剛好傳進了耿裴兩人耳中。
「要有這般能力,需要對於鎖鏈有極高的掌控,而關鍵點就在於他那扣著鎖鏈的手指,隨著手指的扣、夾、轉、搓等技巧……」
笠帽男見解說的是敏銳,但耿菽硬是沒怎理會,甚至還壓了壓束修,要他不要回話。
這樣的情況看似沒甚麼不好,一個願說、一個看似願聽,誰也不理誰,相安無事。然而事情卻是有所變化,讓耿菽是越聽越是忍不住衝動想讓他閉嘴。
「……肉體配合鎖鏈的柔軟度與下盤腿力。當然不僅止於台上的這個鎖鏈表演,點名入側後,無論是哪方都是饒有趣味。盤前,他那陽蹊漉穴,硬而不僵得夾的你離不開他;顧後,也能憑藉著他巧妙的指法,定是讓你穀道暢通無阻,脈元川流不息。還有……」
笠帽男的見解饒是由台上說到了台下,這不是耿菽要帶束修來看走劇的目的。他是來拖時間,不是來讓束修升慾火的。
耿菽很肯定一旁束修肯定是聽了一字不差。耿菽眼角餘光撇見著束修,只見束修雖然在旁邊彷若沒有聽見一樣得看著台上,但是臀腿卻是開始隨著那幾個詞句不安分起來,時而左塌右立、時而立膝束腿,坐姿是一變再變。
耿菽定氣一吐,憤目怒臉一轉,正打算出言制止笠帽男的言語,卻不料鎖鏈少男一個擺動,一轉身就隱沒到後台下了表演,現場戰樂突然一轉變的輕快俏皮起來。
而笠帽男一句「……還有那個體力與、哦!這組的表演我特別喜歡。」就打斷了原本想要制止發言的耿菽。
音樂變得唐突,笠帽男說完也沒再發言,竟是讓耿菽想罵得話語又是忍回了口中。
隨著那躍動感十足的音樂,走上台的是一個滿身肌肉的短髮男子,從臉孔來看不過剛過結髮加冠,也不知道真是如此還是他有張童顏?那身板與臉孔甚是不搭,彷彿是接合一般的詭異。這男子身著短絝與無袖褻衣,如果衣裝得當的話,或許看上去只是個高個男子罷了。
這男子如同剛剛的鎖鏈少男一樣,他可不是空手而來,但拿的也不是什麼小道具,而是一個單手抱距大的寬口甕。
這寬口甕看上去是個酒甕,寬口處還用個喜紅給封個牢固。而這肌肉男子就拿著這個酒甕隨著音樂耍玩起來。
男子僅用一掌壓著甕口就給抓拉了起來!那甕一下是在掌中自轉繞圈、一下是隨著手掌繞著平移,寬口甕靈活得像是自己在男子身上躍動一樣。雖不知道這甕有幾般斤,但就算是個無物木甕,要耍成這樣也是不容易。
這寬口甕的表演並沒有多久,隨著音樂的一個結尾收聲,男子雙腳伸直大開站著,五指撐著甕底,臂肩一撐,高舉著寬口甕,形成一個開天立地般的姿勢,說有多神奇就有多神氣,男子氣概與力美的展現無不缺一。
束修覺得精彩,見表演結束正準備拍手鼓掌,卻給一旁耿菽給擋了下來。
「別拍手。」耿菽在旁一手抓住束修剛舉起要靠合的雙手。
「表演的好看呀!怎就不給點掌聲?」束修還往旁邊遠處的幾人看去,看反應如何?
怎料周圍幾人的確是看專注,不過卻是沒有一絲歡喜與快樂,滿臉說不出的怪異。叫好的倒是有幾個,但卻是沒半個拍手。
「不好看嗎?」難道是自己眼界太小?
「沒什麼,在這裡沒這種拍手習慣。」
束修與耿菽兩人的舉動雖小,但一旁笠帽男貌似注意到了。
他動了動身子半撐著身子轉了過來。耿裴兩人看上去也不知道笠帽中的臉是否有跟著轉過來,只聞那笠帽中傳出聲音道「小兄弟是第一次來南風院?」
這問題顯然是朝束修而問,不過不等束修回答,耿菽自是不客氣地回了一句「與你何干?」
笠帽男聳了聳肩座了回去,也沒多理會耿菽的冷言冷語。
「在格場可別隨便拍手呀。尋場技完拍掌鼓是勵,南風術後貼手點是單。」
耿菽這麼瞞著不說,卻是被笠帽男一口道出。束修這才理解這是甚麼來由,而周邊人的那些人縱然表情有興趣,卻沒半個拍手是何種意義。
束修看的是技術、是表演,感受的自然是快樂與有趣;旁人看的是身體、是能耐,感受的不過是色慾與妄想。
若束修剛剛手掌真拍下去,或許演的就不再是什麼手指抓重物玩了,玩的就會變成拍手被請上台的束修了!
束修辦紅著臉龐,有些尷尬道:「我哪知道……」
這話說的小聲,約略只有旁邊的耿菽聽得見。不過笠帽男貌似也聽見了,他搖了搖手上的翠綠筆棍,轉了一圈像是變戲法一樣說道:「表演可沒結束呢!剩下的才是重點。」
笠帽男的話語說得讓人不解,然而台上音樂與他的話語彷若貼合了在一起、掌握得恰當,笠帽男語氣剛落,台上一個突兀鏘響,肌肉男子掌中寬口甕的封紅竟然凸了一點起來,這甕中想不到竟有活物!又是一個鏘響,那凸點又是立起、又是一個鏘響,封紅被那凸點給撐破,而封紅一破,鏘響不再單敲,而是連續的擊打,響起一陣波爛與高潮!
那寬口中的凸點仔細一看,不是何物而是一雙腳趾。那腳趾隨著連續的鏘響,接連的從甕口越竄越高,從一腳掌到小腿、從小腿到大腿,最後就見甕口直直的伸出了一雙皎潔美麗彷彿不是活物的玉腿!不等眾人細看那腿,台上音樂又是一變,那腿隨著音樂一個彎曲,腳掌輕貼著甕口邊,藏在甕裡的那人一個魚躍挺身,下腹、胸口、頭顱、雙肩雙臂、最後是手掌一出抓住甕口,形成一個四肢著甕,彎身稱腹的挺立姿勢!
這姿勢撐的不久,彈指間這少年就從高舉的甕口一躍而下。這跳躍不似活物一樣,彷彿哪來的地仙一般,柔軟的衣物貼著身子在空中緩慢飄動,著地的裸足觸於地面在台上輕細無聲。平坦的身軀穩於空間在房中散發芬芳,挺邃的眼眸定於眾人在心神撥弄不已。
這少年的驚豔出場,別的部分還先不談,就說這走劇的氛圍卻是明顯變了許多,那音樂不在是正調定曲,而是輕挑熱騰。而那少年就隨著這音樂在台上舞動起來,而剛剛的舉甕男子卻是悄悄的不見蹤影。
若說前面幾人的走劇穿著料少涼快,那現在挺甕少年穿的就是輕薄裸露。那褻衣無袖無腹先不說、那褥絝無腿下腰不講,就談那整身衣物隨著那室內火光,讓少年獨有的初育身子是若隱若現,看去是精而不壯、肉而不肥!隔著褻衣之後,隱約見著連結胸口兩端的一線,那一線在少年舞弄身姿之下,在褻衣之後隨著光線於衣後微微閃耀它獨有的金屬折光。轉眼其下,少年的褥絝腿股本是暴得隨意可見,然隨著少年舞姿大開大合之下,那輕薄褥絝之後的腿根,卻是朦朧可見在其兩者間的垂囊物狀!垂物隨著少年的舞動時上時下,肆意在腿間自由撞擊著。可惜的是,或許少年未長、年歲為足,那物看去卻是微不可視,儘管褥絝在怎麼短的不著腰腿,但那陽垂就是不會見其暴露半分姿色。
而就在台下幾名客人心中暗道可惜之時,那少年舞姿一轉,突然就是單腳抬腿一踢,又單腳原地快速轉了一圈!一個一字馬姿勢快速出招又快速消逝!眼尖的幾人卻也沒錯過這抬腳轉圈的一剎那。薄可透身的褥絝自然是擋不過那些眼尖之人,兩腿間的垂物都可視之,而那抬腿轉圈之後,兩股間的縫隙又怎會錯過?只見兩辦肉股在薄布之後隨著一馬腿分而大開,隱隱綽綽不不見那想像中的幽穴,卻見又是一垂物在那其間!不等眾人確認半分形色,那身子一轉、腿股一合,又是不見其中。
原以三腳單口鼎,知其單斷暗自惜。卻道六足從犬獸,不知單尾判眾異。
這台上艷春暫且不續,台下耿、裴兩人卻是開始坐不住身子。
別說少年開始舞動之時,耿菽在少年剛從甕口跳下之時又知道這場表演早已開始不單純,而這表演內容當然也超出自己原先的預期。
這情況當然讓耿菽快坐不住身子,他甚至都有股衝動想要跳上台阻止整場荒淫的演藝。不過這股衝動自然是只能在心中想想罷了,真跳上去阻止,別說是當面砸了景家場子,不等人家來到現場,現場台下的幾名客人就會先把你給砸了!
你阻止不了,難不成還不能逃?轉過身,耿菽就想拉著束修離開現場。怎料耿菽轉過頭看向束修,就見束修是迅速的把身子往前屈的可以,兩手擋著絝襠部,臉上是一路紅道耳根子!耿菽還沒說個半句話,束修一見耿菽要開口,趕著就插話道:「耿菽,我、我去一下清廁」也不等耿菽說上什麼,連手都沒拉到一下,束修一溜煙的就跑了起來,等到耿菽從束修的生理反應與話語回過神來時,束修早就跑的不見身影。
見束修突然不見,耿菽自然是急著起身要去找人。怎知意外沒想到的話語卻從耿菽旁邊傳了過來。
「急甚麼?早讓人跟著了。」這話說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剛剛坐在他們旁邊的笠帽男。他正拿他的翠綠筆杖在那轉著,頭上依然是那個看不出面孔動靜的竹笠帽。
耿菽當然是不想理這個人,見笠帽男沒再發言,轉過身就要離開。不料耿菽一站起身,就有兩名看似工作人員的人堵了過來,那身子站在耿菽要走的道路上,耿菽繞哪就走哪,這什麼意思是明顯不過。
耿菽不想把事情鬧大,轉過頭就朝後面的笠帽男怒氣沖沖問道:「你這甚麼意思!明目張膽的擄人嗎?」
笠帽男對於充滿怒氣的耿菽卻是有些意外「擄人是甚麼我可沒做,我想你是誤會了什麼,我只是擔心小弟的安全。畢竟,單純的男孩在這已經很少見了。」
「跟我說你派人跟著?那我更懷疑你動機不單純!」
「你不相信我,那我也沒辦法。等等你小弟回來就知道了。不過在那之前,我們需要單獨先聊聊。」
說到這裡,笠帽男好似想通了甚麼,又道「說到這份上,你好像早就知道我是誰了。」笠帽男說完就脫下了罩在他頭上的那個竹編笠帽,露出了他毫無遮擋的面孔。
這面孔並未完全顯現,男子臉上還有一個翠綠色長帶遮著他半張面孔,看上去與他那高盤而起的馬尾髮帶是同一個款。
看這樣貌,尋常人客或許不知道這個男子是誰,耿菽就不同了。
那個遮罩著眼臉看上去像是盲人一樣的臉孔,再加上翠綠色的頭件以及剛剛拿在手上的綠玉筆杖,還有能力自由招呼現場人員與臨時竄改表演的人,這怎麼想都只能是景家大老才有可能辦到,而現在南風院裡最大的景家人沒有別人,就只有景煜。
那個耿菽來南州芳樂最想找到的那個人,也是耿菽進日清冥與束修碰面前,千方百計最想找到的人。
ns3.15.203.16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