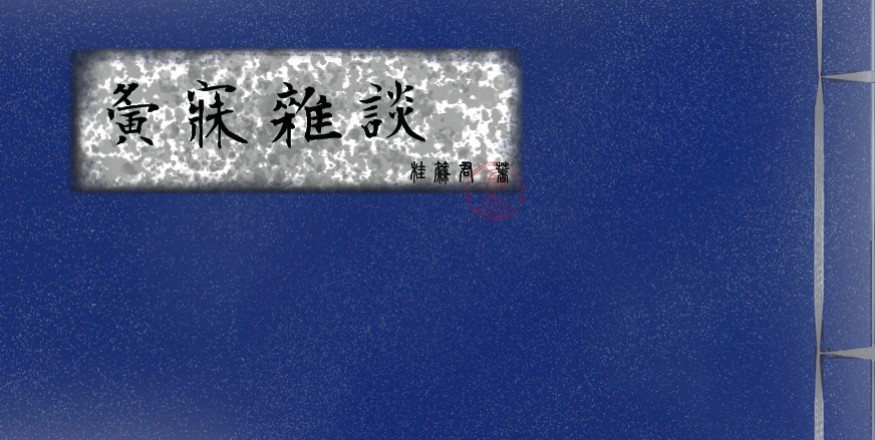芳樂港口之內停了許多的船隻,不過比起上次封港的滿船情況比起來,現在這數量顯然少了許多。儘管港內還有足夠的空間,但港口之外還是有許多的船隻停在那裏。這些船無非就是沒有太多的資金可以進港,又或是因為上次的封港事件而無法傳遞進港文件的船隻。
港口之外其實也沒什麼不好,對於那些沒有太大資金、送貨量不大的船隻來說,與其停進港內付一大筆費用,倒不如停在港口外還比較省支出。當然在芳樂這種大港就算是離港的水域,自然還是要付一筆「停靠費」,不過比港口內還是便宜太多。
真要說停港口之外有什麼缺點的話?那就是上下貨不太方便、人員進出芳樂陸地上不便,諸如此類的方便問題就是。
云丘號就是在這外港的其中一艘。已在這停了許久的它,如今也要在幾日後離開芳樂這裡返回它的老家。
而準備離港的船隻,自然要準備的事項並不少。好在云丘號這次返程並沒有要載滿貨物回去,所以那些上貨的方便問題基本上並不存在,申報文件、填寫算計、數日子什麼的就免了大半!不過像云丘號這種純航行不載貨的船隻,離港準備中最麻煩的事項也最欠缺的就是人員。
上貨出東丘時,除了原先船隊有的水兵,自然還會僱用一些船隊外的人,而這些人多半就是順道要到終點站的人。如今云丘號到了芳樂這個終點站,這些隊外的人自然是散了大半。而反過來說,通常返程也是同樣的道理,雇一些順到要回東丘的人才是。然而整艘船儘管後天就要出航了!但是在云丘號上的人現在看來卻是寥無數人,放眼望去毫無生氣,一點也不像準備要出航的樣子,貌似根本就沒有多雇多少人。
別說其他人見了怕,就連船員本身都有些擔心。
船隊中原有的幾名水兵剛搭上船,見到這空蕩模樣著實有些嚇到。
「船這樣沒問題吧?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云丘號這麼少人。」
「你前幾日沒聽說嗎?耿總的船隊要散啦!」
「我知道呀!只是有點意外會少這麼多人。這樣舵手位的班替會不會輪的很密呀?」
「這一聽下來,你根本就不知道多少吧?返航承順風,根本不需要划多少浬,再加上我聽人家說,這返程連貨都沒載多少,這船輕的可以。」
這水兵話剛說完,後頭另一人剛上來聽到,高興道:「那倒是不錯。前載那次往返回東丘,東西多的可以,就算滿帆搭著風,那速也沒快上多少。或許這次我可以期待會多一候到東丘?」
「扁臉你也回船上喔?不是說沒多雇人。」
這綽號叫扁臉的人來就不是船隊的,真要說算是常跟著耿菽船隊的聘雇人。所以這種雇員也要上船,讓本來船隊的人很是意外!。
「又不只有我!你看後頭還有人咧。」扁臉朝船緣外的船道比了一比。順著看去,的確有許多熟面孔正順著船道找船,搞不好就是要上云丘號。
「還真的咧!所以你是用僱水兵身分上船?」
「又沒貨,顧個屁!我是買票上來的,是乘客!我可得看著你們櫓舵呢。」
扁臉這話一說,雖然這話有大半是實話,但水兵們知道也是個玩笑話,眾船隊水兵皆是做個樣子噓聲一片,朝那扁臉鬧道。
一人邊噓邊無意的往船外看了看,突然是瞪大雙眼,朝旁人揮了揮手道:「我咧,我眼花了是吧?」
在許多人邊詢問邊順著那人看去,那人指著船道上的一人道:「那不是阮堯嗎?他也要登船呀?」
幾人望去船道那人所指的地方,的確是有幾人站在那走著尋船號,其中就有一個長得像阮堯的人。不過阮堯比起之前入港前的樣子,現在更顯疲態,不說原本的身子稱不上有肉,現在誇張點說彷彿就是有些乾癟一樣,身上的衣物看上去就像是單純套著而已,港口的風一吹,衣物就沒有支撐感的隨意散飄。
幾人見著了之後,也是有些議論。見阮堯那模樣還要登船?估計船在搖晃個幾下他人就要散了吧?幾人你一言你一語的說著閒話。
扁臉聽完幾句後,一臉不意外道:「人家老家在東丘,自然也要登船回家吧。」
「憑那身子還能做事喔?來芳樂這的時候我看他在船上都沒做啥事呀?這樣還要登船?沒點臉面呀!」這人說的直接,也不怕難聽,因為本就是事實,其他人也看在眼裡。
不過這話說下來,腦筋轉得快的人,約略就知道是什麼事情。
一人朝著扁臉問道:「他也是乘客?」見扁臉點了點頭,那臭嘴的也不管扁臉如何得知,嘴又是管不住的直接道:「他還不是欠張氏那兩人錢?怎麼還有錢買船票當乘客?」這問題別說扁臉,自然是沒半個人得知。
不過同樣是乘客的扁臉約略朝眾人給了點可能的方向。「這芳樂回東丘的船票沒你們想的貴,不知是柏老開的價還是耿總給的定。那船錢,你用從東丘雇來的薪,根本就不到一半,若是從云丘號來的更是五分及一不到。」
這錢自然算上去便宜,不過臭嘴也是有些不信「他欠的錢根本還不完張氏吧?別說五及一,十及一他都買不起!」幾人聳了聳肩,沒人知道阮堯跟張氏到底借欠多少。
「你瞧阮堯旁邊不是有另個人跟著?搞不好是新的『張老闆』呀?」
「或許他還完了吧?」一人邊說邊比了比自己身子。那甚麼意思,知情的人自是明瞭。
幾人在那猜測話聊,一下說若堯子帶病上船怎辦?一下說怎不你自己去試試他身子?無理又莫名的言論是亂鬧個不停。阮堯真是如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數天前,阮堯甚至還不知道云丘號居然還開了隨行船票這回事,這回東丘的船票還是從張氏那兩兄弟半送半給來的。
那是不知道自己被半軟禁在張凌山的住所第幾天的時候。
那天很是意外的張氏兩人都出了門,沒有半個人留下來看著他。而張氏兩人會怎麼做又不怕他逃的原因阮堯自己也很清楚,因為逃走沒有意義。
逃失敗了,那下慘肯定會比現在還慘!說不得的沒個全肢被賣掉。逃成功了,那自個也回不了家,家裡的幾人肯定會被張氏找上門。他不想這樣害慘自己的家人,不想像他爸一樣,讓自己的弟妹像他這樣承受這些事情。
在說了,張氏兩人除了吃喝拉撒睡覺之外,每日每夜的這樣輪番玩弄著阮堯,阮堯就算現在想逃,估計這身子也殘破得跑不了多遠。
阮堯甚至覺得脖子之下的所有部位都有所麻痺,似乎一點除了痛覺之外的感覺都感受不了。
阮堯躺在地上正嘗試著用自己的手戳著自己的大腿。大腿傳來的只有痠痛的回饋,甚至那肌膚回彈的血色看上去都是緩慢的不正常。
正當阮堯還想確認其他部位的時候,屋外走道的樓梯傳來不小的腳步聲。啪地一聲!房門口就給開了起來,開了的房門外站了三個人,最前方的兩位當然是房主張氏兩人,而後方還有一位全身包得緊緊的人,帶著遮笠穿著纏衣,阮堯見不著他樣貌與身型,當然是完全沒有印象。
張凌山一眼就望向了躺平在屋內角落的阮堯,見阮堯醒著,口中不屑的嘖舌了一聲。「小叔,你帶堯子去院裡端個水,再拿點衣服穿著。」張亦宿朝屋內一看,見了阮堯這模樣,也不難理解張凌山甚麼意思。叫阮堯起來都懶了,一手穿過阮堯的一肩一腋,打算扛著阮堯就要往樓下走。
張亦宿這一拉,阮堯自然是有些掙扎與牴觸,深怕張氏兩人又想對他做些甚麼,現在還有第三個人待著呢!
見懷中阮堯貌似想要掙扎,張亦宿語氣冷冷地在他耳邊道:「诶、別鬧,現在不想對你怎樣,但你還想回家就老實點,等等聽著安排就是。」張亦宿說完也不管阮堯聽不聽,半扛半拉著阮堯就往投下院子的井水走去。
兩人再回來房間的時候,房內張凌山與那不知名的人貌似剛好談了一個段落。
那包得緊緊的人看兩人回來,盯著阮堯就道:「就這人?弱不經風的。」
「這樣才好不是?不會被懷疑的。」
「怎不叫旁邊的人去?」
「你說亦宿呀?我跟他都不會再上船了,那自然是不可能。」
「……這事給你們辦真得行嗎?辦所怎把這任務給你們。」
「這不就是你來這得理由?」
兩人說到此就不再說話。張凌山與那人相視許久,貌似在進行著無言的談判,也不管房門外的張亦宿與阮堯還等著。
阮堯根本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尤其那話題好像有提到他這麼一點。阮堯朝一旁的張亦宿搭起話打聽起來「他們在說甚麼?」
無奈張亦宿根本不甩他,一句「你安靜。」就不再理他。
阮堯也只能這樣陪著亦宿呆坐在門外看著門內的兩人對視著。
片刻之後,也不知道他倆達成甚麼共識。明明兩人在那之後根本一句話與動作都沒做過,然而張凌山彷彿確認了什麼一樣。
張凌山率先動了起來!他轉了頭朝門外的兩人招呼道。
「亦宿跟阮堯進來吧!有些事情得跟你們說一下。」
張凌山易手比了比對面坐著的那人道:「堯子呀!跟你介紹一下。這位是常依先生,他是要跟你一起搭船回東丘的人,自然也是我倆的證人。」阮堯朝張凌山那介紹的手看去,那坐在對面那名叫常依先生的人。他不像剛剛進門時的那樣包得緊緊,現在的他脫去了遮笠露出了面孔。
這人看上去異常漂致,臉孔上的眼耳鼻嘴,一股說不出的長在該長的地方,彷若手藝高超藝師雕刻出來的面具一樣,真假得彷彿分辨不了。
若不是那眼臉還會張合、鼻息還若起伏,阮堯還當真以為那人帶了面具在跟他說話。至於其他的?阮堯也分辨不出甚麼特色,如果包得緊緊的是一種特色的話。
這人就算脫去遮笠,漏出來的也只有臉孔與一些些脖子,那面孔額頭之上的頭髮是全然見不到一絲!全都給他用布網給包頂在頭上,然而那布外也非包得緊實,而是有些鬆塌,看上去也不知道裡面髮量多少,說不定是個光頭也不准?
對著半帶著笑容的阮堯,常依先生嘴動皮不動朝他說道:「基本上你也不用管我是誰,在船上我們就當不認識。」這態度聽上去就是不打算跟阮堯有太多的交集。
人家不理,阮堯也不打算裡搭,反正本來就不是認識的人。轉過頭,怯怯地朝張凌山問:「那個,一起搭船回東丘這件事是指什麼?」
「我說阮堯,你那還欠著我們的帑票還有多少你可有算過?」
阮堯想了想,自個也不太清楚上下,這總共欠張兩兄弟多少,阮堯還是有個頭。但是自己還了多少?他卻是沒個底。
自個從云丘跑到芳樂的這趟薪全給了張氏,這樣算下來還欠多少,阮堯一清二楚。不過在船上榻上那幾次歡活,張氏曾說過一次可以抵他多少,這點算下來可抵多少,阮堯卻是含糊不清。
在船上那做了幾次,當然阮堯不會不記得,畢竟這關係於他欠的錢。然而,現在想來怎樣算一次?卻是全憑張氏說了算。這榻活幹了一次,三人盡興完後就算一次?張凌山可說不算數,這腳都沒下榻,硬是在天亮前都盡洩了幾次,直到下了榻才說是一次;這張凌山人不在,張亦宿自個壓著他來了一次算不算?張凌山可說不算數,他人都不在場沒見著,哪知道你倆是不是忽悠著他;這在芳樂房中幾人你戳我的、我弄你的,算不算一次?張凌山可說不算數,這事情開始時又沒說是要抵債,自然是你情我願,哪說得上次數。
三番兩次下來,阮堯有時候根本就沒意識,這活幹了幾次根本也不知道。現在張凌山個問他還記得欠多少?阮堯一時之間還真答不出來。
張凌山看他吞吞吐吐的半句話不出,也不等阮堯還在顧忌甚麼,突然就插著道:「行了!這欠了多少,我也不計較。我這麼說吧,我這有個活要跟這位仁兄辦,你跟著他要把這事給辦完,我張氏欠你的錢就一筆勾消如何?」
這條件聽下來,阮堯自然是有些警惕,一臉不信之樣。
張凌山看阮堯那臉也不多做解釋,阮堯會有這種反應自然在他預想之內。張凌山不多做甚麼保證與條件,反倒是威脅回去道:「你不做這活我也沒差,我倆這幾日沒回東丘的打算,你跟著我倆兄弟在這過的一載星霜,等到那時再回東丘也行,那這筆欠帳我也給你給算抵完。」張凌山這話聽來,阮堯可道開甚麼玩笑!
「這帳怎可這樣算!你不說過跟著你倆跑完這趟來回東丘的船活,可抵我全部債務一半?那這帳你要怎麼算?」
張凌山搖了搖頭,一副無可奈何樣。「這可不是我不想回東丘,是人家云丘號沒打算再運貨回去、沒打算再多聘水兵。這自然我沒活可做,這沒活可做就沒錢,這沒錢怎還給你算上抵債?」
張凌山這話一出,阮堯一時無話可說。這事情張凌山也沒必要騙他,這種事情跑去港口查看個一輪,不到幾刻就可以清楚的事情,沒必要拿這個說嘴。
「這……其他回東丘的船……不行嗎?」
張凌山嘴角不露痕跡的淺淺一笑道:「也不是不行,但這抵可只算不上你全部的一半,只得四分一。」
「為什麼!說好了來回船務跑一趟不是算我一半?」
「我不說了我倆兄弟短時間沒打算回東丘?你自個找船活回去了,那我見著不見著怎麼算?你是幫我辦事還是幫人辦事?」這話語聽起來有些道理,不等阮堯還要說些甚麼,回過頭張凌山這又道「況且我當時跟你說的是在『云丘號』上來回東丘一趟辦事,可沒說搭其他的船回去呀?你怎又道算你一半債務?」
阮堯放棄在跟張凌山嘴口舌,只道自己沒想清楚、只道上天這般不湊巧得讓云丘號回不了東丘。
「那你要怎樣算?」
「我這不說了?我也理不清這債該怎樣跟你算。所以啦!你跟著這仁兄辦事,辦完事情後,就算我倆債務倆清了!」
這話聽起來阮堯覺得很似划算,本來談好完成的事情給還一半帑,現在這事只做到一半不做了改作另一項,完成後算你還全,來回算去可謂少了四分一的活要辦。
但是阮堯對於張凌山還未完全的放下心防。
「跟著辦什麼事情,我現在可以問清楚嗎?」
這問題張凌山沒正面回答阮堯,而是把視線轉回到常依先生身上。
張凌山此舉可謂精明。做甚麼事情?可不是他說得算。且這事情做得成功不成功,對他又沒什麼影響,最後就算真出甚麼問題,追究上來。張凌山自認要撇清事情還是很簡單的,一句工作介紹人、一句經手就可脫身,阮堯與常依先生要辦的事情?自個根本不清楚。
張凌山甚麼想法、瞞著這個叫阮堯的人甚麼事情,常依先生哪會看不出來?不過常依先生沒戳破,反正他來這跟接「贈烏酒」的張凌山談條件,張凌山要交代給誰做?那自然常依先生這個半個任務兼見證者沒話可說,更何況常依先生自個一開始也沒打算跟阮堯說實話。
常依先生看著張凌山那臉想了想後,很快就想好一套說詞。
常依先生看著阮堯說道:「我這活很簡單,想必你也很熟悉才是。」
「熟悉?」阮堯不解。兩人才剛碰面,常依先生也只聽張凌山與自己說了幾句話,會知道自己熟悉甚麼?
「我特討厭一個人,所以打算對那人下藥迷昏他,順道趁他昏睡時姦了他。」
常依先生話說到這,阮堯就覺這活有些偏頭,還不等他開口時,常依先生又繼續詳細說了下去「你要辦的活就是趁他不注意時,幫我把藥下到他食物裡,就這麼簡單。」
「甚麼我很熟悉!這下毒事情我根本辦不來!」
「你要怎麼下藥我管不著」常依先生看了看張凌山一眼,又繼續朝阮堯道「我也沒說你熟悉下藥,我說的可是你熟悉被下藥迷姦這件事。」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的理當只有張氏倆人與自己才對,怎麼這個人會這麼清楚?
「你不用管我怎麼看出來的,反正這活你只管想辦法下藥,後面的事情你愛看不看、要做不做不關我的事,這活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辦?」
「這活我不……」
我不辦這話還未說完,張凌山可就開口差話冷冷道:「阮堯。你想一想你還欠我倆多少。」
「可是要我幫你下藥……」讓其他人跟自己有一樣的遭遇,阮堯還是沒有這個心做這種贓活。阮堯現在想的心坎,張凌山可管不了這麼多。
「我說的取巧些,你只管下藥而已,事後常依先生要幹前面還是後面都與你無關不是?」
「可是……」
見阮堯還是有些猶豫,張凌山腦中一轉又道「我這都忘了說!這活可是在船上辦,剛好這船可是要回東丘呢!你活辦完可是剛好回老家呢。哇、太方便了吧!這不剛好嗎!」
「回東丘嗎……」
「這你也熟悉喔!是云丘號呢!」
「甚麼!?你不是說云丘號沒有要運貨?」
「我只說云丘沒活要做,可沒說他沒要回東丘喔。人家可是有開順路票回東丘呢!阿,船票錢你不用擔心,常依先生根我會幫你出得。畢竟要一起幹活不是?這只不過你在船上動動手而已,簡單不過的事情了。」
張凌山怕阮堯還在猶豫,再次強調了幾句話。「不就讓人跟其他人歡了一場!你的債就全都沒了喔?」
張凌山那邪淫的話語,說的難聽極致。但是那債務全還的條件可是極大得勾引著阮堯應下此事。
阮堯想了許多,有些是自我良心、有些是善惡判斷。不管阮堯想了多少自己不應該做這種事,然而想到最後心中浮現的總是家裡那貧寒被人追債的環境,以及始終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家人。
阮堯想了想,自覺跟著張家這兩兄弟之後,自身早就在這黑沼中貼遍泥膩,又何嘗差上一片沾?若這一沾能讓自個脫離這沼,換個人那又為何不可?自個過不了日子還有甚麼道裡,管其他人過不過的了日子?
阮堯想歸這麼想,但是不知道是自我的譴責還是留了點良心,阮堯還是不想跟這事情牽扯的太深。
「我、我這只負責下藥,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知情喔。」
張凌山見他答應,哪還管他說甚麼傻話。怕他又拒絕,趕忙是連忙點頭稱是。
「那是當然,你就做你的事就好。」
「那……你們,那個姦、我是說事情辦後,人家醒後怎樣也與我無關喔。」
張凌山沒多說什麼,他眼神快速的朝常依先生撇了一眼,沒讓阮堯發現自個還有甚麼事情瞞著他沒說明白。
畢竟在場,除了阮堯之外的三人,都知道根本就沒有甚麼睡姦的事情,人家壓根就不會再醒過來,根本就沒有甚麼「事後」了!至於跟你這個下藥人有沒有關?那要看常依先生善後做的如何。
常依先生見張凌山那邊把事情說開了,也有人要負責陪著上船完成這任務,也就加減表態一下。
「你只管做好你要下的藥就行,事後發生甚麼,自然與你無關。當然我話說在前頭,你下藥怎麼下的我管不著,若被人發現,後面事情辦不了,我也不會認這事情。」常依先生說完,反過來瞪了張凌山一眼「也就當這『事情』沒完成。」
對於常依先生的反擊,張凌山一副無所謂。
「東西你給、人我提供,事情成不成,你人都在那了,不該成也該有辦法成吧?」
常依先生低聲哼笑了一聲道:「我還沒聽過哪個委託還需要委託人自個上手的。」
「那你大可不用上船確認,就等結果就好。」張凌山馬上回嘴道,全然不怕得罪委託這個贈烏酒任務的人。
因為張凌山知道這人肯定等不起。
雖然張凌山不全然知道這人發這個贈烏酒的任務是為了甚麼,也不知道這事情的全貌是如何。但是他猜得出這人是誰派來的,也約略猜道這種大家子弟有這事情又是為了甚麼。常依先生說是常依,自認藏的好,殊不知有點人面的都知道這常依是誰。
贈烏酒這委託失敗對張凌山來說沒什麼損失。畢竟是黑單委託,賠償也是私底下說,自個頂多跟阮堯切割切割就沒事。而張凌山更篤定,若事情失敗了,別說自個要賠償,常依先生那方肯定得跑路,哪還管的自己要不要賠!
常依先生定是知道這點,所以他才要陪著接單的人一同到現場確認,甚至自己搭個一手收尾確認結果真假。
兩人都知道對方肚裡懷著甚麼鬼胎,但卻又不想說的太白戳破這無意義的面子。最後只得像現在這樣鬧鬧口舌壓著對方。
然而不管兩人怎樣說,張凌山這方卻是佔了較大的優勢,讓常依先生無論怎麼說都壓不了張凌山幾分。不是張凌山有理,而是他佔了許多便宜。
見自個沒上幾分風,常依先生也不想在這給人鬧著嘴上玩。常依先生最後撇了幾句後就打算走人。
「反正委託也就這樣定了,人事物都備齊,就待幾天後開船把事成吧。」常依先生語畢,轉過頭看了看阮堯這個陪他上船的人一眼。雖然心中頗是看不起這人,但是也就只能這樣改不了主。
「開船前我們港口再見吧,船上就當我倆不認識。」
常依先生說完那個遮笠一戴上,整了整頭身儀態後就出了房間。
事情鬧了許久,四人在這說了多久?也就只有日炎跑了盡沒多少才得知。
然而就是說了多少事項,張凌山也沒說多少細節。短短一句話「藥給你戴著上船,你想辦法下藥,他最後辦事,就這樣完事回東丘。」就給結。
這藥甚麼樣?怎麼想辦法下藥都沒給說明,阮堯這個生手哪還有甚麼手段給人做手?
也就張亦宿在旁給他說了幾手簡單,讓他有些想法上的基礎。
阮堯在那邊想著可能的情況,在腦中模擬著張亦宿說的方式時。卻突然想到了這事情最關鍵的地方。
「那個……我是要給誰下藥呀?」
張凌山冷冷的把責任推給了別人「你到船港問常依先生吧。看他討厭誰就給誰下,看他喜歡幹誰就給他幹。」
張凌山說完,不管阮堯還想怎個想,拉了張亦宿就打算去吃晚膳。搭了一句要阮堯顧家就離開了那房。
兩人一路走著卻是沒多說幾句話。且是有一搭沒一搭的亂說著。
「你怎還有心教他下藥要下在哪?」
「反正以後都見不著了,想想以後都沒這麼方便的道可走,就當送他最後一個禮而已。反倒是你,甚麼時候打算回東丘?」
「還回東丘?我連芳樂都不想待。等他倆啟航後我們就離開芳樂。若那事真的成了,肯定會有人追查到東丘那,常依先生那邊沒準也會找上我倆。北鬧事、東不成、南不待,我看我倆到西原去好了。」
「西原?那可有多熱?真要去呀……」
「你還要命嗎?愛惜自個身子吧!我凌山做這貸做的久,自然有我的理。」
「……」
倆人到了攤,點起東西來吃。攤上說了甚麼?卻都與路上剛剛那些話無關,顯是心不在焉、意不在此。
ns3.145.8.23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