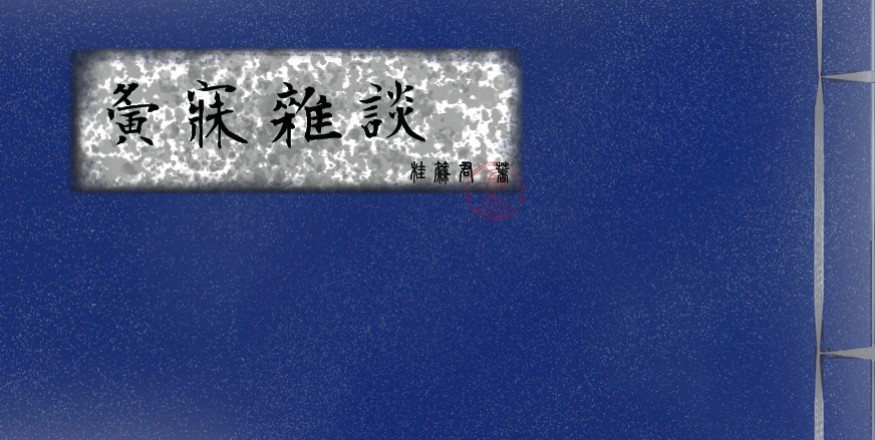8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qvZqeicAU
一絲淡淡的鐵鏽味在樓梯間蔓延,又被燈油味覆蓋,鮮紅的眼神沒有繼續待在那上方匍匐等待,而是隱沒在他身後的漆黑空間裡消失。
至於嗎?束修默默得想著。這肅氣強烈到束修都下意識得擺出備戰的姿態。
這肅氣來的快、離開的也快,隨著上面那人離開後,這氣息與氛圍也跟著漸漸消散。隨著上面那位肅氣之人的離開,樓梯間的人這才敢開口閒談,原來剛剛的暈眩根本是裝的!不過看上去傷口到都是真的。其中一位剛被丟下來的人,看到提了燈站在樓梯口的束修,好心的提醒了他一句
「這位仁兄也想要上去嗎?我勸你放棄吧!葉隊那身手真是太噁心了。」
此話一說,眾人紛紛附和,都勸束修別犯著苦去受罪,有些還帶感想與評論,順時氣氛緩和許多。
「嗚、噁……我的肚子還有點不舒服……」
「甲板上一點光也沒有,這偷襲太陰險了。」
「嗚嗚、我都看不到他打哪出現的,就被戳了一腳,跌回來了……」
這群人搞啥呀?束修都不知道要對他們安慰還是責罵了。還想提光上去?這不更明顯?肯定比不提燈上去還要快被踢回寢間。不過怎這麼多人都想上甲板呀?都跟他一樣想散個步?
「你們怎都晚上想跑甲板呀?乖乖在寢間不好?」
「……」「……」「……」
眾人一副〝你傻了嗎?〞的表情看著束修。周圍一群人不發聲的氣氛真不是滋味,束修也不解是啥情況,不過看來這群人應該都是有同樣的目的,要不這麼有默契的沉默還真是少見。
好在這沉默沒有持續太久,旁邊這人開始跟束修說明原因,其他人倒開始群群聊起天來。這人看束修貌似比他小也就隨口說說了
「弟兄,你做跑船的居然不知夜歌漁願?那你真是白跑了。」
「等等!你這傢伙不是在甲板上亂晃的人嗎?」一人認出在下錨停駛時的束修,不過這群人並不知道當時在觀測台指揮的就是束修,只當他是清點時不知入隊的新跑船員。束修也沒否認也沒澄清,當下直言道「什麼夜歌漁願?我是真沒聽過。」
日清冥還真沒教過這東西,不過說不定只是剛好他沒在課堂上時教過的內容?聽聽這東西也不吃虧,況且自從上船之後,很多事情他自己都不太清楚。
看著眾人陣陣私語一番,深怕自己又可能在甚麼地方說錯話,束修立馬不恥的雙手一揖「小弟不才,有望哥們釋義。」
一旁一位大哥看束修還挺有教養的,搞不好是個來跑船賺錢去讀書的人,也就態度緩和點的開始從頭講起這夜歌漁願的來由。
「這夜歌漁願呀!最早是在十幾年前才發生的事情,且說是真是假先不談,給個希望、說個軼聞人們總會想試試、想看看。」
大哥邊說邊坐在樓梯間,束修看他坐下後還拍了拍旁邊的樓梯段,也就點了點頭坐了過去。看束修坐定後,大哥繼續接道
「事情是這樣的,在某個地方有個落魄的跑船人,雖技術在身、不怕沒活,但沒伴沒家的,事事下來總有股空虛感,然而世事如此、他也無可奈何。不過過了半年,這傢伙卻不知怎的突然走運了起來!不但得了大筆的錢財、還在一地蓋了宅院自個做起生意,漸漸的跑船數也減少、聽說還在該地取了個美嬌娘!周圍的跑船夥伴各各自當羨慕不已,熟識的還想跟他討點關係,問問他的生財之道。」大哥頓了頓節奏、緩了緩口水。看來這故事貌似要進入轉折了!大哥身軀向前、吸足了氣再次開口,語氣興奮激動,口水說的噴飛自己都沒發現。
「怎知他說,一次在外跑船,晚上閒來無事在船上哼著小歌釣夜漁。然而那晚不知怎的釣不到半條魚,就連那沉標都沒怎麼沉過,一個時辰過後那跑船人覺得無趣,也就收起魚竿打算睡覺去了。不料當他想走回去的時候,身後一道陌生的聲音叫住了他,回頭一看甲板沒半個人!叫喚聲雖小卻不停止,那人才發現這聲音居然來自船外。」
「該不會是水鬼、幽靈一類的吧!」
「弟兄、你想多了!不是那類疫邪之物,那聲音雖來自船外,卻是紮紮實實的從海水中發出。那跑船人透過船緣往外一看,水中居然是一位赤裸上身的男子朝他揮著手。」
「當時我聽到這故事,換作是我?我老早就跑掉囉!」「我聽到的倒是個美女在揮手。」「那場景怎麼想怎麼奇怪。」
不知不覺,束修與大哥周圍的那些旁人,皆是或坐或蹲的在一旁聽他們說故事,雖說這故事他們自然是知情,但是八卦傳聞總是加油添醋、百變萬千,從另一個人口中說出來總是不同樣貌,自不覺得會想去反駁或推敲一番。束修也很是好奇,大晚上的一個的人在海水中叫喚豈不奇怪?就算在皇國最南方的沿岸海區,晚上的海水溫度一樣冷得嚇人,更別提這人還赤裸著上身了!束修打斷還在討論推論的眾人,繼續問道
「那這跑船人怎麼了?真不是疫邪之物在水下叫喚交替?」
這大哥不顧其他人還在討論是男是女,繼續跟束修講著後續
「且不論這人到底是怎樣,這水下叫喚到並非是個壞事,當那水下人看到跑船人注意到他之後,往船上投了一個小袋,說他唱的歌很是讓他懷念,這身外之物用不著就給他了!那跑船人取袋一看,袋中盡是金幣,抬頭一看那名男子卻遠遊而去,男子身後水波陣陣,跑船人細眼一看,那男子下半身居然不是雙腿而是尾鰭!」
「鮫人?」束修插話一問。皇國之外異族居多,海外多個魚獸一類並無奇怪,束修在北嶺就曾見過幾次。
「小弟真不愧是第一次跑船,這鮫人雖有,但樣貌可不是這樣!臉孔立體、身無鱗甲、手間無撲、支節無鰭,還會說人話,這水下人絕非鮫獸一類。」
束修聽這大哥這樣分析,倒也覺得合理。
「我聽說是個碩乳美女,這鮫人雌性可沒碩胸一說,男女皆是平的。」一人在胸前畫圈擠了擠道
「或不這某人獸慾太大,一時揮霍向海,這水下人是個異種!」另一人一掌虛握在雙腿間還上下搖了搖道
「總而言之!這跑船人就藉著這些金幣起家,過著圓滿的生活。而這晚上唱歌有錢的故事也就因此不脛而走。之後只要有人跑船,都想在晚上對著海面高歌一曲,想看是否有個水下人拋錢上來。」
大哥趁著話題沒跑沒歪之前,草率的為故事做個總結。語畢還感慨道「原本聽說耿船長的船沒夜哨、沒夜活還可以盡情的試試夜歌魚願,怎知連上去甲板都這麼難……」
還在討論的眾人聽他這麼一說,紛紛唉聲嘆氣,跟著感嘆。
「我聽說在南海這邊唱機率最高的說。」束修無言,怎這東西還有分地區性呀?
「我連要唱怎麼樣的歌都打聽到了!」束修震驚,這還挑曲目唱的!
「我不想試了,大不了候個幾天、再找多點人在說。」
「今天我不想搞了,明早還要搬水,都不知幾時來著,來去睡吧!」
「我聽說前輩有人帶雀牌來玩耶 ,賭不了夜歌、要不跟他們賭個一把?」
「甚好甚好!」
一群人邊說邊起身的離開樓梯間,束修連帶也被人群推拖著走,儘管他一直強調他全然不知雀牌是啥也不會玩,依然是被眾人拉回著去寢間。
不過這看似還算愉快的氣氛,很快的就在半路上被打斷。
「唉呀!這不是我們的旗總大人嗎?」一道叫喚聲從走道另一端傳來,雖然不大聲但在夜間卻是清晰不已。
隨著聲音的傳來,走廊那端也走來了三個人。三人一前二後的隊形行走而來,叫著束修的是這個走在最前方的男子,束修印象中有在後廳吃飯時見過他,當時這男子也是留下來說要看排表的一人。兩群人在走道撞了個著,前面這名男子長的與耿菽超不多高,群人面前也數獨高一頭,一身被汗微微浸溼的褻衣,透的身軀直貼著衣物,壑溝分明,下半身更是只穿著褻袴一件,也是濕的直貼身,凹凸真切。後面兩人皆靜默不語,左邊一人手托著燈油,另一手攙扶著旁邊的男子,盯著束修這群人看,但神色自然,不樂不怒。這兩人倒是不比前面男子壯碩,但也不比束修矮,衣物倒是穿著整齊,至少有穿個短內搭與長袴,不顯其軀。這被攙扶的男子束修認得,雖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這男子的確是剛剛在行春宵之事的人,就是那個與束修撞對眼的弱冠。該弱冠汗出如漿、氣虛息弱,也因為停下步伐而抬起頭來看著束修,當下蒼白的臉孔頓時又開始泛紅。束修與他對看著不說話,看他臉色泛紅就知道,這偷窺一事是被發現了!不過前面這名男子似乎尚不知情,看著束修沒接話,還以為束修被他嚇的發楞,一旁眾人也是一臉驚訝,殊不知束修幾人不是被他嚇,束修驚的是怕弱冠說出偷窺之實、眾人驚的是束修旗總一事!
「我說,你們一群人的不會想上甲板吧?還在做那種不切實際的事情。」語中竟是嘲諷與貶低之味。
「那又如何?凌山你別說沒做甚麼勾當,船上查不到就算了!到芳樂我看你怎麼辦。」說故事的男子挺身站了出說話,有夢最美,總比幹些下三濫的手段好。不過男子感頂撞凌山主要是一時口快,但沒膽敢把事情挑明了說,只期望現實能幫他打凌山一巴掌。
「隨便你怎麼說,反正你們都沒實質證據。」凌山卻是兩手一攤無所謂貌。眼神一轉,朝著束修看了過來。他不討厭跑船人、倒是很討厭這些走學術出來的兵家子弟,都是一個樣,一個正派衛道之樣!
「我說裴旗總,你要不晚上亂晃,是想找人陪你去夜間叉魚是吧?」
束修一驚!也不知凌山是偷聽來的還是聽旁人說的,這事居然還傳開了!
束修臉色雖紅,但是跟揭露魚鉤一事的羞愧來比,嘲諷所帶來的怒意還是佔了多數。不管後面眾人之意,隨口就編了句話「我叉不叉魚不關你的事!我帶著他們回寢間睡覺罷了。」
「是嗎?你高興就好。亦宿走了。」凌山不打算多糾纏口舌,有氣到束修就滿意了。喚了喚後面攙扶人的傢伙就打算走了。
「怎麼?你們也要上甲板?」
「裴大人你誤會了!我凌山辦事再有力,卻也拚不贏甲板上那不要命的傢伙呢!我看也只有耿船長可以搞得定他了吧?哈哈!」凌山話中有話,狂妄卻不失真實,語畢也不等束修回答就打算走人。他人也不攔著他,見他要走趕忙讓了個路給他們三人過,看著三人的眼神除了畏懼還帶了點憐憫。
「等等!你們扶著他還要去哪!」束修倒還有些擔心那名弱冠,都被他人弄到身子這麼虛了還要被他人拖著走,深怕等等又要出甚麼事。旁邊大哥看束修這麼問,倒是拉了拉他的外批袖,用嘴唇不發聲的道「別問太多。」
束修這話凌山也是應道「裴總別擔心,有些人也是第一次上船,這後輩也是第一次,睡覺摔了個床,帶他擦個藥。若是裴總有需要叉魚我也可以幫你,噗、哈哈!」邊說邊伸出一指朝空中繞了幾圈,不帶善意的笑聲也漸行漸遠。
眾人見凌山三人走遠,緊張不快的氣氛也隨之消散
「不知弟兄、喔!不知是旗總大人,剛剛失禮有待包涵」說故事的大哥突抱拳施禮道,旁邊他人也紛紛鞠身。
「你們!……別這樣,我這旗總啥事也不熟,大家就當弟兄朋友一樣,好嗎?」
「旗總以親代屬雖善,但禮少不可為,甚知。」故事大哥言下之意是諾了,但是位階關係依然不可踰越,以免亂了行事準則,並以此提醒束修,此舉雖可但須慎行。這禮行完,口頭諾了也就過了!私底下大家一樣是朋友。
「這凌山我看是個老手。大家都很熟他?勾當又是怎麼一回事?」
「旗總有所不知,這凌山是東洲張氏一族,連一旁攙扶人的也是張家的,是凌山的叔伯一輩,這張凌山在跑船人眼中很是遠名,專貸錢給其他跑船人。」
「東丘不是葉商最大嗎?沒聽過東洲張氏還有錢莊的。」這話束修可是清楚不過,說商,錢脫不了關係。裴家自個在北嶺也有裴武錢莊,一看就知道是裴家開的,東丘最大家的錢莊也是四商之一的葉家開的,葉文錢莊。至於這張氏?聽都沒聽過。
「這張凌山可不是開錢莊,但貸錢可貸不少,也從不在東丘路上貸,專帶年輕一輩的跑船人。」
「也只能騙騙那些舞象了。」
「可憐堯子了……我明明在上船前勸過他了。」
「凌山這人錢也不知哪來的?」
一旁眾人跟著混談補充著。
束修聽眾人雜談這才梳理知情。這張凌山可不是普通的貸錢商,專貸錢給那些剛入行的跑船人。這些跑船人新手不懂這行,總以為事少錢多,殊不知力氣活多,整趟船跑完活沒做多少,自然上頭看著給的工資也少。一些過不下去,船約沒到期還缺錢的人就想貸錢過活,這時就會被凌山給找上。
「找他貸錢太危險了!這傢伙利息開的雖低,口頭上說還不起沒差,私底下卻叫人用身體還,真是不安好心!」
「阮堯也沒辦法,他在南洲還有幾口小的要養,上無父母、旁無親戚的,無份無職一般錢莊也不貸他……剛看他那樣子,唉、當初真應該阻撓他來跑船的。」
束修心想,看來他剛剛偷窺到的就是他們口中所說的賣身還錢了!本以為這事只會發生在樓欄之人身上,怎知張凌山這人還把這事搬到跑船上了!
「這人怎沒被官辦呀?」
「你別說沒被辦,上次在南州被人關了,我看他不到一天就出來了!你能說什麼?」
「裴總有空看到堯子也勸勸他吧。」
看來這是不簡單,束修口頭諾了諾,心中卻是在分析思考這事。
南洲被關還能放出來,這說明他背後有靠山呀!但有靠山的話還需要跑船做啥?單純為了龍陽分桃一事?雖說跑船皆以男性居多,但要找男子非沒必要至船上找,有靠山還怕沒地方找?這事看來確有內幕。
束修想著想著,看到寢間一人冒頭出來,眾人走近一看,這才發現是萬幸叔。
萬幸叔一臉惺忪,看到束修等人後,這才聲音沙啞的道:「裴總還沒睡呀?」
「吵到萬叔了嗎?抱歉、抱歉。要睡了要睡了!」束修帶頭在前小聲地說著,邊說邊作勢把旁邊眾人揮得回去寢間。眾人眼看這樣也不好意思還要抓著束修打牌,只好互道晚安一一回各寢間去了。
「怎麼?又是夜歌漁願啊?也就只有年輕小夥子會信這事了。」
「萬幸叔也知道這事?」
「這事當初鬧得挺大的,晚上一堆人上甲板在那唱歌。」
「我能想像那場景是怎麼一回事。」束修想了想晚上甲板各處站著人,在那船緣唱歌的景象,那景象讓束修都不自覺的笑了笑。
「辛苦你了,還要帶這些年輕人回來。不過我想大概也沒人上的去吧!」
「你說的也是啦……」的確是沒看到半個人上去,全都被打了回來。「甲板上的是小葉吧?真沒半個人上去過?」
「也只有耿船長上的去了。」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呀……」束修有些震驚,看小葉比他年紀還小的樣子,這船上居然沒人打得贏他!就連那比他高且還狀的張凌山都承認打不贏他。
「至少我跟著耿船長的時候就是這樣了,拖他所伺,晚上終於少了點人想試夜歌了」
也就幾個新入船的不信邪,總想在耿船的夜間試試這事了。
「裴總若沒別的事,我可要先睡了。」萬幸叔還打了個大哈欠道
「阿!恩、晚安。」「晚安、晚安」
看著萬幸叔回到寢間躺回榻上,束修也就只好靜靜地離開。
原先他本想再回樓梯處,上甲板看看的。不過怕回頭過去又會撞到凌山他們三人,他也只好乖乖地回船長室睡覺了。
稍早前。夜間微微搖晃的船艦,正常來說只有船首船尾吊燃的夜燈,不過今晚卻意外地在前廳間也還點著夜燈。
「你終於來啦?」柏老在桌前書寫著文書喊道。看到進門的耿菽後,柏老停了停他的筆擱在台上,這時耿菽也剛好入座放下書卷。
「要哄人睡覺,耽擱了一下。」
「……我到現在還是不認為帶著裴少是個好事。況且我們還有別的任務在身。」
「也就帶著而已,不出事、沒人說,還會出甚麼事?」
耿菽態度鎮定無禮,一比早上對柏老的恭敬態度,此時甚是無所謂與冷漠。
「誰曉得是不是只有我們知道裴少上了船?他會上船是不是也是任務的一環?」
「這你不需要想的太多。把上期內容給我看看。」
柏老沒多說什麼,默默把書卷攤開遞上。一時片刻安寧,耿菽沒有說話,而是對著桌前的書卷觀看。書卷寫的不是航海渡船之事、也非貨物運輸之詞,而是南洲景家的諸多交易清單!其中盡是一些非法勾當。柏老靜靜地等耿菽看完此卷,這是他名目上當商人私底下蒐集謄寫而來東西,不過這東西說多了,也沒有甚麼用,一來它不是正本,其他人會說它是贗造的可能性很大、二來景家對於此類東西很有辦法去推卸,常常有實無證、有證無實。要不這景家也不會壯大到成為南洲一方商人了!大到連皇國帝家都不得不關注的地步。
耿菽就是關注的其中一人,當初他沒有從日清冥畢業而是肄業,主要的原因是被帝家招攬,名目上是肄業而離開海軍軍校的人,實質上是被帝家隱藏重任。
而耿菽的主要任務則是幫帝家蒐集景家各類情報,在外他是個船長,專跑東丘南洲的商貨,在內他是帝家的情蒐員,而柏老是他的下屬,也是對外的假上司。柏老幫忙耿菽蒐集景家在商貨上的交易。此類內幕也只有他們兩人知情,就連船員與柏老的商會他人都一蓋不知。
「你帶裴束修上船,真心沒有半點心思?」
耿菽也知道這是沒辦法瞞柏老太久,兩人共事數年,彼此的行為到有一定了解。他嘆了口氣後說道
「這類交易清單再多都沒用,我要有個實質的作為,一個能讓景家露餡的物證。束修是個破口。」
「你想拿裴束修當誘餌?」
耿菽依舊淡定,默默地還喝了杯水、潤潤喉,沒有否認柏老的推測。
「我不認為一個北方少爺的身價,有必要讓景家出面動他。」
「這事你就知道的不多了,柏老。」耿菽放鬆身軀背靠在椅背上,閉起雙眼開始淡淡回憶道
「當初皇國北方有裴氏與凝氏兩族,雖說裴凝兩家沒到互信互愛的友好,但也沒到交惡互戰的地步,但你知為何當初裴氏會幫帝家與凝氏打起來,甚至幫帝家固守北方領土嗎?」
「帝家錢多不是?光是消耗在北嶺與西原的禦敵支出,就佔了帝家的三分之一。」
「你說的是現在。當時的裴氏早已富可敵國,你覺得僅是送些金銀財寶會打得動裴氏一族?」
「恕我孤陋寡聞,那你說說看是甚麼原因?這又跟南州景家有何相關?」柏老一副不屑的樣子。
「你可知裴氏當時的內當家是誰嗎?」
「……彤君?」這事柏老就是真無消息了。現今北嶺的裴家大院真是無一女卷,就連僕傭都是小廝兵卒一類,陽剛十足,眾人皆傳裴院不是住家,而是兵營!不過無一女眷,那裴家兒眷何來?總不能說是風雪中迸出來的吧?
裴氏內當家無人知道來歷,只知在早時裴老爺突然取了個女伴回來,姓氏些不知曉,眾人只管叫裴夫人,裴老爺也只管叫她彤君,但彤君不姓彤,眾人問之,彤君但笑不語,眾人皆無可奈何。生了兩胎皆是男孩,後戰事發生,彤君被凝氏一族擄去,待帝家統一皇國,各地戰事消緩平和到來時,回來裴院的卻只剩彤君的頭顱。
自此,人們總說裴家與凝氏交惡,是因為彤君;裴家歸順帝家皇國,是因為錢財。
幫著帝家固守皇國北嶺之地,排除北嶺其他外族,而這其它外族則多指的是凝氏一族。
耿菽仍然躺在椅背上,雙手平靜的交握在腹前。他沒有馬上接著柏老的話,而是在思考一些事情,待他組織完話語並小小聲地說出口時,這話卻讓柏老驚的從座椅上站了起來!
「若我說彤君沒冠裴氏之名時,她的舊氏姓帝呢?」
ns3.149.255.2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