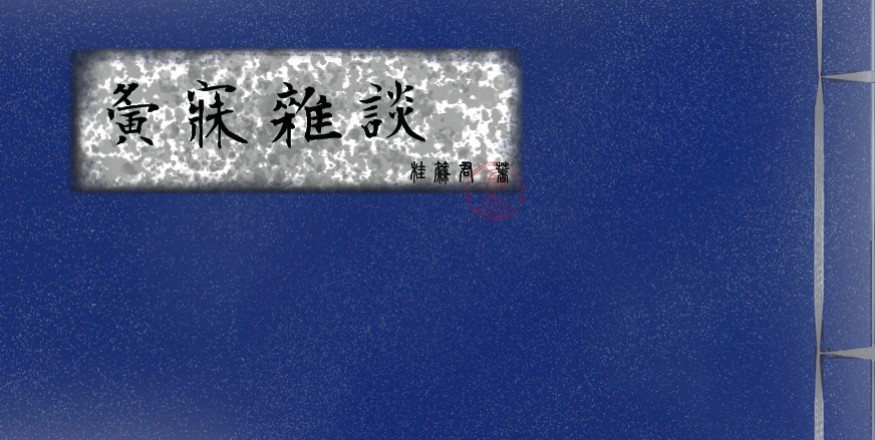芳樂港外的冥波正隨著季風往北流動,而多數的帆風商船也會選在這時候乘著水流往北航行。
港口與近水還有引水會在船上與小船在旁支援移動,而離開芳樂的管理範圍之後,這些船隻往往就需要憑藉著自己的經驗在這碩大的冥流中移動。
往北流動的水流總體上來說雖然只有一條,但是細化來看這一條往北流的水流可是有大大小小不同分歧的水流匯聚而成,若是稍微偏離一條水道稍微久一些,那要回到原先的航道上可就要在花上大半的精力,白白浪費半天到一天的例子也不是沒有過。
所以船上這個觀測臺就很重要,除了主要的航道修正之外,平日還要觀望水面上是否有其他突發事故出現。平常一點的像是水面上的漂浮物、其他船隻之外,更為麻煩的是近海的礁岩與冥水之下的那些奇怪的生物。好在黃國周邊的航道區域早已被掃蕩過數次,航道之內的冥族生物早已減少了許多,陸地與冥族的衝突也減少了許多,但也不敢說完全沒有。
照理說站觀測臺這個位置的人非常重要,沒有觀測臺上這個人的觀測指引,那船上的舵手與水兵們也是無法對船隻有所操作,形同身體沒了視覺,無法對當下情況能有立即的反應。
然而現在云丘號觀測臺上的那個人卻是毫無精神。
船桅平台上放著簡易航圖,然而觀測臺上的男子並沒有詳細的觀看著這張航圖比對著現況,就連船體外的偌大水面也無一關心,雙眼望去的地方盡是空無,顯然這男子的眼神根本就沒有對焦在視線所及之處,僅僅是「看著」前方罷了。
萬幸叔剛爬上觀測臺,看到的景色就是如此,葉平毫無精神的趴在觀測臺上,放空著精神遙望著不斷波動的水面。
小葉面無表情,嘴上頻頻嘆著氣息,顯得有些死氣沉沉。
小葉這樣的狀態也不是什麼一次兩次才出現過,常跟著耿菽船隊的萬幸叔哪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小葉獨自一人躲在觀測臺上發呆放空,哪一次不是因為與耿菽有衝突?
然而無論是犯錯了被耿菽罵,還是夜哨出事情被責怪等事情,都沒法與這次相同並論。
萬幸叔上觀測臺時,刻意的拉大了步伐,發出了不小的聲響,示意著小葉自己的到來。然而葉平也只是眼角餘光朝萬幸除這撇了一下之後又回歸,根本就沒打算理會。
「我說小葉。就算回程沒貨了,船隻航行時固定要做的觀測依然是少不了!」
「都入航道內的水流了,基本上也沒我的事吧?」
這回話看似無禮,但是在萬幸叔的眼中來看,卻很是不一樣的無禮。那感覺與那剛從東丘出航,在觀測臺上被發現偷懶而回嘴的葉平大是不同。
對於葉平的這句話,萬幸叔沒多說什麼指責。他僅是待在了觀測臺上的另一邊,靜靜的看著葉平現在給人的感覺。
萬幸叔靜靜地看著葉平的身影說道:「我覺得你這樣還比較有些……成長了的感覺。」
「什麼?成長什麼?」葉平本來就沒有把思緒放在身旁,萬幸叔這突然的一句話自然葉平也沒聽上幾分。
看著葉平終於有些回應,萬幸叔這才繼續說著一些他原本想說的話。
「我說你現在看上去,比較有些成長獨當一面的感覺。」萬幸叔說完後,又頓了頓嘴,想等著葉平有些反應。不過見葉平沒什麼動靜後,萬幸叔只得又\補充了舉句道「尤其跟耿總分開了這麼段時間後。」
這幾句關鍵字終於是讓葉平對萬幸叔有些反應。雖然葉平隱約知道萬幸叔有什麼話要跟他說,但這話、這開頭聽來肯定是不怎麼好聽。
「說的好似希望我倆分開會比較好一樣。」
「難道不是?」
「……」答案葉平自己也明白,他只是回不了嘴、說不出口。
「總跟著人也不好,獨自一人也算是種成長。」
「我也……沒有一直跟著呀。」葉平自己說著說著也知道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就大方向來看,自己的確是跟了耿菽許久,從離開芳月的南風院、東丘的小住處、一片大冥中的云丘號上,那個地方是沒有跟在耿叔旁邊?
「葉平,你有沒有想過船隊水兵做了這般久,自己一個人出來當隊總?」其實就云丘號耿菽那隊老水兵裡,哪一個老手不能出來當管?葉平也只不過是年紀輕了點。那經歷在萬幸叔眼中看來可不算少,不敢說當個司總管全,當個旗、局總還是可以,葉平缺的只是些機會與時間的歷練而已。
不過萬幸叔眼中是這樣看,葉平可不這麼想。
就耿菽身邊待過這般久來看,司總這個職位對葉平來說管的可太多。云丘號算中小型的商船,現在一個總沒滿制,那也有五十多人,這總真滿起來,算下來也近千人!葉平自知他沒這個能力。更別說現在區區五十人的云丘號上,他都還有許多問題沒法解決。更別提他那沒幾個人知道的奇怪體質。
葉平沒跟萬幸叔解釋這麼多,只是簡單地回了句「沒有、不想」
「耿總離開後,你還要做什麼?」葉平自個不想,萬幸叔卻是又勸幾句。
「……這事情等回東丘再說吧。耿菽也不是一回東丘就要馬上離開了。」
「你要多想想也不是沒甚麼不可以,就怕你什麼都不想。」萬幸叔看著小葉那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就怕他一拖再拖,真拖到耿菽走了都還會攤在原地。
萬幸叔對於小葉的看法,其實還真給他給說中。
幾日前與耿菽談過話的葉平,如今心中還是有些紊亂。在交談的當下,葉平本來就沒什麼心思多想,想到甚麼就問什麼。如今過了幾日,這船隊散了一事還是有些這麼的不真實,彷彿耿菽說的話就像個玩笑一般。突然自己在意的一切都不再這麼重要,那突然的空虛感著實讓葉平什麼都不想再考慮,能過一天就是一天的度過。
看著觀測臺下的人員頗有生氣的走進走出,一會看著船外指指比比、一會聚在一起說話談天,葉平開始有種厭煩的感覺。
葉平繼續看著船桅下的那些老面孔與新乘客,頭沒動半下地朝身後的萬幸叔反問道:「那萬幸叔呢?船隊解散後還要繼續待在云丘號?」
「叔我呀!到東丘後,可能換個船隊試試看吧。」萬幸叔說到這,走到葉平旁邊又指了指觀測臺下的一群人。「又或者找些老好,我們自己組個船隊就是。」
「其他人也都這麼想?」
「怎麼?有興趣加入?」
「……」葉平沒多說什麼。對他來說,現在談什麼加不加入還太早。就連他還要不要繼續待在東丘討生活都不知道。
看葉平不說話,萬幸叔以為葉平情緒上來,也不再多說什麼玩笑,語氣轉為正經道:「不知道該做甚麼的時候,或許回到初心是個方法。但是這麼說對你來說太過老成,初心什麼的,萬叔我其實也不知道是什麼,更何況是你。想想什麼時光能讓你高興、想想做甚麼能讓自己快樂,或許那才是你應該待的地方。」
「我……」
不等葉平開口,萬幸叔早已猜到葉平想說什麼。「不要說為了誰而活,那對你來說不是個選擇,也還未碰到那種要你陪伴一生的人。你該還的就我來看,早還清了,人家或許還不想你還呢。」
萬幸叔口中說的是誰,葉平哪會不清楚?剩下的萬幸叔也不多說,拍了拍葉平的肩膀後就離開了觀測臺,剩下不知道有沒有聽進心裡的葉平獨自待著。
觀測臺上沉重,甲板平臺卻是笑鬧聲不斷。氣氛如此歡快這不僅僅是因為航行快速,能早點返活東丘的緣故,更大的原因還是在於這些乘客沒有多大的負擔。相比從東丘來芳樂時的艱辛,現在不只沒有貨物要顧,也沒有耿菽那些帶水兵隊的諸多規範,就連那水流與季風都幫著船隻飛快的前行,更別提那來時風雨,現在連片烏云都沒見著半片。
這不那甲板上一群原云丘號上的水兵,正與那第一次搭船的人聊起話來。
這船上話題聊來聊去,什麼家鄉景色與鄉土名產,人家也不在意這般多,說的在多見不著也沒什麼用,且道是上了岸後自個找找就是。那現在在船上,一夥東丘人跟南洲人能聊什麼聊到這般歡樂有趣?那自是船上的事情。
一人語意大聲鮮明的朝那南洲人驚訝道:「這事情你居然沒聽過?虧你老兄還是做船辦的!」
「欸、欸!你這說可不准了。我跑這麼多地方,別說東丘了,在遠一點比北嶺還遠的黃國外港都去過,就你這事聽都沒聽過,就你東丘這條有傳過此聞。」
「真的假的?這聞在東丘可有名啦!雖然我不敢說是什麼家喻戶曉的事,但是在東丘跑遠航的,沒一個是不知道這事的,怎樣、今晚來試試?」
這可不是什麼夜晚的聲色邀約,那東丘人說的可是那夜願漁歌!
這南州人還在猶豫,另一頭的東丘人卻是在旁喊道:「老好!云丘晚上不是有那小子守夜?這還有得夜願可唱?」
「這你就不知了!這夜哨你說說看,是誰給安排?」
這問題沒什好想的,那人是不假思索的就答:「這當然是船總給排的,這船總應當還是耿總吧?」
「那你猜怎麼來著?這夜哨的事情我早些時刻就問過耿總啦!你猜他怎麼個說?」
眾人聽他這麼一說,且早心知這事有個頭。但還是頗有給臺的托道:「怎個說?」
「總說了!這哨且是有的,依然是那葉小子。但是大家要上板,總是不反對的,且顧個安全、不要太吵鬧到日墮夤夜就是。」
這話一出語畢,眾人紛紛譁然!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起來。
且說這廝講的不假,別說這廝知道,基本上這話題一開的時候,整個從東丘的過來人幾乎都知道了!哪個在船上的東丘人是不沉迷於這事?
現在就連船總都給解宵了,哪個東丘人是不想好好試試看?
真要說有哪個東丘過來人不對此事有興趣的?或許也就只有那一上船就躲在船艙的阮堯了吧。
這船艙對於阮堯來說可沒多少好回憶,有的多半是羞辱與淫穢的景色。然而一上云丘號之後,阮堯還未來得及與人打招呼,就被身後的常依先生給推擠到了船艙內。原先是水兵們的寢間,現在因為改成客船的緣故,多數的寢間現在都變成客間,每個人分配到的船艙空間大了些,原先一間四、六人擠著的寢倉,瞬間因為一間只配額兩人而大了不少。
但是對於阮堯來說,只要這個常依先生待在這裡,多大的空間都會顯得擁擠。
整個寢間並沒有因為改成客間而有多修飾些什麼,這日陽都還未入海,整個寢間卻是暗了七八成,也就只有靠甲板窗與走道的部分還有幾片光線映入。
客間暗成這樣,自然是沒有多少人想繼續待在這毫無光景的地方。也因為這樣,整條走道的客間也就只有常依先生與阮堯待在客間內。
客間的門口依然只有簾子沒有門板,這也讓常依先生看上去非常緊繃。從與阮堯一起上船之後,常依先生那包緊緊的外觀就沒有變過,就連現在進到室內空間了,常依先生都沒有想要退去自己衣物的打算。
其實若非必要,常依先生甚至還想要自己一個人獨間。無奈還有許多關於阮堯的細項需要他自己操作確認,更別提如何對目標下藥都還未有個底,獨間獨幹的事情,常依先生暫且還是放下,總已大事為重。
常依先生坐在榻邊,身旁幾乎沒有任何行囊,又或者說他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身外之物。
此刻的他手上拿著那個方盒子,雙眼非常專注地盯著盒子。不過常依先生並不是多在意這個方盒子,而是在意要如何使用這東西。
阮堯看著常依先生如此專注,原先也是不怎麼想要打擾他。但是只要沒有常依先生的允許,阮堯幾乎是離不開常依先生半步,從上船到現在,阮堯幾乎不曾脫離常依先生的視線之外。
而常依先生這樣的專注舉動已經維持快半個時辰,若再繼續下去,阮堯估計自個甚麼都別想離開了。
眼見船外光影的變化,阮堯最後鼓起了一些些膽量,小聲地朝常依先生試探道:「常、常先生,那個就快到吃飯時間了,我們要不要先移步到廳堂去?」
「……」
肯定對方有聽到卻是沒反應,阮堯又出聲喊了一下「常先生?」
這一聲終於讓常依先生有反應。他把方盒子收回了懷內的內袋,抬起那有些假詭的面容,淡淡地回著阮堯「廳堂有很多人對吧?我不會出去的,你幫我端過來,我要在房裡吃。當然,你若太晚回來,會有什麼下場你應該清楚。」
阮堯聽完也就是點了點頭,沒有反抗太多。
這些事情是早在芳樂就談好的。只要幫常依先生迷姦完這一次,自己跟張氏的債務就一筆勾消,至於常依先生與那個被迷姦的人如何?阮堯自個也沒打算管太多。阮堯深信,只要自個不被發現,事後迷姦的人追究下來,自個只要推給常依先生就行。反正自個是欠債給張氏,張氏與常依先生關係如何?阮堯自個可沒打算搭上去。
不過依照張氏這種做暗事的性格來看,阮堯估計這個常依先生也像張氏一樣,肯定有甚麼後手可以脫身,也不怕自個推罪。
阮堯猜想廳堂或許還未準備好所有的食物,也就沒急著要離開這房。回過頭,就開始想跟常依先生談論關於迷姦這事的細節了。
「常先生,那個……事情你打算什麼時候做?」阮堯問的有些直接,到也還記得甚麼事情不能明著說。不過就常依先生來看,這藏詞還是有些下劣。
「自有打算,不怕做不著。」常依先生回的隨意,沒有指誰也未說是誰指,作甚麼事沒說,甚麼事情說了也不怕。局外人聽的不明白,然而知情人卻是聽的有意。
常依先生不想多談,但阮堯卻沒聽出這意。這事情關係於阮堯與張氏的債務,阮堯自然上心許多。這頭一句沒問出個果,後一句自然是開始往細節問去。
「常先生,那你說要……就是那個……人是誰呀?」
在張氏那房間討論這事情時,常依先生只說特討厭一個人,要下藥迷昏姦染他。但是這個人是誰?討厭他甚麼地方?卻始終沒有說出個來由。
這討厭人家什麼地方,阮堯自覺是管不著,也用不到。但是這人都上船了,好歹說一下目標是誰吧?連是誰都不知道,還要人家幫你下藥迷姦,這說不太過去吧?
阮堯這簡單的一問,想不到連這單純的問題,常依先生都給了個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阮堯驚訝得差點大叫出來,好在最後這聲「什麼」的大喊是給鱉在了心中。阮堯緩了緩口氣後,繼續問道:「常先生要找的人真的是在這艘船上嗎?」
「當然是這艘船!他來芳越是這艘船,回東丘自然也是這艘船。」
聽著常依先生的回答,阮堯自個是在心中推敲著可能的人選。這來去都是云丘號的人?那八九不離十,多半是云丘號船隊的人。不過這船上原先船隊的人就佔了六七成,這要篩選特定對象,那還有得挑。
阮堯暫時放棄了推敲,想了些比較直接的法子。
「常先生要不要去大廳看看?直接指認是誰不是比較妥當。」
這方法的確是最直接的法子,除非指認錯人,要不然出錯的可能也是最少。然而常依先生對於這個法子卻是沒多少理會。
他饒著身子,口氣滿是不滿道:「我不是說了我不出去?你是聽不懂嗎?」
阮堯不確定常依先生在想什麼,他這樣畏著出去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阮堯一開始想著,或許常依先生是畏懼人群,怕人見著。可是在上船前,常依先生在街口上走著貌似一點也不怕人,應該不是怕人見著這理由才是。
「先生是第一次坐船?」阮堯猜道。
「甚麼意思?」
「我是想說先生一直蹲著不出去,是不是第一次坐船,怕暈著了,在人面前見笑?」
常依先生嗤笑一聲道:「我就算是第一次坐船,這點風浪我還暈不著。」回過頭,這才跟阮堯解釋到自個不出去的原因。
「我這樣貌怕見到那人會被認出來。我可不能在他面前透露出我的身分。」
常依先生的樣貌獨特沒話說,那真實得有些虛假的容貌,第一次讓人見著的確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撇除容貌的問題,阮堯覺得常依先生那包布網的頭型與全身包緊的樣子,那才更讓人會留下印象。
「常先生在其他地方……恩,我是說不像現在這樣的情況,也是這樣的穿著?」
「你是不是探究我太多了些?」常依先生貌似有動怒,語氣有些不善起來。
阮堯見狀也不再深入常依先生的外貿問題,不說就不說、不出去就不出去。
阮堯轉個話題,那目標還是得搞清楚才是。
「那常先生要如何告知我對象是誰?」
這問題常依先生自個其實也是為難。他不想冒然地出房間被人發現他的到來,但是這樣不出房門自然也無法跟阮堯說明自己到底想要對誰下藥。常依先生安靜了一陣子,沒有直接回答阮堯的問題。
常依先生深吸了一口氣,想通為了這個事情,自個其實也不該太過堅持甚麼。他鬆了些口風,朝阮堯說白一些事情。
「我不是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他在外肯定用假名。所以我說了你也不知道是誰,那我倒不如不說,免得你漏嘴失了口風。」
這個說法讓阮堯可以理解「那常先生可有其他方法讓我知道是誰?」
常依先生淡淡說著「他是個男生。」
「常先生,這整艘船都是男生。」
「你又知道了?」就常依先生自個想來,就不只有男生。然而阮堯當然不知道常依先生如何想。
「這不是知不知道的問題……好吧、你還有甚麼其他敘述?」看著常依先生又一副不滿的姿態,阮堯決定不再追究那個無腦的問題,轉而繼續話題的延續。
「他年紀比我大。」
阮堯看了看常依先生那密不通風的衣著與那樣貌,真要猜先生年齡?這橫跨的可能未免太多,更何況是比他大,那是更不用談可以去掉多少。
避免挨罵的可能,阮堯不多跟先生解釋甚麼,繼續問道是否還有其他資訊?
「我聽聞云丘號上的船長是一個姓耿的傢伙,這人跟他還挺熟的。」
像這資訊就有用多了!阮堯一聽這敘述,這六七成人選可以除到剩下兩三。跟耿總熟悉的人那肯定是云丘號上那原先船隊上的人,那些老管什麼的,肯定脫去不了。
阮堯很高興事情終於有了進展,繼續深入道:「哦!那常先生知不知道他有甚麼身形特色?高的矮的?神色如何?」
常依先生想了很久,不知道是想不起來還是不知道如何敘述,最後只簡單答了一句「應該比我高一些、但也沒高去哪。姿態來說,有練過武,應該是格正勢直吧?」
阮堯又看了看常衣先生一眼,放棄細問這類外型問題。
「長相呢?有沒有外觀地特色?例如頭髮或是面孔?痣傷疤痘什麼的?」
這問題比起剛剛深思的態度來看,常依先生這次可是想都沒想,很快地就說了出來。「長得特討厭、特醜!」
顯然這話還是沒說清楚什麼……
特醜這話一出,遠遠的在船長室待著的束修是不來由地噴了一個響亮噴嚏。
一旁待著沒離多遠的耿菽一聽到這噴嚏,很快地就道了束修的旁邊摸起他的額頭。
「是不是那風邪沒好,這又復發了?」
束修撇開了耿菽的手道:「沒事,那病都過多久了?你擔心太多了。」
「我怕你身子又受傷,這上路還得回北嶺,這還受的了?」耿菽手離開,身子卻是貼了上去,身體面容就往束修肩上搭去。
耿菽一貼,束修雖然有感卻是故作不知。那是故作道:「你真擔心我身子受傷,怎上船了還如此多般亂弄。」
「我又亂弄什麼了?」耿菽這話說的不恥,那臉甚是移動半步都沒有,又是乎咧乎咧地在束修耳邊吹著。
束修被呼地以些不耐,一手就往身後拍去喊道:「你這物還往我腰後頂!你說這不亂弄?」
束修這往後一拍,是拍往貼在自個身後的耿菽腰下。這身後耿菽腰下雙腿之間,有何物在束修腰上亂蹭?自是不在話下。
這一拍卻未拍去耿菽的亂蹭,反倒讓他更起興致,那物是不離反近,不縮反脹。
耿菽頂了頂腰身,臉靠在束修肩上耳邊,微開著雙脣,呵著熱氣,等著另一雙唇肉皓齒貼近過來。
然而耿菽這束修的熱嘴沒等到,卻是被束修又一個噴嚏給噴了滿臉。
「恩、抱歉,真的忍不住。」束修這話說完又是一個噴嚏「可能有什麼人在說我壞話吧?」束修擤了擤鼻息忍住了一次噴嚏道。
ns3.144.127.18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