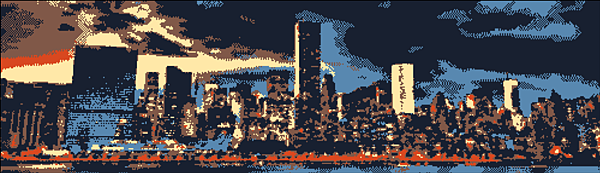 x
x
Disclaimer2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BRv8zktd6
【原作者贊助連結】
阿特力士開始搖搖晃晃。相比之下,昆蟲較沒有人類或其他動物那種,可以逼自己超過極限的能力。大部分昆蟲都很小,身體效率極高,只留下最基本的要件。假如蟲子需要跳躍、撲動或飛行,它就會有特定能力,通常不會有其他的能力。實情不全然是那樣,但我還是發現了這種傾向。
簡短來說,它們身上不存在「百分之一百一十」。阿特力士開始表現出疲勞、難以載我,我沒浪費時間,直接讓他降到地上。
我將手放到那隻巨型甲蟲的殼上,媘蜜跟瑞秋也趕了上來。
「有問題嗎?」媘蜜問。
「沒。」我說。「算是有吧。我可以騎一隻狗嗎?」
「可啊。」瑞秋說。她吹了聲口哨,口哨聲響亮、尖銳到使我縮了一下;她朝我一掃出手指。她其中一隻狗就理解了信號、走近我。
「阿特力士怎麼了?」媘蜜問。
「沒力了。」我說。我的嗓子聽起來很平坦。「在愛剋妲娜戰的時候,我有看出他很快就會疲倦,我有記下他跟我分離時,多久沒好好吃東西⋯⋯但我也想到,事情不只有這樣——我還沒搞清楚他所需的完美飲食,我也幾乎無法維持他的體內平衡了。他每次受傷,每一次變累,都承受我無法抵銷的損耗。」
「我感到很遺憾。」媘蜜說,
「事情就是這樣啊,不是嗎?沒什麼東西可以百分之百正確。」
「我想妳是對的。」她說。「我在想,妳幫他命名的時候叫他阿特力士時,妳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媽從我小時候就教我讀書。」我說。「他是巨型的赫克力士甲蟲,我能想到、唯一比赫克力士還要強的名字就是阿特力士了。」
「用肩膀扛起整個世界的泰坦嗎。恰如其分呢。」
我聳肩。
「他就他的主人一樣,難以扛起自己的負擔呢。」
「我真的沒心情討論媘蜜的心理分析。」我爬到那隻狗背上。我不怎麼認識這隻狗,而牠在我爬上牠身側時也移開身體,讓攀爬過程變得更尷尬。瑞秋發出一道「啊」似的吠叫,那隻動物就靜止了。
「也許它不全然是妳想要的阿特力士,但它還是有幫上忙?」媘蜜問。
「我的問題不是說說話就能解決的東西。」我說。「除非妳有任何關於拓閣的觀察,能讓這個世界忽然變得合理,或是能讓大家別這樣混帳、這麼智障,那我就不確定我會想要聽妳說更多話了。」
「他戳痛妳了。」
「才沒有。」我說,搖了搖頭。「他說的東西都沒有⋯⋯」
「就算妳忽略他說的所有東西,他還是戳痛妳了。」
「兵器大師。」我說。「凱薩。純潔。民軍小姐。皮戈特。理龍⋯⋯還有另一大群我根本懶得記住的人。為什麼要找到願意合作的人,要找到跟我想法一致的人,有這麼困難呢?他們一直在下著我根本無法理解的決定,有些時候還是沒有人能理解的、愚蠢的決定,然後還讓事情分崩離析呢?」
「他們在看著妳的時候,八成也在納悶妳幹嘛不同意他們對許多事情的想法呢。」
我搖了搖頭。「這件事不是那樣啊。」
媘蜜沒有插話或爭論。
我掙扎著要找到那些詞彙。「⋯⋯我想說的,是像維護和平、保護人們的安危、確保所有人都很安全的那些概念,都⋯⋯都沒有很複雜啊。這都是很基礎的東西。而假使我們連基礎都沒辦法打穩,那我們到底該如何處理更複雜的東西,像是要繼續讓這座城市運轉,或是要防止戰爭開打?」
「假使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處理基礎的東西,更大的問題就不會存在了。」
「不對,他⋯⋯不管妳是在說基礎或更大規模的東西,這都不會合理啊。他攻擊一間學校就為了——他怎麼說的——把我揍到鼻破血流?」
「事情八成比那種說法複雜。妳跟任何人都一樣清楚,我們在面對敵人時都會戴上面具、扮演角色。他也在扮演特定的角色,因為他知道只有這樣才能搞到妳。」
「為什麼他一定得要『搞到我』呢?」
「妳攻擊他了啊。」
「我是說,為什麼得做到那種程度。他們在八十八帝國沒有超能力的人將人們從家裡拖出來的時候,對凱薩和純潔都也沒那麽有攻擊性。在ABB在販賣嚴重毒品,因為大家父母出生地點在某些地方,就在大街上攻擊人,強迫他們成為士兵或娼妓,不然每個月都要繳保護費,那個時候他們也沒這麼做。而且那些受害者可是國中生欸。」
「妳可是奪取一座城市。」
「這怎麼會比較糟糕?那怎麼能跟其他人比?」
「那是不能比。」媘蜜說。她跳下班特利的背。走在瑞秋跟我之間,雙手拇指勾在腰帶上。瑞秋盯著我,表情難以辨認,她的面具吊掛在她脖子上。媘蜜繼續說:「真的沒辦法比。但這對他們來說是天差地別。他們必須在意外表。」
「保住面子有重要到讓他們必須攻擊一所學校嗎?打破潛規則?」
「我可以洋洋灑灑說一大堆關於潛規則的話題。但那不重要。對於拓閣跟皮戈特這種人,那都是超亞人類的東西,而他們也不怎麼算是超亞人類呢。啊對呢,對於他們所面對的東西來說,面子是比孩子重要。這裡的事情才剛靜下來⋯⋯」
瑞秋輕蔑地哼了一聲。
「⋯⋯他們PRT才剛好轉。他們夾著尾巴逃跑,成員數量大量失血。他們分崩離析,他們在大局之下也重要到我們不知道事後影響會是什麼。每個要跟終結召喚者戰鬥的隊伍,都會仰賴捍衛者的情報、後援、儀器跟定期訓練。但甚至在這些東西以外,除開假面,全世界有上億人在觀望著捍衛者、向他們尋求保證。我們的觀點跟感覺,在那上億雙觀望的眼睛裡,幾乎不成影響。」
「幾乎不成影響。」
媘蜜聳肩。「他們會擺出一副勇敢的神情,把一個固執己見的混帳推上官位,他們就會預備好要咬我們一口。他們不想獲勝。不用全面獲勝,也不用一次全贏。他們需要我們,因為他們沒有假面可以全心保護這片地盤,就連傳送門變成重要地點也不可能讓他們增加人手的。他們的目標是要解決掉妳,顛覆我們的組織,然後他們也許會希望能瞄準其他壞蛋。爪牙、終徒,還有之後出現的、其他任何不守規矩的人。他們會做事,對世界保證自己的重要性——他們會保持平衡,也只會花費最少量的資源。」
「而為了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卻亂搞規則,攻擊一所學校。」
「妳真的會對他們打破規則,感到驚訝嗎?我們有打破規則,皮戈特在我們扮演誘餌時,轟炸我們跟更重大的威脅時,全都一樣啊。規則只有在保護現狀時才會有用,而布拉克頓灣已經在好久以前,扭曲、肏翻了那些規則啦。」
「那學校呢?」
「黛娜。」她說。「他們有些基礎、扎實的數字,說妳不會搞出一些災難,他們也有公關可以清理餘波。我猜明天早上會有一些新聞。他們會說妳無可否認就是一個威脅,他們會扭曲事實,亂搞真相或直接說謊,他們也會壓下任何跟那個策略相衝的東西。在那之後,他們就會讓拓閣跟當地英雄要來咬我們一口,為了數億個觀望者,他們就會做出一些自己可以拍到的損傷,而在完成目標以前,他們都不會停下來。他在這件事上,是很誠實呢。」
我握緊拳頭。我不想去思考黛娜的事情。
「抱歉。」她說。「但妳最好事先知道,讓妳不會在看到新聞時失去理智⋯⋯」
「瑞秋。」我打段媘蜜。
「幹嘛?」瑞秋問。她雙眼還沒離開我。
「我可以借用這隻狗嗎?我會照顧好他的。」
「他需要吃飯。妳可以在明天早上把他帶回到我那邊嗎?」
「我以防萬一,有請媘蜜把狗飼料運到每一個總部,跟妳餵給狗吃的飼料是同一種。」我說。「明天早上不行,但我會確認他有吃飯。」
媘蜜皺眉:「掠翅,我們需要討論⋯⋯」
「我理解重點了。」我說。「妳有訂狗食吧?」
「有啊。」
我看向瑞秋:「我會帶他散步,確保他有飼料跟水。」
「沒必要散步。」瑞秋說。「波士頓㹴一天不需要散步一次以上。」
「好的。」我說。
「我明天下午會去接他。」她說。也像之後才想到地,說:「他叫雷德利。」
「謝謝妳。」我說。
不詢問,不施壓,也沒有解釋。只有瑞秋,踏出了她自己的舒適圈,將她其中一隻狗交給別人。這比媘蜜說過的所有東西的總和,都還更有幫助。
不是說這會多有意義呢。
「雷德利,走吧。」
雷德利遲疑了一下才聽令。我稍微以為瑞秋會催促他前進,但她沒有說話,顯然是願意讓我下令。
我在他開始跑動時,在許多方面都感到歡欣。
移動感覺很好。這不像我自己在跑步、雙腳踩在地板上,但雷德利的肌肉在我底下鼓動,他腳踩上地面的衝擊感衝撞過我的全身,使我必須咬緊牙關才不會咬到舌頭,這感覺很棒。
我一直都很喜歡風吹入頭髮的感覺。風若不讓人放鬆的話,仍很清新、柔軟。在我周圍空氣溫暖潮濕時,風則會涼爽。
我轉換姿勢,只用一隻手抓著他,另一隻手拿下面具。世界變得很模糊,而我沒空出手戴上眼鏡,但我現在也能讓臉感覺到風了。我緊閉雙眼,相信雷德利跟我的蟲群感知,可以領我穿過街道。
但我到底該去哪裡呢?
我想去看黛娜,我也知道那是我最不應該去的地方。我已經知道答案,知道結論早已出爐。我不想思考這件事,就像我不想思考她在我們於車子裡分手時,留下的那兩張紙片。事實上,我正在積極拒絕思考這件事。
黛娜給我留了兩則訊息,我不懷疑她那麼做的背後,是有個理由。現在要跟她見面,就會是抗拒那個理由,也會使我進入英雄們的視線之下,那樣會將我完全不想思考的事情,僵固為單一一種的討論話題。
我爸?不行。沒什麼好說的,也沒有信號可以用。如果他還在家裡的話,我不確定自己想看到他周圍的新聞媒體,或是捍衛者——那會讓我想起,我不只拋棄了他,還讓我的存在對他造成麻煩。
我將雷德利轉過一個街角,搬動一條鐵鍊。我沒強壯到能讓他轉頭,但瑞秋已經把他訓練可以察覺極其細微的暗示,而他的性格也似乎較願意配合人。如果他很固執的話,他就會選擇繼續奔跑,直到母狗的超能力消退。不是說,我不想要那種結果呢。
「好孩子。」我說。
我到底該怎麼做?我沒有任何興趣。一年半以來,我都只能勉強過生活、撐過學校,讀書,然後漫無目的地上網。一當我的超能力浮現時,我的興趣就是要預備自己作為超能英雄出道。我從那時候,每天生活都只在做著這件事,也只有這一件事存續至今。
我們的奔跑漫無目標,直到雷德利嘴角有了泡沫,然後,他背脊肌肉的動作開始顯示出他體型正在縮小。
雷德利在指示下,開始行走,然後徹底停了下來。我滑下他的背脊。握著一條鐵鍊,領著他散步。這能讓我扯開雙手雙腳的筋結,也能讓雷德利血肉蛻在他周圍,在奔跑後冷靜下來。阿特力士跟了過來,飛在我們上方。
我想去見見布萊恩,卻不想繼續我們先前的談話。
我渴望去處理掉我的敵人,我想騎著狗前往戰場,對爪牙和終徒的情形做某些事情,但我不相信自己夠有注意力,能以最好的狀態來面對戰況。
我也沒辦法想像,自己可以在一夜好眠之後那樣專注呢。
雷德利沒辦法繼續走路,我就等著他身上最後要蛻落的血肉,撿起所有鐵鍊。而在要捲起鐵鍊時,它的重量很讓我驚訝。
其中一條鐵鍊上有個項圈。我在一個充滿液體的囊袋裡頭找出雷德利真正的身體,用雙手刺穿囊皮、撈出他。我成功套上了那個項圈,並將一根鐵鏈扣上項圈。我將一些鐵鍊交給阿特力士,將剩餘的部分提在手裡,扛著這份重擔。
即使我不確定自己想去哪裡,沒有阿特力士或雷德利載著我,我就得面臨那一長段路途了。
有時間思考,也沒有任何外在力量來干涉我的思考。
去他的拓閣。我痛恨我自己跟他的對話成了我無法不一直回想起來的東西。
雷德利跟我,他媽的到底要去哪才好?還有哪些地方會靠近這裡呢?上校陵?森林?戰慄地盤的北端?我到底是為了什麼才來到這裡?
我繼續行走。我有點無法回去我的地盤,去回答我的部下的問題。我也有些知道,今天晚上間間斷斷的睡眠後醒來,我就會繼續當掠翅。我在一長段時間內,在與我互動的任何人、所有人面前,都會是掠翅。
在我發現一道矮石牆上的鋼鐵格子圍欄,金屬格尖指天空、保護著那片土地裡的住戶,我那團混亂的想法,實體化為一道領悟。
我一手撈起雷德利,爬過那面牆。
地面很鬆軟,滿是蟲子。這片地區有著濃密樹林——那裡先前只有稀疏小樹,現在就過度茂盛。多虧白天的樹林陰影跟周遭丘陵吹下的風,這裡的空氣就比較涼爽。
我坐到草地上。
「老天。」我說:「我該從哪裡開始呢?」
雷德利似乎以為我在跟他說話。他走近我,用鼻子戳著我。我輕柔地抓了抓他的耳朵。我改造的手套裝甲,讓手指末端更尖銳。雷德利似乎很喜歡這樣,就推上我的指尖,閉著雙眼。
「媽,我猜我應該說,我很抱歉拖這麼久才來。」我說,繼續抓著雷德利。
那顆石碑,自然是沒有回應。上面只刻寫著:
安妮塔・蘿絲・赫本2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xSxb0iKWas
1969-2008年2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6iIjcTKd6E
她將珍貴的事情教給我們每一個人。
「那是⋯⋯要思考整件事的前後脈絡,就感覺有點丟臉呢。在我想解釋,讓妳趕上過去幾個月以來的所有新聞時,我胸口就有這個結,卡在鎖骨周圍。」
沈默拖延。我們所在位置偏遠到,就連城市的聲響都不會傳過來。就如待在戰慄的黑暗裡一般,清清楚楚地失去感覺。
「我猜事情是有點被前後顛倒了。我之前,有跟妳說過的那個超能英雄的東西?那⋯⋯並沒有成功。」
我稍稍笑了下,發出一小段聲響,毫無笑意。
雷德利爬上我的大腿,轉過身、直到他可以舒服安頓下來。
「那像是⋯⋯我可不可以從頭告訴妳之前發生的所有事,還有爸八成會發現的所有東西?也許還有,比我在新聞上的手機影片裡、用來威嚇理龍跟目空大師的事情,更加糟糕的東西?我不認為我可以撐過去。那是⋯⋯該怎麼講這個重點呢?我做過很可怕的事,我在想像要告訴妳跟爸那些事情時,會讓我感覺像個三呎高的小孩子,而愚蠢的部分是,我也不是很確定自己若能重頭來過,就會有所改變。」
「所以我該從哪裡開始?我到底該如何表達?所有事情都被扔來扔去的。我不再孤單一人。也許有一百五十個人為我工作,有些人還會將性命交託於我,其他人則欠了我一命的恩情。我有莉莎跟布萊恩。有瑞秋。還有艾利克跟愛紗,但我跟他們沒那麼親密。我們,呃,我們經歷過許多事。生死之事。在電視上,或電影跟書本裡妳都會覺得,跟自己這樣一起同甘共苦的人,就會因為外在環境而緊密相連。妳在晚上給我讀的書很多都是這樣。而現實,就不是如此了。
「然而撐過了那個危機,也不表示我們所有人能撇清我們自己的問題、繼續待在一起。我們很親密,我們在所有事後餘波裡也變得更親密,但我不確定布萊恩跟我的情感是什麼狀態。現在說起來,我也許正經歷著我有生以來的最低點,我也根本沒感覺自己可以跟他們說話啊。」
我的蟲群偵測到有人走過地面。我瞥向那個方向,看到手電筒的昏暗燈光。光線轉向我這邊,然後過了一分鐘他就不見了。墓園管理人。墓理員?隨便啦。
「布萊恩想解決那個問題,莉莎想搞清楚那個問題。我去找了瑞秋——我之後會去找瑞秋——但我不知道我真的能跟她談這件事的任何一部份。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真正理解我今天喪失的東西。我不想暗示說,妳是我最後一個想找的人,但我認為我來到這邊的真正理由,是因為我不確定自己要去哪裡,才會有人傾聽我說話。」
我嘆了口氣。雷德利應和著我,慵懶趴在我腿上、閉著眼睛。
「呃。我從一個不重要的小人物,變成某個全世界都在談論的大人物。我甚至沒想結果變成這樣,但我最後,算是稍微統治了整座城市。這件事是必要的,所以我就行動了,然後也沒辦法放棄這份工作,因為其他人會站出來掌權,而我也認為,他們對當地人都不會那樣公平。媘⋯⋯莉莎在說,她認為當局正在放水,因為他們需要我們待在這裡。他們不喜歡我們,他們現在也會不喜歡我這個人。所以我在這裡這麼做,地球另一端的政府八成就會討論,壞蛋奪取他們的城鎮時的偶然情況與可能性。我會出現在新聞上,也在被人貼到網路上的各個地方;我猜,連妳的名字也有出現吧。爸的也是。」
我從腰帶上的位置抽出面具,翻過來。我端著面具,好讓它面對著墓碑。
「我猜我應該是要直接說清楚。我是個超能反派。布拉克段彎的罪犯軍閥。這聽起來沒有那麼壞。或許事實會比我的感覺還要糟糕。我有救過人命。有跟利魔維坦戰鬥,跟屠宰場九號跟愛剋妲娜戰鬥過。我也有奪走一個人的性命。我也光是為了傳達一個重點,就跟英雄戰鬥,傷害了那些不該受傷的人。」
我希望就此停止。我嘆了聲氣,回頭盯著那片毫無光芒的墓園,還有矮牆外側的城市。
「我完全,都沒想讓任何這種事情發生。我僅僅是為了過日子,就將自己打造成這一個⋯⋯實體。我八成得繼續這樣做。我有避免因為生氣而傷害人,但那在我看見自己所做過的事情時,就挺薄弱呢。一小陣子以前,有一個傢伙就快死了。他是商團的一員。那男人將一個男孩從他姊姊身邊奪走,大概也做過某些十分惡劣的事情、傷害人。我放他在那裡去死,而我這麼做,一部分是因為我知道自己必須更嚴厲,要確保自己能在關鍵時刻裡殺掉其他人。而我也確實殺過人了。
「我告訴自己說,這麼做是要拯救一個小女孩。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重視這件事——拯救黛娜。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因為,我想做正確的事,也是因為我不確定其他任何人是否能做到這件事。但我越思考,就越覺得自己是想彌補我已經犯下的壞事。」
那石碑底部的小小窄口花瓶裡,有一簇新花。我撿起花,仔細觀察。我爸今晚有來過這裡?
「妳知道嗎?那個被我救出來的女孩。她轉頭攻擊我了。」我說。「我想,我算是理解她為什麼這麼做。我理解那個道理。我甚至也不怪罪她。」
我撈出腰帶裡那兩張小字條。我這麼多次壓皺、攤平紙條,那紙質就幾乎只能算是衛生紙。我還不想讀內容,但我也沒能將其丟掉。
「媽的。」我低語。「比其他東西更影響我的是,這整件事有多麽不公不義。這裡沒有因果報應,好人沒有好報,壞人也沒有壞報。而幾乎是正相反。這就可能解釋捍衛者狀態為什麼這樣差勁了吧。
「我做過很糟糕的事情,殺過一個人,而我也完全無法讓自己對此懺悔。我有嚇過無辜人士,造成財產損傷,攻擊過那些試圖保護這城市的好的英雄,還有那些為了自私自利的原因而當英雄的人,然後我也獲得獎賞。權力、名望、尊重。」
我攤直那些字條,好讓它們都能平躺,小心不要撕破紙張。
「然後我也從邪惡魔爪、詭計多端的犯罪首腦的手裡,救出了一個女孩,而這就是我的獎賞。」
我端出紙張給墓碑。兩張方形紙。每張的左上角都有個數子,被圈起來,表示了筆記應該被閱讀的順序。第一張字條只有兩個詞彙,第二章則是兩個半。
1. 切斷關係。
2. 我很抱歉。
「媽,讓我跟妳說啊。妳不會想聽見一個可以看見未來的人,對妳說出那兩個半的詞彙——『我很抱歉』。太可怕了。她有給我指令,我卻沒有遵守它們。我知道,但我還是有好幾次差點行動——我都沒打出那通電話。我沒離開爸。所以也許那就是她為何去找當局,告訴他們要揭發我,如此來強迫我行動。」
我花了時間折起字條,將其塞入腰帶裡。
「如果她願意在我為她所做的所有事情之後,還願意這麼做,我猜接下來的部分是很重要吧。也許這是為了所有人的好。也許那最能給我存活下來的機率。」
在墓園管理人的手電筒再次點亮時,我繃緊起來。手電筒轉向我這,他卻似乎沒注意到我。
「她說她很抱歉,而這像是⋯⋯我對她並不生氣。我不怪她,因為她只是大局之中的一小塊拼圖,整個棋局上的一個卒子,跟我一樣。被搞爛的是所有事物,不是嗎?這整個互動形式獎勵著做錯事的人,而正確的人卻被懲罰,有些好人實際上比壞人中最壞的人還要差勁,人們彼此之間也完全缺乏著合作時,我們不只有一個末日將臨,而是有兩種世界終結啊——有終結召喚者,還有那個快斬傑克的東西。」
我嘆了口氣。
「我花太多時間盯著這些字條,想著她為什麼寫下這些東西,想要解讀出背後的意義,也有在想著最糟糕的情況。想到,我都開始陷入迴圈。不斷回到同一個點子的不同面向。」
我可以想像她就在那。我媽,作為一個實體存在,站在我面前。散發出她所有的溫柔與溫暖。她的沈默,安靜地予以非難。她的才華光輝,現在都無法與我分享。
我感到有點鬆了口氣。可以這樣直接談論,幫忙我理清那些先前曾令我感到迷失的想法。我現在感覺比較有方向了。我能看到一個目標、可以前進的目的地。我不喜歡這個目標,但我也知道,我一閱讀黛娜的字條,我就不會喜歡那個結果了。
「我想,我必須變得無情。」我說,我的嗓音幾乎沒有比低語還要大聲。我有意識到墓園管理人正要走過來,但我沒有走開。「我知道妳跟爸都不會同意這種做法,但是黛娜似乎認為,我在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中,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也許我若沒這麼做,我就不會在正確的時間裡,位於正確的地位、位置了。」
雷德利被墓園管理人的腳步噪音給激起。我抓著他的項圈,以防他攻擊人。
我拉開雷德利,起身面對著墓園管理人。就算在手電筒的刺眼亮光下,我仍可以在昏光中看到他的雙眼眼白。他年紀稍長,有著圓臉,頂著啤酒肚,頭髮也稍微有點太長了。
他看起來很擔憂。畢竟這個女孩,穿著全身有灰色防彈裝甲的黑色緊身衣,身旁帶著一隻小狗,坐在墓碑旁邊呢。
「不好意思我闖進來了。」我說。「我會離開的。」
他瞥看著我,然後看向我媽的墓碑。「妳是來探訪的?」
「來看我媽。」
「沒想惹任何麻煩吧?」
我搖了搖頭。
「只要妳不會造成任何騷動或留下髒亂,我就不會趕妳。妳也要清理那條狗的善後。」
我沈默地,再次點頭。我沒帶袋子,但我有蟲子。
他的表情稍稍軟化了。「妳需要任何東西嗎?我在今晚再一次巡視之前會煮些茶,但如果妳會在這裡坐一會兒,我也可以煮杯咖啡。」
我感到眼角滲出淚水。怪呢,先前我都沒想哭呢。
「茶的話⋯⋯」我掙扎著要找到詞彙。我幾乎說太好了,但那聽起來很錯謬。「茶,就好了。如果不會讓你麻煩的話。」
「我會給妳倒一杯的。」
「可以給我紙嗎?」我不經意衝口說道。
「我想,我是只有影印紙喔。」
「影印紙就好了。」
「要多少張?」
我張開嘴要說話,但我毫無想法。
又一次,他臉上浮現一道那我不應得的溫柔神情。「我會給妳拿來夠用的份量。妳還來茶杯的時候,把剩下的紙張拿到我辦公室就好了。」
「謝謝你。」我跟他說。
過了一陣子之後他才拿著茶過來。我在那段時間裡,沒跟我媽的墓碑說話,而而我在墓園管理人過來之後,也沒有任何話想說了。
我開始寫字——十二張紙,前後面都寫了。書寫的過程並不快。在墓園管理人又巡邏過墓園之前已經過了兩小時。我也不確定這是他份內的日常工作,還是他因為沒有其他事情好做才會巡邏,但他巡邏完後,就去山丘上一棟小屋裡休息,今晚就休息了。
等我寫完時,我的手在抽筋,脖子感到僵硬。我花太多小時在腿部裝甲板上寫字、考量著該如何措辭,也知道不會有完美的講述方式。
我寫下最後的言詞:
我愛你,爸。我很抱歉。2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qBuKZ79FXf
——泰勒
我抽出花瓶裡的花朵,將其放到墓碑底部。我捲起紙張,將其塞入花瓶,然後倒放花瓶,讓雨水不會浸濕裡面的紙。我爸會是唯一一個讀到這東西的人。而假如墓園管理人等人來調查,我也不怎麼在意。
我站起身,伸展一下。雷德利朝我搖著尾巴,興奮地等著要再次跑動。他是個很快活、輕鬆隨和的小傢伙。瑞秋將他派給我,是有考慮到他的性格嗎?
我想著要對我媽說更多東西,但那個幻覺已經被打破了。我下了決定,而那也不是我在離開PRT總部時準備作出的決心。說說話,讓我能理清思緒。我感覺沒像之前那樣迷失、挫折。我可以寫下一個要讓我爸看的解釋——那或許,不如他所應得的坦承那樣詳細、完整,但也能算是個解釋了。
「謝謝妳聽我說話。」我說,敏銳察覺到她並不在這裡,她也沒在聆聽。「我會變得很忙碌,所以我八成要等一陣子之後才會再次來訪。抱歉了。」
我離開時,喉嚨裡有著一團腫塊,也有想到一個方向了。
#阿特力士 #班特利 #瑞秋 #媘蜜 #泰勒 #泰勒她媽2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LS92PjIB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