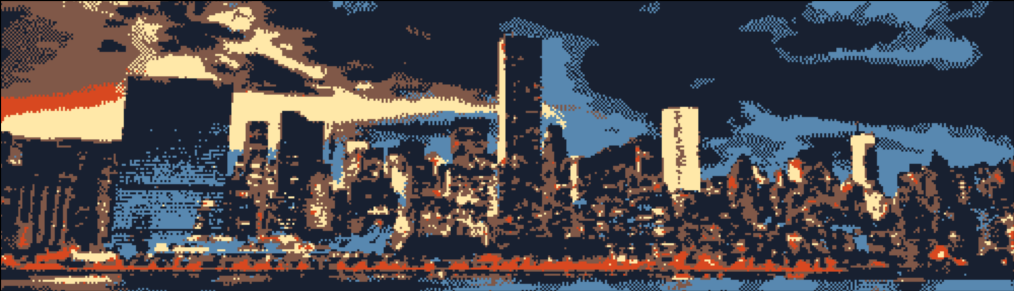 x
x
鋼鐵的高音曲調在刀劍格擋刀劍、擊打盾牌與落到地板時,吟響於空中。較沒那樣甜蜜的是,喉頭咕噥與肉體被痛揍打擊的模糊拍聲。靴子踩進肚子,手肘或拳頭擊中一張臉。
鐵血狼牙經過他對練的新兵之間。他們很疲倦了,將自己逼過精疲力竭。所有人都想留在這裡。訓練對任何不想留下來的人太過嚴厲。沒多少預期要吃飯睡覺,他們的日子填滿了操演、肉搏對練、槍枝訓練以及近戰武器訓練。
選民主要的對手都是僱傭軍人、警察和英雄們。為什麼他的選民需要任何比自己人低等的標準?不,如果他的隊伍表現出真正的雅利安戰士,他們必須有更高標準。他們必須做到最好。
就是這份認知,那份獻身感,才將他的新兵全力付出。太多人把雅利安人視為煽動仇恨之人,無法看到更大的景象——那將人類提升至更高層次的希望。他站在房間一端看著他們的進度,想找出那些有他需要的殺手本能的人。嵐虎與梅嘉在房間另一端,也在找同樣的人。嵐虎拋開面具,只化了臉彩。他仍因腿上所受的槍傷而走得有點僵硬。奧哈拉幾週前照料了他們,也會在每天晚上給他半小時到一小時的再生能力到他好起來,但膝蓋治癒得很緩慢。梅嘉穿著裝甲,在看著戰鬥人員的戰姿與習慣時表情嚴峻。蟋蟀女坐在房間一角,沒看螢幕地打字,筆記下新兵的事。
鐵血狼牙看著梅嘉,她舉起一隻手,伸出兩根手指。她打信號,指向三十四個新兵裡的兩人。一位正於肉體尖峰的光頭男人,和二十幾歲的女孩,綁辮子的頭髮末端有著漂白金色。對他而言有點太像栗米頭。也許那是要用來挖苦。不過,他喜歡她第一個選擇。他有注意到那個光頭男。他在初次見面時就記住他們的名字,但他也忘記了幾個人。他知道那男人是布萊德利,那女人叫莉安或蘿拉之類的。他自己的選擇是那個近三十歲精瘦拳擊手,拉奧夫。
「停止!」他命令道。
他的新兵們行動如一,從戰鬥中退開、收起鈍劍。他們並非所有人都能站直。不止一小群人有流鼻血或眼睛瘀青。
「你們已經進入我們一週訓練的第三天。如果你還在這,你們就是我們的驕傲。」
他能看到有幾個人因此站得更直了。鐵血狼牙在成為有超能力的鬥士以前,就是鬥士。他花大量時間待在運動員身邊,非常清楚只有一點點認可和一點點鼓勵,就能產生不同世界般的差異。
「你們有些人贏得了特別關注。你們比其他人更努力戰鬥,更卑劣也更強。布萊德利,過來。」
那個光頭男走近。
「梅嘉。」
梅嘉走過聚集的新兵,站到布萊德利身旁。
「你們兩人戰鬥。沒有武器,沒有護甲。梅嘉?妳可以使用能力,用一點點就好。」
梅嘉微笑,接著長大一呎半。布萊德利的站高正超過六呎,但她依然壓倒性高過他的頭與雙肩。她解開護甲,將其丟到一旁。
布萊德利看向鐵血狼牙,他五官中閃過一瞬擔憂。
「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我想看你怎麼對付比你巨大的人。」鐵血狼牙說。「你很累了。你整天都在受訓、對打,而梅嘉沒有運動。狀況艱鉅。如果你要作為我們的菁英代表選民,你會被要求對付假面。狀況會如此一面倒或更糟糕。」
布萊德利看向他左邊,打量梅嘉。
「想想你能對付她而又不讓我們丟臉?如果你認為你可以幹,你可能就會有我們戰團領袖或副官的其中一個位置了。」
「我不是懦夫。」布萊德利回答。他轉向梅嘉,採取戰鬥姿態。
鐵血狼牙帶著認可看那兩人擺好姿勢。戰況從一開始布萊德利被梅嘉有多強壯、被嚇到時就很清楚了,他不習慣與更長攻擊距離、每一擊力道更強壯的人戰鬥時,則是加倍清楚。但他有受過訓練,而他很熟悉該如何使用身體,他也迅速適應。
布萊德利切換成防禦,梅嘉迅速踢他身側、撲踏向前朝他臉上刺拳。他算準時間抓住她、迅速轉成手臂固定,強迫梅嘉彎倒。有一瞬間,看起來他控制住戰況,但梅嘉閃回普通身型,將手臂滑脫,揍了他,同時又漲大。他被推到地上。
「夠了。」鐵血狼牙說。
讓那男人擊敗梅嘉可不好,而他看起來也愈來愈可能會贏。與沒能力的人比較後,會傷到她的自尊、弱化他的超能力副手的地位。
「好傢伙。」他在自己的面具下說。他向那男人伸手,布萊德利也握住他。「幹的好。恭喜你成為選民的菁英。」
布萊德利點頭,立正站好。
鐵血狼牙轉向那金髮女孩。「莉亞,是吧?」
她看起來很驚訝被選中,但她點了頭。
「梅嘉喜歡妳。我不喜歡妳。妳有一次機會證明我是錯的。梅嘉?妳要她對付誰?」
沒有太多選項。嵐虎沒辦法走路,梅嘉無法提名自己,要找來符文、奧哈拉或勝利人也很是麻煩,但那三人在搏鬥中不是太強就是實際上毫無戰力。這就留下鐵血狼牙和⋯⋯
「蟋蟀女。」梅嘉說。「同樣的理由。莉亞很快,蟋蟀女更快。」
蟋蟀女從角落的位子上站起來,一拐一拐前進。他遇見她之前,她就拒絕了奧哈拉給嵐虎的那份幫助,她腿上的傷和她喉嚨被割開時聲帶所受的傷都一樣。要花上幾天她才會回復到尖峰狀態,可是她太過重視自己的戰鬥傷疤。
「想幹嗎,莉亞?」鐵血狼牙微笑。蟋蟀女的傷會把她拖慢了一點,可是那年輕女性絕不是個容易受影響的人。
蟋蟀女伸手到她身側,拿起一根小銀管。她壓住喉嚨底部,發出的嗓音聽起來像扭曲、數位聲:「有些東西不對勁。」
「是這場戰鬥?」鐵血狼牙問,抬起一邊眉毛。
蟋蟀女張嘴,把管子壓上脖子要回答,卻沒了機會。窗戶在一陣爆發性力量中粉碎,撞倒房間裡大部分人。鐵血狼牙是少數之一依然站立,不過他在玻璃碎片扯過皮膚、穿過金屬身體的覆蓋皮的時便彎下腰。
他花了點時間在爆風中讓自己鎮定下來。他耳邊鳴響,幾十處割傷流了血,但他或多或少都還算好。他的人都不行了。他們在苦痛中呻吟尖叫,伴隨室外車子警鈴被觸響的聲音。
兩個新兵和他其中一位已畢業的選民都死了。他們都戴著眼鏡,玻璃刺穿他們的眼珠、咬進他們的大腦。其他人都受到等級不同的傷。有些人則被其他人戴的眼鏡玻璃擊中,有些受窗戶波及,還有一、兩人身上口袋——手機所放之處——有迅速擴張的血塊。
為什麼他們不能在開始對練時把手機放到一邊呢?
莉亞躺在地上垂死,嵐虎一隻手壓住喉嚨,血液從一道割口湧出那可能擦到了動脈——但也可能沒擦到。
鐵血狼牙觸及自己的內核,那身體內部的金屬抽芽的源頭「心臟」。他能感到心臟開始活動、攪拌,已經把開始翻攪的肌肉包裹。很快金屬就進出、交叉刺穿他的氣孔,幾束刀刃或針頭彼此滑衝,發出打磨的刀刺尖聲。幾秒內,他就覆蓋起身體,保護自己不被再次攻擊。
「碎歌鳥!」他一知道自己安全了,便吼道。沒人回應。當然了。她是從安全地點攻擊。
從她而來的攻擊表示這是屠宰場九號的攻擊。令人畏懼,但並非無能處理。他在這形態中幾乎無敵。沒多少人能主動傷害他。烙疤女。欷帛力虎。爬者。還有爛斧臉,那假面之中的夜魔人。爛斧臉作為例外,那群人都不能傷到他,除非他被迫站在原地。
更麻煩的是他也沒辦法撂倒那九人。欷帛力虎無法被碰觸,是個無可能移動的物體,是連雅麗珊卓也沒企及的無敵。就算他能傷害爬者,他也不想幹。偶人,他就不確定了。他知道那個瘋巧匠把自己包在幾乎堅不可摧的殼甲裡。就算鐵血狼牙再強,他還得面對任何這些人可以把他釘住或設計使他被其他人幹掉的隱約可能性。
還有誰?他絞盡腦汁。快斬傑克是作戰時的腦袋和領頭。本身不成威脅。他也幾乎肯定,碎歌鳥無法傷害他。
骨鋸。她是張萬用牌,她能提供上牌桌的東西,是最無可預測的要素。巧匠很常如此。
他大步走過房間到窗戶,望出去看那環繞選民母基地的城市街區。玻璃依然從天空墜落,在落日的橘紫陽光中微光閃爍。視野裡每扇窗戶都破了,沒有玻璃。車窗、路燈和號誌全都被影響,周圍的木板、金屬和玻璃纖維表面上都有著脆弱砲彈碎片的刮痕、刨痕。
房間裡每片玻璃頓時站立,尖端朝上。他為此分出一瞬注意,接著轉向窗外的世界,希望瞥見敵手,有他們在何處的線索。
「蟋蟀女。」他喊道。「妳還活著?」
他聽見了個聲音,有動作,他就轉身。她正輕手輕腳在武器化的玻璃碎片地面上找她的人工喉嚨。她找到後,把那根管子壓上喉嚨。「活著。」
「妳說有東西不對勁。妳注意到了什麼?」
「聲音。玻璃在唱歌。還在唱。」她指向一面牆壁。鐵血狼牙追看對街建築的天際線和幾條到另一邊的路線。
他雙耳鳴響,但他懷疑那不是碎歌鳥的能力。那會是,某種蟋蟀女用她超能力所察覺的超音波。
「那麼,妳就和我來。梅嘉,嵐虎,我就留你們看好我的選民。看看奧哈拉是否能來幫忙。」
「照做了。」梅嘉說。血液細流下玻璃裂片刺穿皮膚之處,但損傷沒更深入。她往下撈、撿起嵐虎到雙手中。
命令下達了,鐵血狼牙把他大部分血肉拉近他「核心」裡的濃縮點,感到自己在更多金屬噴出來時,活了過來。只有雙眼維持在原本位置,座落於深陷的眼眶裡,在轉動刀刃的遮蔽之下。他刀劍敲擊到有節奏的動作之前都是半盲,刀刃會快到,比眨眼更迅速地劃過眼珠表面。
他讓自己從三樓窗戶落下,比起固體更接近液態地落上地面。刀劍、矛槍、鉤子和其他扭曲的金屬形狀全流到地板上,吸收了衝擊。
他將自己拉湊回來,進入他喜愛的四足獸形。他往窗戶上看,在「雙肩」間造出一根高聳尖矛。蟋蟀女跳出來、抓住矛桿,滑到她能躍下、著陸於他身旁,在玻璃覆蓋的地面上滑步。她往下看鞋子,貌似惱怒,抬起一隻腳離地面、檢查鞋子底下。玻璃扎進了鞋底。
他能叫她無視鞋子,但他也沒辦法說話。實際上,她也沒辦法說話。
蟋蟀女指了一下,他領著路,她直接跟在他身後。他走著時,他沒移動四肢到身體可能在一瞥中被看見。他取而代之的是,在自己回收鋼鐵時也延出、生成金屬,只為了創造出四腳獸幻象。每秒長出一百個新零件來暗示那轉動的鋼鐵肌肉,成了有黏著性的型態,他完全沒在變身。只有核心骨架,在肩膀上或臀部到他膝蓋的金屬軸形成肢體,才不用收縮、延伸來實際動作。
玻璃從地面升起,組成一扇飄在空中的窗戶,他前肢打穿它。另一道障蔽升起,較為厚實,他也把它打爛。玻璃開始形成數十個,甚至數百道障蔽。他迅速發現一擊已經不足以清開路線了。
穿過幾十團骯髒、潮濕的的玻璃板,他看見她。碎歌鳥。就記憶和她暴露的膚色來看,是個沙皮黑鬼。她上半部頭覆蓋著有色玻璃頭盔,她的身體也覆蓋了細微玻璃碎片組成的流動衣著,如鱗片般。
他在雙腳上起身,筆直站立,也重組雙手。他用如電話線桿粗的尖矛,四、五十片玻璃全部打穿,接著用另一隻手也做同樣的事。這樣前進很緩慢,玻璃不斷重組、在他面前自己拼湊回來,但他也在拉近距離。
她猛然放下障蔽,轉換策略。這區裡大部分玻璃都形成一個形狀——固態玻璃的圓錐體,指向紫紅天空的中央,有二層半高。
她舉起一隻手,將椎體筆直射入上空,直到椎體成為一個污點。
鐵血狼牙撲向她,卻只發現殘留在地上的玻璃,就算有沈重衝擊和他頗有威嚴的重量,仍使他沒有任何摩擦力。拉近距離時也證實,他比希望的還要緩慢。
巨大的玻璃刺柱從空中俯衝。他知道那正在襲來,看準、算準它落下的時機然後同時跳開。
沒用。玻璃錐毫無差錯轉向他,打穿的力道幾乎足以將他撕成兩半。蟋蟀女在被玻璃碎片與金屬殘塊波及時,發出窒息般的尖叫。
「站起來。」碎歌鳥說。她有一點英國口音,而她肢體語言和清晰宣言讓她聽起來傲慢專橫、如上流階級。「我知道你有活下來。」
鐵血狼牙掙扎著將自己組裝回來。他用鉤子把金屬接回核心,鋼鐵能被重新吸收、回收再利用。不會花太多內部儲藏能量來創造、移動金屬,但耗費了一部份能量,而他不太想耗空自己。
他知道,這有風險,但他需要點時間將自己拉扯回形、重建身體。他讓頭與上部胸膛從核心冒出來,從犬科型態的鋼鐵中空「頭部」裡成形。
「你們想幹嘛?」他問。
「要人。一個。我是我們隊唯一在這的成員。」碎歌鳥告訴他。
「真自大。」
「等到你夠強你就可以自大。你也該知道的,鐵血狼牙。」
「妳是來找碴?」
她搖頭,頭盔在落日陽光裡發光。「我是九人裡主要的招募員。我有眼光看出那些能在我們之中茁壯的人,我也帶了五人以上進來。我在決定你之前想了很久、也想得很努力。我沒要讓你拒絕我。」
所以那正是她還沒用音波打擊整座城市、粉碎玻璃、殺害毀壞數百人的原因。她沒想殺掉任何未來成員,也想保存力量等著最戲劇性的時刻。
「我在原本的地方很好。」
「這不是請求。」
「是嗎?妳要逼我?」他幾乎回嘴。如果他需要,也能戰鬥。
「是的。我知道你是誰,鐵血狼牙。我花費了一點時間研究你的歷史。」
「我沒那麼有趣。」
「我倆意見不盡相同。你與雅利安隊伍同夥。順其發展,但你的動機似乎不同。我有猜過為什麼呢,可是我比較想要你告訴我。」
「告訴妳?我為什麼要告訴妳?我們講完了。」
碎歌鳥舉起一隻手,皺眉,她雙唇緊抿。「嗯。」
蟋蟀女爬了起來。她暴露的皮膚正在重重流血,大塊玻璃部分埋進了她雙手雙腿裡。發出一陣刺耳笑聲。
「失敗以前必有驕矜。」鐵血狼牙說道,大步走向敵人。「看來蟋蟀女能用她的超聲波把妳的能力取消掉。」
「看來如此。」碎歌鳥回答,迅速後退、與鐵血狼牙保持點距離。
「而我這還以為妳贏了超能力彩券。無比的攻擊範圍,細緻控制,破壞性威力,靈活性⋯⋯只要正確的噪音,所有東西就分崩離析?」
「我猜買下我的能力的那男人應該會想退錢。」
「不。我沒興趣被騙進那個,猜猜看妳到底在說什麼的遊戲。也沒要給妳機會想出搞我的方法。」他朝她打出其中一支巨大鋼矛,她將自己推到地上,滾到那把穿刺武器下。她一站立,從她閃亮裙子摺疊處裡抽出一把槍。她從鐵血狼牙的雙腿之間對蟋蟀女開槍,槍響震穿於空中。
鐵血狼牙甚至連看都不必看。他笑道:「不。恐怕我的副官比妳還要更快了一點點。」
「小心。」蟋蟀女在他身後說,她嗓音的的人工聲減損了變調與急迫性。
一波玻璃撞上他。他只用兩腿站立,一個不穩,他沒能防止被推倒在身側。
「沒在瞄準她。」碎歌鳥說。她又打出數發子彈,同時從空手中解放一片玻璃碎片。鐵血狼牙轉身,看到蟋蟀女在抓著她喉嚨,她躲開了子彈,可是碎歌鳥控制射向蟋蟀女的飛行玻璃碎片,和她控制巨大玻璃釘差不多方式。它擊中了目標。
「只是需要打散她的集中力。」
蟋蟀女倒了下來,大量鮮血噴出她指間、湧出她抓住喉嚨的雙手。
「現在就你和我了。」碎歌鳥說道。她撢掉灰塵,對構成她衣著的玻璃碎片尖銳邊緣沒有任何擔憂。「我們來談談。」
「我認為我會殺掉妳。」鐵血狼牙咆哮。
「急什麼呢?實際上,我們拖長的任何時間,都讓你有機會有增援抵達。你的嵐虎,你的奧哈拉,你的梅嘉,他們都可以幫上你一點點。延遲我們的戰鬥對你有好處。」
「除了,我可以自己把妳幹掉。」
「大概吧。」
他調整了型態,再次四肢落地。美學會受損,但他在肩膀上創造出兩根針尖肢體,高懸如蠍尾。
「啊,那樣好太多了。」她說:「但你還是太注重傳統形式。為什麼還要腿呢?」
「腿就夠了。」他猛撲。她跳到一旁,幾乎滑到大街對面。她用假面浮上的玻璃使自己懸浮。
從新優勢位置,她對他說:「我有說過我猜了你的動機。我認為自己很瞭解你。傑克很鼓勵這個,你知道的——了解我們的目標,新員或受害者都一樣。你和他待在一起就會學到很多東西。我相信你,鐵血狼牙,是個天生的戰士。」
他再次猛撲,前掌揮向她,緊跟打出針尖長肢的兩次快速刺拳。她躲開全部三次攻擊,接著在他迅速撲追她時,在他腳下掃出一大片玻璃。他落地,像走在大理石路面似地滑過地面,跌落在身側,她又朝他扔出一波玻璃碎片,把他再次推過一段街道。
他停下,將頭與上半身拉回進核心之內。玻璃浪潮靠得太近,穿透他型態的頭部、切開他的血肉。身體脆弱得太危險。
她說,他內心是戰士。他有些時候,想到自己生錯時代。若出生在羅馬的興旺時期、十字軍或世界大戰,在武技的驕傲和力量被賦予價值時代,他認為自己可能成為偉人、在戰場上為人畏懼的士兵。他津津有味地享受那種生活。這裡,現在?就算有超能力,他依然不怎麼顯著。有暴力傾向的人與渴望鮮血的人根本不會興旺。
「我沒辦法搞清楚的⋯⋯」她頓了一下,將自己扔上四樓建築頂端,接著拉高聲音讓地面層也可以聽見:「是你在和你那些『選民』在做的事。」
他無法開口回應,只爬上那建築的牆面。他爬到四分之三處時她就一躍而下,向對側街道的人行道翱翔。總是保持距離。
一道強風捉住她,她的橫向動作停了下來。風扭在她身邊時,她被重重,壓下到街道。
鐵血狼牙如果能笑的話就會笑了。他看向自己的總部,見到嵐虎蹲在前門旁,抓住自己沾滿血液的喉嚨。嵐虎無法干預重點戰鬥,但他會給鐵血狼牙對抗敵手的機會。他調整姿勢、落到碎歌鳥身旁的街上。她仰躺時抱著一條腿。她墜落得很慘。
他大步走向她,聽見她仍在說話:「你稱呼他們為芬尼爾的選民。不管相不相信,我都算是個學者。我知道芬尼爾是帶來諸神黃昏、眾神之死的獸類之一。芬尼爾也是那殺害奧丁——全父、眾神之王——的野獸。芬尼爾也是隻狼。對你來說太接近,不能說是巧合呢。」
他激起構成型態的刀刃,漲大自己,縮短距離時也漲大、使自己更顯危險。
「劍之年代,斧之年代。風之時日,狼之時日。無人有慈悲的世界。我能相信那是你的目標,你的終極任務。你渴望將這座城市拖入黑暗、鮮血與塵埃,好讓唯一的強者存活?你告訴你的追隨者說只有純血會升到新世界秩序的頂端嗎?」
他將一隻爪腳踩到她身上。他能感覺幾道自己腳下的刀刃咬進她血肉裡。她沒有戰鬥或抵抗。
「加入我們吧。」她說,嗓音扭緊。
他形成出一顆頭和嘴巴。他聲音從金屬頭骨中迴盪:「妳把我描述成戰士,那為什麼我會加入可悲的殺人犯?」
她換了姿勢,在痛苦喘息間呼出詞句:「只有規模不同而已。需要你在我們之中。前線戰鬥員。能夠在一群群無辜人士中殺出血路。打穿我們的敵人。我們能成為偉大的戰士。」
「沒興趣。」
「我們比任何數量的選民,更能創造你的諸神黃昏。」
「他們是我的人。我不會背棄他們的。」
「那就殺了我啊。」一道細微微笑展在她臉上,不過她的表情被痛苦扭曲。她說話時,更多了短句。「但要知道你的夢沒了。除非你和我們一起來。一旦你被提名就會被測試。由其他人測驗,不管願不願意。我還有留下筆記。鼓勵他們殺你的兵。夷平你可能稱為家的地方。賜予你比死亡更糟的命運。」
他把爪子從她身上抬起來。她肚子、盆骨上的傷口正在流血。
他要殺這一個就已經夠困難了。如果其他七人過來?不行,他無法自己阻擋他們,而且他的小隊長們也沒強到足以與他們僵持。
「妳不會撤回那些命令和要求?」
「我會喔。如果你加入的話。你答應我,我就離開。你會被測試。你的人不會被殺。而等到測驗結束了你⋯⋯不是死了,就是我們一員。」
「妳想要做什麼?」
「創造歷史。在史書中留名。數年裡成為學校孩子們的課本人物。數世紀皆如此。我們的目標⋯⋯」她皺眉,一隻手壓住自己的肚子:「是一致的。」
他仔細衡量了短暫一陣子。他們可以逃跑嗎?不,你無法逃脫九號。他已經考慮要戰鬥,但那選項不成。
他有對他們設陷阱。或是為他的人爭取時間逃跑的可能性。
「好吧。」
另一道淺淺微笑擦過她臉龐。她用自己的能力升起到站姿,她的腳尖僅輕觸地面。「真是忠心。」
「但我不會忘記妳做過的事。如果妳活了下來,我會等待正確的時間和地點,我會殺了妳。等著那一天。」
「已經像⋯⋯我們一員思考了呢。放心吧。我會活下來的。」
玻璃飄向她、填滿傷口,霹啪擠進正確位置,好讓每塊碎片都完美合襯傷口。最小塊的玻璃,細碎的粉塵團塊,也流進去、填滿了空隙。
接著她飛升到空中。鐵血狼牙朝嵐虎打信號,叫他停止射擊。
他沒要接受這種交易。他們污辱了他,傷害他的人。他們想破壞他的任務、將其扭成他們自己的目標?不行。
他在俯視鋪一層玻璃的街道,和蟋蟀女匍伏姿態時,他沉下臉。他告訴碎歌鳥他在未來某時,會殺掉她,也希望她預期那種事發生。
不,即使是短期加入他們,他要通過他們種種「測驗」。但他遲早都會殺了他們。在他們離開這座城市之前殺了他們。
他看向自己的人,看到奧哈拉趕緊到蟋蟀女身邊,給那年輕女性再生能力。符文也受了傷,她右側臉被扯爛,只被治癒到足夠合起傷口,阻止大量血流。大概是奧哈拉幫的。其他所有人都受了某些程度傷,很多都是重傷。
他需要其他幫助。
#蟋蟀女 #鐵血狼牙 #梅嘉 #奧哈拉 #符文 #碎歌鳥 #勝利人
ns3.14.133.138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