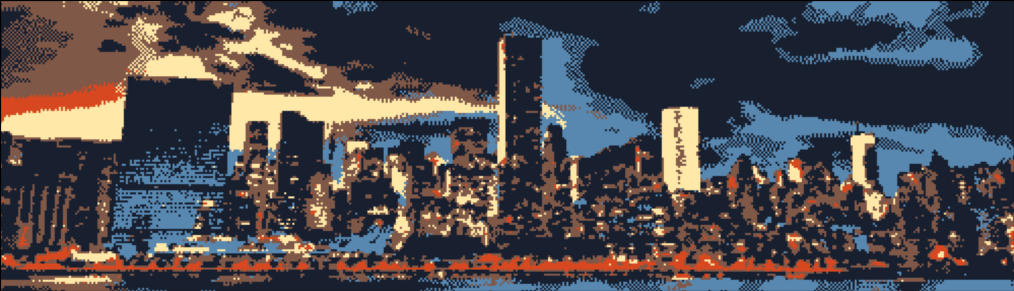 x
x
不論母狗權力展示能多麼有效,依舊對於我們這群人之間的派系緊繃,沒多少幫助。不只有凱薩被血噴到時被嚇一跳。最糟糕的狀況是,如果這個隊伍裡面爆發了場戰鬥,我很擔心這件事引起的負面情感會讓其他人聯合對抗我們。
我決定要試補救這情況。行旅人看起來是這個隊伍在場唯一,沒有已經被捲入這灘爭吵糞水之中。
「嘿。」我慢下步伐,好讓我能對那個行旅人女孩說話:「妳的名字是?」
「我的代號?」
「是啊。」
「烈陽舞者。」
「叫我掠翅吧。我之前沒辦法決定好名字,所以媒體算是幫我選了一個。」
「妳是外地黨的一個,對嗎?」
「暗地黨。我是隊上的新人,老實說,他們人還不錯。」
「呃哼。」她看向母狗的方向。
「沒有妳想的那麼糟啦。」我微笑著說。我的面具遮住了嘴巴,她沒辦法看見我的微笑,但我希望她能從聽出我語調中的幽默。「行旅人的生活怎麼樣呢?」
她貌似對這個問題來不及招架。花了數秒鐘才決定要如何回答:「強烈。暴力。孤獨。」
這個回答讓我很驚訝。她挑選了強烈這個詞,而不是令人興奮,可是那還不是她的回應最奇怪的部分。「孤獨?花時間和隊友在一起,我不認為會孤獨欸。」
她聳了聳肩:「有些發生的事讓玩樂變得比原本應該的還要不好玩。我不會解釋,所以別問。」
我舉起雙手,手掌朝上,打斷她說:「我沒要問。我只是好奇其他隊伍的情形,因為我對假面這些事還很新。」
她在我回應後有一點放鬆:「不只有那個……我沒辦法想出比吵鬧更好的詞了……可是吵鬧聽起來又太保守。不管啦。不只有正在發生的事,我們也有不斷移動,不常在同一個地方停留超過一週的時間,妳懂嗎?」
「我不懂。」我承認道。我稍微胡謅了點,就是小心以防萬一:「我小時候搬家兩次,可是我太小,根本不記得了。我主要來說,是在這裡長大的。」
「會習慣的,必須……」我突然被推到另一側時停止說話。紐特尾巴尖端推了我胸口中央把我往後推,將我頂向一輛廢棄的老車車蓬。
「嘿。」我咕噥地說,可是他搖了搖頭,將一隻手指按在他唇上。他藍色雙眼視線緊緊鑽在我身上。那是雙詭異的眼睛。沒有眼白,就只有天藍色虹膜延伸到兩側眼角,帶有著長方形、橫向的瞳孔。
我看向其他人,他們全都跑向掩護。凱薩、梵嘉和梅嘉全都躲進一條巷子裡。母狗和她的狗都消失在同樣那棟建築另一側的角落,只發出了爪子刮水泥的噪音。
在我們前面,有個穿著ABB顏色的三人組正走過街道。一個男人和一個女孩在說話,他們看起來挺像是爆彈的硬派徵召活動前的幫派成員。還有個差不多和我年紀相同的青少年女孩,在他們身後拖著腳步跟著,她看起來太累、太害怕了,做不了任何除了當新人以外的任何事。他們全都有武裝,一把大砍刀【形狀像西瓜刀但也像彎刀,刀尖刃面有圓弧設計】在混混男的手裡擺盪,而那女孩手裡則玩著一把手槍。那個看起來很害怕的女孩有一把棒球棍,好幾根釘子被打上去做成了狼牙棒。真的有人做那種東西?那根狼牙棒?
他們後面剛好就是我們的目標建築物。那是棟倉庫,牆上灰色帶著髒斑,還有著「ABB」的紅色綠色字母以精巧風格噴漆在裝載灣門周圍。
巡邏的人走了之後,紐特說:「他們有巡邏兵,而且有盯那棟樓的梢。今天,這就會是我們的目標了。」他看了眼他的手錶。
「兩分鐘之後就是行動時間。」
「我女孩們和我會繞過去。」凱薩在巷子一角聲明道:「從另一個角度攻擊。」
「嘿,不行。」我回答:「那不是說好的交易內容。我們這樣組隊是有理由的,而這個理由在我們那樣分開之後就毫無作用了。」
「我沒有向妳請求許可。」凱薩回答時,他的嗓音十分冰冷。他沒有等著回應,直接轉身離開。梵嘉和梅嘉跟著他。
「我們要阻止他們嗎?」我問。
「我能追上他們。」母狗騎在布魯圖斯的背上走進時如此告訴我們。
紐特搖了搖頭,他的薄唇緊緊抿成一條線,只讓那奇怪的外表更有特色:「不值得,而且在敵方領域裡內鬥十分危險。再說,我們也沒時間了。」
「母狗,妳能打電話給戰慄和媘蜜,讓他們知道嗎?」我問說:「他們如果需要的話,能做出相應措施。」
她點了頭就把手機拿了出來。
母狗在打電話的同時,紐特招手叫其他人靠在一起。「我們來談談攻擊的計畫吧。掠翅、母狗,妳們倆對付這些人最有經驗,所以就先說吧。」
我瞄了眼母狗。她在忙著打電話,她也曾在上次和ABB的遭遇戰時無法行動,她不怎麼瞭解爆彈是什麼樣的人。就靠我了。
我沈默地清了清喉嚨,朗聲道:「爆彈喜歡設置陷阱,而且如果這地方足以重要到有人巡邏,就會重要到有陷阱。讓我先派蟲子進去。這樣我能瞭解地形,蟲子也會讓裡面的人困惑又被分心,你們做事就比較簡單一點了。」
紐特點了一次頭:「好的。那就是第一步了。母狗,妳和妳的狗能攻擊地面層嗎?我會從二樓進去。」
母狗對他簡慢地點頭回應。
「那些蟲子不會咬她嗎?」紐特問。
「不會。」我回答說:「也不會咬你。」
「蟲子就算試了也咬不了我。」紐特微笑回答我。有趣,如果你能不看那詭異外表--藍色頭髮、奇怪的雙眼、橘皮膚和尾巴--他其實是個外表挺好看的男人。
「烈陽舞者,妳能做什麼?」紐特問。
「我猜你能說我是砲台。」烈陽舞者回應:「但是我和軌彈天人有同樣的問題……呃,他是我另一個隊友。我不確定我能不能在不會嚴重傷害很多人的前提下,用我的超能力。」
「那就和拉比琳忒斯待在後衛。妳們兩個準備好,在我們跑進麻煩裡時掩護我們撤退或推進去。」
「聽起來你滿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嘛。」我評論道。
「也許我被斷層線感染了吧。」他微微笑。然後他瞥了眼手錶:「二十秒。」
紐特看了兩位蛇蜷派來的士兵:「你們兩個,你們能……」
「我們會在這裡,取得這棟樓的屋頂位置。」兩人中比較矮的男人回應,指著我們旁邊的兩層樓公寓。「我們會以火力壓制來支援你們。」
「嗯,很好。盡量不要殺任何人。」紐特說道,再次確認他的手錶:「五秒。掠翅?開始行動吧?」
我延伸到我收集的蟲子們,排除掉那些我保存在假面服之下的個體。我指示它們前往我們面對建築的那面牆。
蟲群掃過打開來或破掉的窗戶,還有一扇在建築側面開著的門,湧流進走廊裡面。我確保它們覆蓋了每一片表面,感覺任何不在正確位置上或不尋常的東西。有好幾個人在房子裡,這並不特別讓人驚訝,可是我的蟲子和裸露的皮膚有相當多接觸。我察覺到聚集在倉庫一樓中間的人幾乎是裸體。衣服被脫到只剩內衣。這實在太突如其來讓我停下腳步。
我搖了搖頭。無法負擔分心的代價。在蟲子超級精細的感知下,牆壁顯示出完全不同的材質,爆彈大概用了金屬和塑膠。我試著將普通的東西過濾掉,只去感覺塑膠或金屬。從入口幾呎開始,我發現前往二樓樓梯兩側有兩個穹頂形狀腫塊,有金屬和塑膠。
「那裡有些東西。」我說:「給我一秒鐘。」
我運用了戰慄的作法,將一群蟲子緊密聚集起來,模糊地形成人形。我將那團蟲群移動過好幾扇門,進入那個小穹頂座落的位置。
爆炸將頗大一塊最靠近我們的建築外牆吹飛。在裡面的人們已經對匯集的蟲子們相當緊張,他們開始邊跑散開來邊尖聲吼叫,跑向出口。
「我的老天!」紐特瞪大了雙眼。
「我想,是動態偵測吧。」我說:「或是屬於距離啟動。我的蟲子普通並不會引爆炸彈,得要騙過它們才行。」
地面對於地雷來說太硬了,所以我集中注意力讓剩餘的蟲子掃過建築其他空間,略覽各個表面,尋找更多亂源。我又發現了兩個炸彈,確認沒有人在附近,便用同樣方式引爆它們。火焰的飛羽、煙霧和碎片,在我們蹲著位子都清晰可見。
「有二、三十個人在一樓,沒有武裝又半裸,十個人在樓上辦公室,有武器。」我說:「盡我所能清掉了路線上的陷阱。去吧!」
母狗跳起跑動,紐特只有幾步落後。他半跑、半爬著,他尾巴在身後揮擺,推測是來幫忙他維持平衡吧。
母狗和她的狗兒們撞進載貨灣門,直接撞穿了進去,紐特攔截了最先從建築側面防火門跑出來的人們。他一躍,像我揮出拳頭那樣快速地縮短了十五呎的距離,從一個人身上跳到另一個人身上,立刻撂倒了他們。他們那群人中有很多女人,我能以肉眼確認蟲子曾告訴我的事--那群人十有八九混了亞裔男人女人,而且他們只穿著內衣。是奴隸人口販賣?妓院?某些更黑暗的東西?我感覺皮膚上像有東西在爬一樣。
當他猛衝上建築側面,風馳電掣地滑進一扇大開的窗戶,我感到紐特輕觸過我的蟲子們。每一隻被他碰到的蟲子都從牆上掉落下來,墜到地上,還活著,但是昏迷了。
我想起自己曾在網路上讀過他的事。他的相關情報十分稀少,因為斷層線的隊員不是那種會出現在報紙和電視上的反派,很難從推測之中挑出具體細節。我確實知道的是,他的體液是強而有力的迷幻藥。即使是他皮膚累積下來的汗水,顯然在僅數秒的皮膚吸收後,就足以讓人們進入夢幻園地。
我將注意力集中在追蹤建築物內發生的事。紐特在二樓,大概在他靠近那位於樓上辦公室裡的人同時也在躲著子彈。我讓蟲子靠近他們身邊,咬他們的手和臉。我派它們爬進鼻子、耳朵和嘴巴來干擾那些可能瞄準、射中紐特的人。
凱薩、梵嘉和梅嘉在從我們對面另一側來攻擊這棟屋子。他們吸引了大部分武裝人士和巡邏兵的火力,讓母狗和她的狗兒們被卡在一、二十個沒有武裝、沒穿衣服還被嚇壞的的人們之中。從我的蟲子感知道的情形來看,她在對她的狗下很多命令。
我相當慢意識到,某個人擋在母狗可能用來參加戰鬥的路線上。攔阻她的攻擊物邊緣很細,很尖銳。刀子?這表示凱薩是那個阻擋她的人。是故意的嗎,或者他是要阻斷ABB的逃生路線?
我沒辦法感知道紐特在做什麼,因為我的蟲子沒辦法碰觸到他,但我能從他激起的空氣流動來感覺到他的動作,我能追蹤在他碰觸到的蟲子被毒品擊昏前的位置,而且我也知道紐特跑到人群中,輕輕一碰就被放倒的人癱倒的地方。一、兩個人甚至沒被他碰到就倒地了。那是其他東西嗎?血?口水?
只有一個人還站著。他和紐特在對著對方繞圈。我的蟲子在他身上沒多少作用,因為他戴著面巾或是某個蓋住他臉的東西。
不對,等等,那裡還有第二個人,正在紐特身後。我怎麼沒注意到他?
第一個人消失後,我就知道了。
我抓起我的手機,進入通訊人,自動撥出母狗的號碼。
「拜託啊,接電話啊,接電話啊。」我對著手機低語著。
我不少蟲子被打昏,紐特倒在它們身上時還有幾隻被壓扁了。我引導我在建築內的大部分蟲子去干擾那個攻擊者,希望能給紐特足夠的時間撤退。這沒有用--紐特沒有移動。
「幹!接電話啊,母狗!」
「發生什麼事了?」烈陽舞者問道。
「紐特受傷了。」
拉比琳忒斯將她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將我轉半身面向她。她沒有說一個字,她的表情在她面具布料下幾乎沒有任何改變,但是這依然是我從她身上看到最有情感的回應。
我會說些什麼,但是母狗選擇在這一秒鐘接起電話。
「母狗!二樓,紐特受傷了,李鬼在房子裡。」
在她回答前,有一段很長的停頓:「竜也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