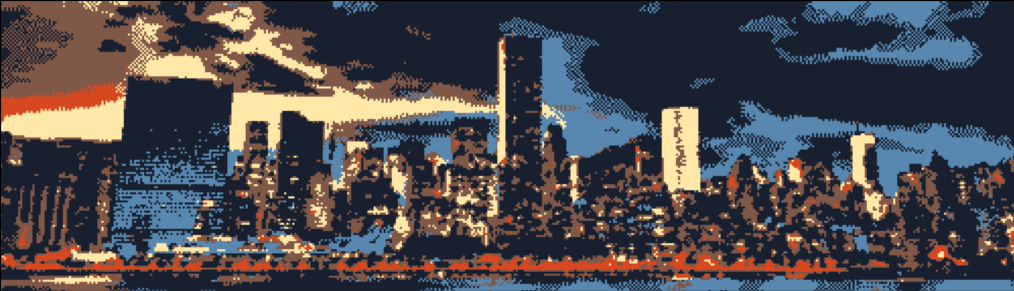 x
x
「布拉克頓灣九一一專線,你有什麼緊急狀況?」
「多處重傷。」我說,瞥了眼離我最近的街道招牌:「在懷特摩爾和桑賽特的倉庫。也請派警察和假面。這些人是ABB成員。」
電話那頭有非常短暫的停頓:「是懷特摩爾和桑賽特?」
「懷特摩爾和桑賽特,對。聽著,ABB的領袖--被稱作竜的超亞人類--在現場被無力化了,但不久後就不會全然如此。他被下藥也被致盲,可是一段時間後他的生理系統便會排除那些藥劑。」
「妳是假面嗎?」她問:「我能要妳的身分證明嗎?」
「我再重複一次。」我無視她:「他被下藥和致盲,但只有失明會是最先抵達現場的人會考慮的因素。請警告他們要小心點。妳也可以告訴他們第二個自稱李鬼的超亞人類曾經出現,可是在受傷後逃走了。他可能還在這個區域內。」
「我瞭解了。捍衛者會在抵達現場前被告知。我也有救護車、警察和PRG隊伍趕在路上。可以請妳給我妳的身分證明嗎?」
我掛斷了。
「我無法相信妳竟然把他兩顆眼睛都挖出來了。」烈陽舞者說。我們正輕快地朝著我們留下拉比琳忑斯的地方走去。
「他會治好的。」我指出:「最後總會治好。」
「妳把一個毫無能力反抗的人弄瞎了。這有點不正常。」
我沒辦法對這有太多評論。不管正常與否,這都是必要的。我沒辦法接受,假使我們將他留在那,然後他最後還能回來重操舊業的情形。我要盡了我所能,阻止他。
好吧,好吧。我願意承認,也許這個方法有一點點可疑。我和糟糕透頂的人們一起戰鬥,我也曾把他打殘。我讓梵嘉、梅嘉和凱薩離開,也算是饒恕他們對竜的人所做的事。但最後,這就是我想當超級英雄時,就想做的事:我打倒了恐怖的壞人。
我只希望,英雄們能清理這一團亂,這次也好好把竜關進大牢裡。
「嘿母狗。」我說:「妳為什麼回來了啊?」我沒辦法說得不冒犯到她,但我也想知道,為什麼當她應該要把蠑人和蛇蜷的士兵帶去看醫生時,轉頭回來了。
母狗高高騎著布魯圖斯。她看起來瞭解我的意思:「另一個士兵說他有醫療兵訓練。跟我說他能處理,我就回來戰鬥了。」
「啊。」我說:「瞭了。」
母狗並沒有說謊,我在接近我們隊伍其他成員時就看到他們。蠑人被綁上繃帶,醒了過來,另一個士兵仍躺著,失去意識。也許是投了藥,避免痛楚。
「妳做到了。」蠑人微笑說。
「差點失敗。」我承認道:「你還好?」
「我比我外表看起來更強壯。」他回答說:「算是我的,呃,獨特生理構造的好處。」
「很酷。」我回應他,沒想到更好的回應感覺有點無趣,但我想不出任何東西在說出口後,不會聽起來像太努力粉飾形象,或更糟還可能會,聽起來像諷刺。
「這位兄弟說你們八成救了我的性命。」蠑人拇指指向那位醒著的蛇蜷士兵。
「老實說,我還是很難相信,你現在竟然可以起來講話。」那個醫療兵答道。
「不管如何,謝啦。」蠑人說,他雙眼從我移到烈陽舞者到母狗,然後又繞了回來。
「不成問題。」我回答他,感覺沒有更好、更合適的回應有些無聊。尷尬之中,我找了個理由來切換話題:「聽著,我們應該要在幾分鐘內離開這裡。假面、警察還有救護車都在趕來處理殘局。」
「好喔。」蠑人說:「但我得問……有個蟑螂軍團把那些拿了出來?」
他在指著剛才躺過的地方旁邊時,微笑著。好幾包紙鈔整齊地堆疊在那。
「我忘了我做過這件事呢。」我承認說:「如果我們最後得撤退,把ABB的錢留下來,就感覺不對了,所以我讓蟲子把錢堆在那裡。每個人拿一包吧。」
「我們能拿嗎?」蠑人問道:「妳確定?」
我聳了聳肩回應。錢對我來說沒多大意義。「把這當作獎金吧,作為來幫忙的謝禮。這些,呃,沒有平均分配,所以如果從那裡拿到一整袋一元紙鈔,我沒有要污辱人的意思。」
「沒想抱怨。」蠑人說。他伸出尾巴,拎起一袋錢。蛇蜷的人幫他站立起來,你能看到蠑人花費這般力氣時皺了眉,吐出一口氣。他站起來時有些搖晃,把一隻手放在拉比琳忑斯肩膀上來穩住他自己。烈陽舞者拿了一袋,蛇蜷的醫療兵/偵查員拿了兩袋。
拉比琳忑斯沒有拿,所以我走了過去,抓起一袋,然後遞給她。她沒有回應。
「我會幫她拿。」蠑人提議說。
「她還好吧?」
「她……滿正常的。不管怎樣,對她來說還好啦。」
他拿走錢袋,留下三個給母狗和我,但沒有人抱怨或指出這一點來。
「你們需要便車嗎?」我問。
蠑人搖了搖頭,接著指向道路不遠處的人孔蓋:「我們會從那回到我們其中一個巢穴。那裡對我來說比較熟悉。」
「你有傷,那是個好點子嗎?我是指,明顯來說,那下面會很噁心欸。」
他微微一笑:「我不會被感染。我認為,我的生理對細菌和寄生蟲有毒吧。以我能記得的,我從沒生過病。」
當然是這樣。現在,我對叫烈陽舞者用酒精幫他消毒的自己感到愚蠢,而且還額外用了衛生棉,就是確保我用的東西是乾淨的。
「那你們呢?」我問蛇蜷的人:「便車?」
「我們已經有了,但還是謝了。」那個醫療兵彎下腰,抓住他伙伴的雙腕,將那人的雙手繞過頭,好讓自己能有效地把他伙伴扛在肩上。他花了點時間整理了那幾把槍,然後朝向凱薩、梵嘉和梅嘉在戰鬥開始前走過的那條街口走去。
烈陽舞者要走向相反方向,所以她簡短地道再見便離開了。蠑人與拉比琳忑斯走的方向和母狗和我一樣,所以我們就走在一起。
拉比琳忑斯就彷彿在迷亂中走路,蠑人把她當作個孩子似地牽著她帶路。這看起來很有趣,不只是看到他們之間的這種互動,還有她的雙手手套看起來並不像布料,這大概也是為什麼他敢在可能對她下藥的情況下牽著她吧……除非她免疫。這是她的能力所造成的結果?他發現我在看著,微微一笑,聳了下肩。
「自閉?」我猜著說。
他搖了搖頭:「不是,不果我們最開始有想過那種可能性。看起來,她在她的超能力出現前都是個普通的孩子。在那之後,她或多或少,都待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我想她現在看到我受傷之後,有一點惡化。」
「真的嗎?」我問,指著自己的頭,沒辦法想出一個不會冒犯人的簡單句子來描述我的疑問。
他聳了肩:「有些時候得到超能力會幹翻妳的身體。」他用尾巴指著自己,而尾巴上還拿著那兩個紙袋:「有些時候它會幹翻妳的腦子。運氣不好,但妳也只能打出妳手上有的牌了。」
「喔。」我回應道。我不確定該怎樣回答。一陣冰冷、沈靜的恐懼爬上了我的背脊。我的超能力和我的腦袋有關。我能想起自己在超能力顯現時,有多麼瘋狂,那股惡夢般的畫面、訊號和從我蟲子而來的細節的洪流。我仍會做那個事件的惡夢。我距離那種永久狀態有多近呢?
他微微笑:「沒關係啦。她真的很喜歡我們,而且我們也和她很親近。她有清醒的時候,她也在那時,讓我們知道維持現狀也沒關係。當然,她也有不好的日子,也是當她完全與世界死絕時,不過我們所有人的能力都有缺陷,對吧?」
「是啊。」我回應他,不過我仍無法認為我的超能力的缺陷和她的等級相近。
「妳認為我們現在這樣也可以吧。嗯,小拉?妳在我們把妳從那地方弄出來之後,都很開心吧?」
拉比琳忑斯就像是從迷茫中被喚醒,抬頭看向他。
「對呀。」蠑人微笑著:「妳能看出來,因為這些日子裡,她用超能力做出來的東西都更漂亮了。」他指向那個人孔蓋:「這就是我們分手的地方了。」
拉比琳忑斯往下看著他指著的地方。片刻過後,一個銀線蛛網窗花格出現在人孔蓋周圍,就像藤蔓一樣伸展、分岔。當那些銀線接觸了道路的一部分時,那一部分的馬路被提高、翻轉,展現出它底層的白大理石質地。當有足夠多白大理石裂縫圍繞時,人孔蓋翻了起來,露出底下的銀色光澤,接著被一個看不見的鉸鏈,啵地一聲打開來。一座大理石或象牙質地的旋轉樓梯一直延伸到深處。底下的白色牆面還有些微弱螢光。
「滿酷的,對吧?」蠑人回應道。當他踩著階梯往下走,他腳下踩著的東西是固體。他舉起紙袋時說:「大夥謝啦。」
「當然。」我回應:「回見。」
人孔蓋在他們身後關上,然後幾乎同一時間,環繞人孔蓋的白色物體開始消去。
我抬頭看向,坐在單眼布魯圖斯身上的母狗。安潔力卡與那隻仍沾滿粉塵的猶大正好在她身後。她遞出手協助我爬到布魯圖斯的背上。
有面具或頭盔遮住我整顆頭,會有很多缺點。如果我坐下來好好花費更多時間弄完我的面具、將護甲的部分擴大,我也許就不會得到那令人厭煩的腦震盪了。
不過好處是,在我們騎過空蕩蕩的街道,有風吹過我的頭髮時,感覺棒極了。對上李鬼後僅僅間隔幾分鐘就和竜幹起架,所引起的瘋狂腎上腺素快感,帶來了完美的放鬆感。我閉上雙眼,讓身體緊繃自然而然地順道流出。
我們這樣騎了幾分鐘。母狗有些漫無目標地轉彎移動,朝東方前進,前往水邊和沙灘。也許她是為了避免我們被跟蹤而做出閃避動作,也許她只是想要這樣騎著。我沒真心在意。
當我們終於停下來時,我突然有點錯亂。布魯圖斯踏過沙地,踩著沙走下到海灘上。母狗跳了下來,我跟著她的信號跟上了她。
現在還算下午初期,所以海灘空無一人,而且這也不是那種,會看到很多遊客出現的海灘。一座水泥牆從我們上方的路邊,把海灘隔了開來,還有一個裂開的洞口,有著曾是個爐柵的繡紅殘骸,顯示出了碼頭底下各式各樣的洩洪口。垃圾、腐敗的樹葉還有一、兩個穿過濾網的針頭,流到排水孔底下的沙子裡。
「回家去。」母狗命令狗兒們。他們一隻接著一隻,成排走進洩洪口。我猜他們會讓變形在回到閣樓之前消退掉。
接著母狗拿下了她的面具。她像是看著可笑的東西般看向我。
「幹嘛?」
「妳要換衣服嗎?不能那樣走回去。」
「我沒有代替換的衣服在身上。或放在其他地方。」
「好吧。那真他媽白癡。」她回應我。
「我決定要來之前沒想清楚。告我啊。」我挑戰她。
「妳底下穿著什麼?」
「無袖上衣和伸縮長褲。」
她看了看周圍:「天氣沒那麼冷。」
我嘆了口氣,卸下我的護甲到能將假面服後面拉鍊拉下的程度。我把假面服剝了下來--比起穿上去還要簡單得多--然後把它捆成一團,好讓面具和護甲這些所有能被認出的部分,被布料纖維隱藏起來。我赤腳底下,沙子感覺很潮濕又黏膩。
當母狗朝我臉伸手,我被嚇了一跳。她將一隻手放在我的臉一側,然後只有那麼一秒鐘的瞬間,我認為某些極端尷尬的事情就要發生了。
然後,她用力扭我的頭,讓我頭彎曲的角度幾乎與地面平行。
「妳看起來就像有人試著要把妳吊死一樣。」
「什麼?」我問。
她碰了我的脖子一側,可是我不可能在沒有鏡子的情況下,看見自己的那部分皮膚。我思考一陣子後,理解到她在說什麼。我拉起無袖上衣一角,果真,我肚子和腰上有紅黑色的淤清。我把上衣拉更高一點,發現另一個淤清在我的肋骨上。我知道也有另一個靠近我的腋下位置,一個環繞著我的脖子。
我身體上有個巨大手印,竜真有禮貌啊。
我發出長長一段呻吟,摸著脖子一碰就痛的地方:「我沒可能把這東西隱瞞我爸了。」
我好心情在我們開始步履艱辛走回到閣樓時,全都被沖進風裡。因為我幾乎只穿著內衣又光著腳,地面對我的腳來說又很冰冷,讓所有事情變得更加不愉快。
我顫抖了下,雙手盡可能環抱身體,同時也把我那捲起來的假面裝和裝著錢的紙袋拿在手中。
某個溫暖的東西落在我肩上。母狗將她的夾克裹住我時,我看向她。她往後退,那雙眉毛仍緊緊皺在一起,瞪著我,我把袋子和我的假面服捲放下,好能把雙手穿進袖子裡,也把扣子扣上。那是件帶有毛皮領的帆布夾克,但對我來說大小不適合,穿起來太重。我試著將手插進這些口袋裡面時,發現裡面塞滿了東西。塑膠袋、巧克力條、蛋白質棒、一盒果汁這樣混亂的情況,還有讓口袋往下陷的球體--我猜那是狗點心或狗食。不全然是假面的東西。整體來說,這幾乎能算上不舒服。
但這件夾克是暖的。
「謝謝妳。」我對她說,被她這舉動大大震驚。
「妳需要東西來蓋住妳的脖子。」她看起來十分惱怒:「有人會看。」
「那不重要。謝謝妳。」我給了她一道微笑。
「妳已經說過了。」她從惱怒神情直接變為憤怒:「那是我的。我能要回來。」
「當然啦。」我說。然後以防萬一,我提議問道:「妳要拿回去嗎?」
她沒有回應,讓我徹底不知所措了。為什麼感謝爸這樣的人給我禮物時,我的話語不管怎樣努力,聽起來都感覺有諷刺意味,或是很無趣,但在我這該死的唯一一次百分之九十五確定自己聽起來,正如我感覺那樣真誠,卻對母狗說,而她又不接受?
我擔心自己能說的任何話都會刺激她,我退回一直以來的沈默,也發現自己和她愈來愈常這麼做。這段路程很短,我雙腳仍感覺,在我踩路面磚時熱度離開了身體,但我的軀幹仍然是暖的,這足夠讓我繼續行動了。就這樣,我們走回了閣樓。
她打開門鎖,按著門讓我倆進去。我喊了聲布萊恩和莉莎,可是沒有人回應我。其他人還沒回來,這滿合理的,因為戰慄得在回來前去接媘蜜和攝政,而電話中聽起來媘蜜的小組也很快就要結束工作。母狗領在前頭走上閣樓,我在她之後上樓,把夾克脫下,無言遞給她。她還是在瞪著我。
我能做什麼,我還能說什麼?這就好像,我做的每件事都讓她不爽,都踩上了她的地雷。
我回到我在閣樓裡的房間,挖出了還放在那的購物袋,找出一件寬鬆的牛仔褲還有一件長袖襯衫,來蓋住我的內衣。不幸的是,沒有乾淨的襪子,不過床上是有一些袋子。我抓起一些袋子,把它們拖在我身後到客廳裡,母狗正在那看電視。她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當我在另一個沙發上把假面服放進去時,也沒有抱怨。
她拿著遙控器,我也願意讓她拿著。她持續換著電視頻道,停在一個武打電影五分鐘,接著當廣告插撥時又開始換頻道,但沒回去電影。
這樣並不怎麼有趣,可是我並不介意。我放鬆躺著,想想今天的這些事件、這些對話,還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情報。
我發現自己開始打瞌睡,我那慵懶的思考過程也卡在,那個自己恐懼睡著後忘掉思考的結果上。我強迫自己睜開雙眼,稍微坐正一些。
「母狗?」我冒險引起她的注意,希望她已經冷靜了一點。她看向我。
「呃。我們之前說話的時候,剛才不久前,我感謝了妳。妳認為那聽起來很諷刺,還是其他感覺?」
「妳又要找我麻煩?」
「不是。」我舉起雙手阻止她:「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我只是納悶而已。」
「要納悶就自己納悶啊。」她開始抓狂。在她將注意力轉回電視時,她切換頻道的速度增加了一個等級。
「如果妳回答我的話,我會給妳錢。」我試著說。
她看著我。
「那個我們拿回來的錢。妳可以拿走那些。」
她的雙眼瞇了起來:「我們應該要把那些錢分成五份。」
「是我們賺來的,對吧?我們兩人的?如果妳不說的話我也不會告訴其他人。而且我說,妳可以全部拿走。我不確定那有多少錢,但那會是妳的。」
「這是惡作劇?」
「不是惡作劇。就只是回答我的問題。妳甚至可以叫我之後滾開,我也會回房間,小睡一下之類的。」
她往後靠著,把那隻拿著遙控器的手放在她腿上,瞪著我。我將這當作同意了。
「所以,我之前問的,當我說謝謝時,妳認為我是在諷刺,還是認為我很真誠,是哪個?」
「不知。」
「妳是說妳不知道,還是妳想不起來,還是……」
「我說不知。」
「好吧。」我嘆氣道:「都可以。錢是妳的了。」
「這麼簡單?」
我聳了聳肩。
「妳說妳問完之後就會離開。」她指出說。
我點了點頭,拿起了袋子撤退到我的房間裡。
不過我沒有睡覺。取而代之的,我瞪著那架住天花板的金屬梁,深深思考,想著和蠑人談論關於拉比琳忑斯的對話。
我還在整理我的想法時,我們這夥人的其他成員就回來了。
我走出房間,身上仍捲著被子,和他們打招呼。布萊恩拿下他的頭盔,給了我一個勝利笑容,而我似乎獲得了這個下午最顯眼的傷了。
艾利克、布萊恩和母狗開始各自講著他們的冒險,莉莎把我拉到一旁。我們最後到廚房談話。莉莎問我時把一個水壺熱上:「妳還好吧?」
「沒真的受傷,看起來是很醜,我想,我感覺對學校的事情感覺更好了。」
「但妳被某件事情影響著。」
「我之前跟蠑人聊了。妳知道拉比琳忑斯因為她的超能力而有點恍神,對吧?」
「妳想知道妳自己有什麼問題,妳卻不知道?」
「不是。」我搖著我的頭:「等等,我有嗎?」
「沒啦。所以怎麼了?」
「是母狗。」
「啊啊啊。」
「我一直在想,可是我不想在腦子裡建立起某些理論,做出個假設然後讓自己丟了臉。」
「跟我說妳在想什麼,然後如果妳想錯了,我會跟妳說。」
「她真的很會讀肢體語言,對吧?她就算布萊恩有他的黑暗模糊了身影,還戴著面具,也能讀出他來。那是,什麼,她的某種次級能力嗎?」
「那某部分是天然能力。某部分--是呀--是她的超能力調整她的思考方式。這樣她才能好好與她的狗溝通。」
「對。」我瞥了眼其他人在說話的大廳。或者說是,布萊恩和艾利克在說話,母狗只站在那。「那就是了。我想著的是……也許當她的超能力給她和狗溝通的能力,也覆寫了其他東西?亂搞了她面對人的能力?」
莉莎轉了身,從杯架上拿出幾個馬克杯。她給了我一個半含歉意的微笑:「是啊。大致是那種情況。」
「所以,像什麼,她不能讀出表情,或語調?」
「所有我們在通常的對話中,給其他人的線索?她全都不懂,她集中一年的精力大概也學不來。她不只是不懂……連最基本的互動,也被硬寫入她腦子裡的犬科心理構造搞砸了。妳的微笑,問了她最近怎樣的問候,她的第一個想法是妳憤怒地露出牙齒,而她得提醒自己妳並不是如此。但就算這樣做,她大概還是想著,妳是不是諷刺,或藐視她,或某種類似的意圖,或隨便其他的東西。她知道能從妳的語氣知道妳沒在吼她,可是我們不總是在我們生氣時提高音量,妳懂嗎?」
「是啊。」
「她也會退回她能理解的東西:犬科行為,因為那在某種程度上還能運行。支配者的命令、眼神的接觸、族群的階級還有建立地盤,全部都被調整、適應進了她的人類生活。」
「所以她不真的是反社會人士。」
「不是,不算是。」
「那為什麼妳什麼都不說呢?」我有點晚才瞭解,自己聽起來像是在指責。也許我的指責是對的。
「因為她若是聽到的話,就會離開了,也因為我無法理解的原因,老闆想要她跟著我們。她花了一輩子時間接受自己曾有悲慘的童年,那些日子把她變成了一個被搞砸的人類。她的狗兒們是唯一一件對她來說正常、正確的東西。如果她發現自己這麼糟糕的原因同樣使她與她的狗如此親近呢?」
她讓這個問題滯留在空中。
「懂了。」我回應。
「所以別再談這個話題,拜託了,除非是絕對必要,而且妳也絕對、百分之百確定她不會聽到才行。」
「其他人知道嗎?」
「我不覺得會有什麼改變,而且我也不信任那兩人保守這個秘密。布萊恩是……我不想說太誠實。但是他很透明,母狗也能讀懂他。艾利克會忘記這回事,然後把這當成笑話的一部分說溜口。他有些時候不懂事情的輕重。」
「好吧。」
她倒了杯阿華田,攪拌了下,也給了我一杯。她把其他馬克杯放在托盤上,端著托盤走到客廳。我留在原地,思考著。
我回想起自己曾讀過的一本非虛構書,有個孩子在上學上到一半時他的老師才發現他是文盲。他靠著當作班上的小丑來掩飾過去。母狗是同樣的情況嗎?那些暴力和惡意能屬於掩蓋她無能交流的東西,至少部分是如此。不過,我猜想她的行為有不少部分是真誠的。她確實曾有一個糟糕的童年,她曾經生活在街頭上,拼命地過活、避免被逮捕。
但是到最後呢?就算我對每一天的互動再怎樣感覺尷尬?她肯定感覺一百倍更糟。





















